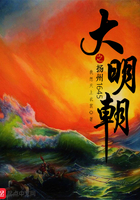(3)于是,大公爱上良秀女儿的流言也就多起来了。其中有人说,画《地狱变》屏风的事,起因就是女儿不肯顺从大公,当然这种事是不会有的。
(4)在我们看来,大公……本来是对这女子的好意嘛,好色的说法,不过是牵强附会无影无踪的谣言。
(5)这期间,有一种说法,说是大公要收她上房,她不肯依从。从此以后,大家似乎忘了她,再也没人讲她闲话了。
(6)大公为什么要烧死良秀闺女?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大公想这女子想不到手,出于对女子的报复。可是我从大公口气中了解到,好像大公烧车杀人,是作为对屏风画师怪脾气的一种惩罚。
虽是欲盖弥彰,但是小说确是从未正面交待崛川大公有何不轨,即使当“我”顺着猴儿的拉扯,“见到不该见到的事”,也还是没有明确那个让他施暴未成的人是谁。“我是笨蛋,向来除了一目了然的事,都是不能了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所有的掩饰全都不攻自破。
再看画师良秀与女儿的关系。那目空一切的良秀唯独对独生女“怀着极为深厚的情爱”——“爱得简直跟发疯似的”:(1)女儿是性情温和的孝女,可是他对女儿的爱,也不下于女儿对他的爱。寺庙向他化缘,他向来一毛不拔,可是对女儿,身上的衣衫,头上的首饰,却毫不吝惜金钱,都备办得周周到到,慷慨得叫人不能相信。
(2)良秀对女儿光是爱,可做梦也想不到给女儿找个好女婿。(吕译:但是良秀疼爱女儿,仅仅是疼爱罢了。他压根儿就没想过,快些给女儿找个好女婿。)
(3)溺爱女儿的良秀一直在求大公放还他的女儿。(吕译:良秀也一心挂念着亲骨肉,一直在祈求女儿回到他身边来。)(以上均)
(4)“我当是谁……哼,是你吗?我想,大概是你。什么,你是来接我的?来啊,到地狱来啊。地狱里……我的闺女在地狱里等我。”(良秀呓语,)
(5)“她在等,坐上这个车子啊……坐上这个车子到地狱里来啊……(吕译:等着你哪,就坐这辆车去吧!——坐上这辆车,到地狱里去!——)”(良秀呓语,)
(6)最奇怪的是,在火柱前木然站着的良秀,刚才还同落入地狱般在受罪的良秀,现在他皱瘪的脸上,却发出了一种不能形容的光辉,这好像是一种神情恍惚的法悦的光。……似乎在他眼中已不见婉转就死的闺女,而只有美丽的烈火,和火中殉难的美女,正感到无限兴趣地——观看着当前的一切。奇怪的是这人似乎还十分高兴见到自己亲闺女临死的惨痛。不但如此,似乎这时候,他已不是一个凡人,样子极其威猛,像梦中所见的怒狮。
小说几乎从来没有让良秀父女正面相遇(生离),唯一的一次就是观看火烧槟榔毛车(死别)。良秀似乎早有预感,似乎早就酝酿着一场大悲痛,似乎早就怀揣了甘下地狱的决绝。也许在他看来,活着的女儿是活在地狱里,死亡对她来说反倒是最好的解脱。对一个父亲来说,这样的爱太残酷,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样的爱也太残忍,无论怎样选择,对他都是折磨,他无能为力,他无可奈何。
因此,画师良秀与崛川大公的冲突全都集中在小女侍身上。大公把他女儿提拔为小女侍时,他“大为不服”,当场向大公“诉苦”,后来良秀几次三番地请求大公“放还”他女儿,大公的眼光则一次比一次冷淡。
(1)别的府邸不说,侍奉崛川大公的人,不管你当老子的多么疼爱,居然请求放还,这是任何一国都没有的规矩。
(2)在我们看来,大公不肯放还良秀女儿,倒是为了爱护她,以为她去跟她那怪老子一起,还不如在府里过得舒服。
(3)总而言之,就为了女儿的事,大公对良秀开始不快了。正在这时候,大公突然命令良秀画一座《地狱变》的屏风。(以上均)
可以说,他们是在争夺对小侍女的“爱护”权,不知“规矩”的良秀终于把大公一点点激怒了,“惩罚”已经不可避免,与其说让他画《地狱变》,不如说是让他自我煎熬。这是崛川大公给良秀留下的机会,给良秀女儿留下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自己留下的机会。这个机会何其漫长!良秀画到约莫八成画不下去了,变得神情“阴郁”,感情“脆弱”,这位高傲的画师,竟然“常常独自掉泪”、“满眶泪水”!难道真是因为屏风画得不顺利?而另一边,他的女儿,“也不知为了何事,渐渐地变得忧郁起来”,她“忍泪含悲”,“原本就带着愁容的这位白皙腼腆的姑娘,更变得睫毛低垂,眼圈黝黑,显出分外忧伤的神情了”。难道真是因为想念父亲?不是,都不是,这父女二人分明是觉察到恶魔逼近了,危险正在静悄悄地降临。而这时崛川大公却没出场,代替他出场的只是一个人匆匆跑去的脚步声,只剩下良秀的女儿脸色通红通红,衣衫凌乱,显得“分外艳丽”,她的“美丽”第一次暴露在月光中——最后又消散在火光中。
三个人都没有利用好自己的“机会”,他们对对方失望了,也对自己失望了,他们对峙、消耗、僵持,这时候谁轻举妄动谁就可能陷于被动,果然,“约莫过了半月”,按捺不住的良秀赤膊上阵了,他凭着对艺术的冲动,想要复原梦中的地狱之车,他没料到那车正是女儿的死亡之车,他“了不起”的灵感也让崛川大公骤然产生了“带着一股杀气”的灵感,至此,两个男人心中的怨毒终于相遇,毁灭已在所难免。
故事在悄悄地推进,不经意间最无辜的人已被拉上祭台。谋杀者剥夺的是肉体,就死者得到的则是涅槃。“在夜风吹散浓烟时,只见在火花缤纷的烈焰中,现出口咬黑发,在铁索中使劲挣扎的身子,活活地画出了地狱的苦难……”死者死矣,生何以堪?惨烈至此作者仍嫌不够,还要让一只猴子舍生取义,“只跟这位平时最亲密的姑娘在一起,它不惜跳进大火里去”。动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杀人的是人,看杀人的是人,唯有一只偷偷找来的猴儿属于异类,它不愿与人为伍了,它要逃脱,它情愿死。猴儿的意外出现强化了小女侍的死,它把绝望的惨叫留给了观众,不但给这场死亡表演增加了戏剧性,也把几近凝滞的故事推向了高潮。
作为“模特儿”的小女侍死了,作为“畜生”的猴子死了,作为画家的良秀也死了,作为“人物”的崛川大公最终也会死,作为“宝物”的《地狱变》屏风却会流传下去,有生无命,有命无生,命运种种,谁来交割,怎样均衡?芥川设下了谜局,我只能沿着猜测的小道摸索前行。
毋庸置疑,《地狱变》是一篇关于人的小说,它反复求证的是关于“美、人性、欲望、死亡、灵魂”等这样一些终极命题,而小女侍正是毫不知情的承重者,在她身上最突出的就是人性之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她让我相信:愈是人性的,愈是美的,美与人性同在。小女侍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她的人性之光,更因为那光泄露了她潜在的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好事物的认同应该是人类的普遍本能,甚至动物,甚至魔鬼。所以,猴子会热爱小女侍,良秀会珍爱小女侍,大公会宠爱小女侍,他们无一例外都看上了小女侍身上的美。这三种目光,只有猴子的目光是依恋性的,只有猴子的目光是非功利的,只有它与小女侍和谐相处,双方由此建立了一种生死与共的平等关系。当这种平衡被打破了,猴子也难以容忍美的缺席,于是蹈火赴死,替人类挽回一点自尊。它比某些人更像人,比某些人更通人性,缅想这只在火中熔炼的灵猴,有时我会想,或许它根本没死,或许它已经像悟空一样炼出了火眼金睛,或许它一直在嘲笑我们,嘲笑人类。
如果说小女侍和猴子是互补的,那么崛川大公和画师良秀则是相悖的。我注意到,在芥川笔下,崛川大公由神变成了兽,而画师良秀却从魔变成了佛。在小说又说他像“魔鬼”。神灵/大公与魔鬼/良秀怎会相安无事?二者的矛盾简直是宿命的。豪气的大公一高兴就会赏人白马三十匹,把宠爱的童子活活埋到桥柱底下,罪恶也非常“逸事”;而“堕入邪道”的良秀却蔑视神佛,给女巫画一张鬼脸,把神仙画成小丑、流氓无赖,画笔底下尽是“丑恶”。从这儿,可以看出他们大相径庭的审美趣味:前者指向的是美的表面,后者则指向了美的内核。良秀追求“丑中的美”,实际是在努力向事物本质靠近。那么多人的厌憎、咒骂良秀,绝不是因为他对丑的痴迷,实则因为害怕那支画笔,害怕他的目光。从良秀身上,能看到他对艺术的执著,虽然行为怪诞,却以绘画为使命,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气概。而崛川大公,虽与良秀格格不入,却一直相安无事,盖因神灵和魔鬼还在相互逆转的途中。
终于,小女侍进入神魔混沌处,崛川大公的肉体思维逐渐占据上风,把画师良秀的艺术思维压倒了。肉体思维讲究的是使用,艺术思维讲究的是创造。当使用无法顺利进行时,肉体思维要做的是破坏、销毁,当创造难以正常进行时,艺术思维要做的则是保存、欣赏。在大公眼中,小女侍美则美矣,他的目的不过“收房”而已。良秀要求“放还”女儿,无异于虎口夺食,欲望受阻的崛川大公激怒了,他已没有等待的耐心。以下要做的再清楚不过了,他们都必须露出原形。
在美丽的烈火中,是火中殉难的美女——面对小女侍最后的美,良秀皱瘪的脸上,现出了“法悦的光”,“他头上有一圈圆光,犹如庄严的神”,“开眼大佛一般”;而崛川大公,“却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口角流出泡沫,两手抓紧盖着紫花绣袍的膝盖,嗓子里,像一匹口渴的野兽,呼呼地喘着粗气……”这当口,良秀像神佛,大公像野兽,作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作为美的象征,小女侍驰火而去,只有《地狱变》,还完美地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