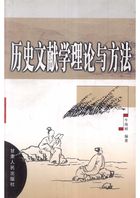“公主有言,还不快速速退去?!”见两妇人竟然充耳不闻,徐荆只得暴呵。
“诺,诺…..”。
终于明白公主是放她们走的张氏急忙爬起身,没有忘记一把猛力拉起差点瘫倒的阮氏,半拖半抱着低低道:“妹妹,走!公主答应你了,走!快些走!”
……
看见两妇人跌跌撞撞地相扶着走远,昕阳转身牵了颜女的手,迈步回府。
颜女见她心事重重,也不言语,只管相随而走。
“颜女可怪我无情?”
行至正堂聚宝盆前,昕阳看着盆里的游得欢畅的金鱼,问道。
“公主多虑了,那妇人的话确有不妥”。
颜女坦然答。
“呵呵,你有所不知。那洛阳府最是勤勉,此案关系重大,怎可不细察?若察无结果,不过是察无可察而已”。
“若真是黑巫所为,如何处之?”
颜女思索了一会儿,问道。
“颜女可有办法?”
昕阳反问。
“不知,或可一试”。
目前连公主府都没有走出去过,她自然底气不足。
“呵呵,颜女无需为此事忧虑。待我明日见过二皇兄,看他如何置之”。
“公主要去洛闲王府?不是说……”
“总是要过去看看,方可安心”
…….
与昕阳别过,颜女回到玉兰堂,却无法静心看书,阮心的哭声犹在耳际。
于是她找来一张纸,草草写“我出去了”,避过婢女和侍卫,悄然无息地走了出去。为怕被发现,她一奔千米,坐进了一间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酒馆。
酒馆是各类消息汇聚和发散的最佳地方,她想听听洛阳人对于时局的议论,所以选择了这家酒馆。
此时洒馆里,一名体形发福的中年男子和一名黑瘦青年男子一开始是悄声议论着什么洛阳、长安、黑巫、盅虫。或许是劣质酒的发酵效应,议着论着就情绪激动、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地大声争辩,及至拍桌子、踢板凳,大有打起来的势头。
酒馆的老板和伙计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全然不当一回事,只管扯破了嗓子大声地招呼其他客人。
周遭的人一面兴致盎然地观听,一面欢畅地放声大笑,更有人时不时插上几句,来个火上烧油,恨不得青年蓦地拔出别挂在腰上的利剑,去势如虹,就此来上一场鲜血四溅的生死博杀。
可是另一桌的酒已过三巡菜已过五味,这两人仍旧只是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青年男子似乎忘记腰上有剑,中年男子狂乱挥舞的拳头始终抵不到对方的面颊。
有人看着听着,就失了兴趣,安心坐下来,喝自己的小酒,也不去听那没有意义的唇枪舌剑,开始重新拾起自己的话题。
“听说没有?前几日有个丢了丈夫的妇人到公主府前哭泣,被带进府去问话”。
“爷岂会不知?那妇人正是西市的阮氏”
“当真?昕阳公主仁德,这回怕是有希望了”
“未必,公主再是仁德位高,也只是一介凡人”
“…….”
“听说官府断定此事是黑巫所有”,声音压得足够的低,却逃不过有心人的耳。
“黑巫?”,声音里满是惊惧,压抑得更低。
“怕什么?要是黑巫,太华山那边绝不可能坐视不理”
“那就好,可是大先生不是百年前已经白日飞升了么?”
“无知!大先生飞升了,不是还有二先生三先生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