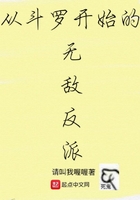Kervin的心猛地一颤。
在她小时候,她受尽了周围人的唾弃,唯有他愿意蹲下颀长的身躯将小小的她扶起,拍掉她身上的灰尘,牵着她回家。
那时,小小的她仰头望他,小声问他,大哥哥,你是坏人吗?
因她从未遇见过一个真正的好人,所以她在质疑,质疑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他还叫顾弦,接近她自然是有目的。因为律祯虽然将这个孩子带离了她亲生父母的身边,却要求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个孩子的命。所以,他的目的,仅仅是保证她性命无忧。
面对着一个稚嫩孩童小声的质疑,他低了头,对上她清澈却又有伤痕的眸,终是不忍骗她,变低下头,轻声告诉她,哥哥不是好人,但,哥哥不会伤害你的。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或许“不是好人”就等同了“是坏人”。但意外地小安然没有害怕他,只抓着他的手轻轻摇了摇,请求道,大哥哥,你不要做坏人了好不好?
那年,他也已经二十好几,却被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的眸震慑了。
她是想要喜欢这个世界的,她的眼眸里饱含了期盼与隐隐的请求,就像她现在一般。
“安然……”Kervin有口难言,碧蓝色的瞳仁里染上了一丝苦楚,许久后他才轻声说:“安然,我不想伤害你。”
“可是,你还是伤害了。”许安然轻言,“你催眠了律凌天,让他在意识涣散的状态下开走了一辆你事先准备好的车,然后他发生了事故。他的血液里检测不出酒精或是任何药物成分,车子的轮胎与刹车一切都好,所有人都会以为这只是一桩意外。”整个过程她都没有过激的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让Kervin放下心来。说完这些之后她又轻叹了一口气,“可是你不知道,当我知道这件事情和你有关的时候,我宁愿这是一场意外。”
Kervin缄默不语。
许安然深吸了一口气后接着说:“十二年前我逃出尹家的时候,我很感激你救了我,让我的人生没有差一点被毁掉。但是救了我的代价却是毁掉另一个无辜女孩的清白吗?尹思初……无论她现在如何,当年她也只是一个孩子啊!”
“对不起。”Kervin说,“但当时我没得选。当时天很黑,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必须要保住你。”
“难怪,她会恨我。”意外的,许安然笑了。声音很轻,但她笑了,笑得有些苦涩,笑得令人心疼,“你怕我愧疚,又或是怕当年的事情败露,所以在救出了我之后对我做了催眠。所以醒来后我根本不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替我遭受了原本应该是我遭受的罪责,但我确实还是受了很重的伤,又加上躲在暗处亲眼目睹了那一幕,因此潜意识里一直认为,那个被几个大男人轮番侵犯的人……是我。”她艰难地说完了这一番话,然后去看Kervin的神情。
Kervin表面虽波澜不惊,但实则却在隐忍着什么。半晌后,他才苦涩开口:“其实,我宁愿你大骂我一顿。甚至打我也行。”但是她始终没有歇斯底里,这两者的区别便像是古代的斩首与车裂两种酷刑,结果同样是死,但过程却大相径庭。
“我还想相信你。”许安然说,“Kervin,我还想相信你。所以请你收手吧!你害了律凌天,已经让凌辰丢了半条命。还有夜南歌,至少她是无辜的。”
“我很感谢你还想要相信我,这样对我接下来要对你做的治疗很有帮助。”Kervin笑得有些隐晦,“安然,以后就不要相信我了。我的立场终究与你们不同,所以还是不要信的好。”
“你不打算告诉我?”许安然反问。
“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想太多。”
许安然笑,“你真以为我清醒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做吗?”眼底隐入了丝丝寒芒,她轻声唤道:“Kervin Miller。”
米勒家族是律凌辰的母亲艾妮恩的家族,也就是说,Kervin和律凌辰,实则是或远或近表兄弟关系。
Kervin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律门还在的时候,应该也没少和米勒家族合作的吧。Kervin,你那天说你背后代表的利益是律门的,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做的吗?”许安然的语气变得有些咄咄逼人,“回答我!想毁掉凌辰的人,莫非是律门的?”
关于律门,关于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的律门,许安然其实并没有想要去追根溯源。如果她真的很想知道什么的话,就不会把Royal脖子上的那个东西藏起来不曾打开来看。也许是女人的第六感,她遏制住了自己强烈的好奇心,她想,有些秘密是她不能去触碰的。今天她之所以那么明确地问Kervin,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关乎律门的利益,无非只是想知道,是谁想要置律凌辰于死地,是谁想要毁了他。
但其实她心里又清楚,如果真的是律门,她有的只是心寒,而律凌辰,应该会生不如死。
那么,律凌辰他,究竟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的?
“是。”沉默了许久之后,Kervin才艰难地吐出了这么一个字。但坦言之后他反而觉得没必要藏着掖着了,便也觉心口的郁结散开了不少,坦然地对上了许安然的眼,“但你要清楚,无论是律门还是米勒家,都没有人想要毁掉律凌辰。”
许安然狐疑,又猛然想到那日Kervin在电话里说,律凌辰为了她已经做出了不少的退让。莫非……
Kervin见她脸色有异,叹了口气,“安然,这不是你现在要操心的事情。现在对方是有所消停了,无非是不忍再雪上加霜,让律承受更多。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好好调理自己的身体,他才能分心来做自己本来该做的事情。”
许安然从来都不想要成为律凌辰的软肋,这也是她曾经对律凌辰说的。如果非要选择的话,她愿意做他手中的那张王牌。只是她也知道,就算她真的是律凌辰手中的那张王牌,想必他也不会真的利用她。虽然,他曾经利用过。
坐在床上盯着自己洁白的小脚丫看了半晌,许安然轻叹了口气。
这时头顶冷不丁传来了一句,“想什么呢这么出神?”吓了她一大跳。
“你想吓死我啊?”是沈东驰。在知道她转院了之后,他时常会来探望她。虽然不是每次都会进来,但她知道,他来过。
沈东驰将带给她的东西放在了一边,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盯着她瞧了半晌,然后双手枕着头笑:“嗯,气色好看多了。”
许安然给他一个白眼,“你当医生白瞎的啊?”
“不错啊,还会和我斗嘴了?”沈东驰的笑意扩大,又想到她目前的状况不算特别稳定,也就不逗她了,“你留在别墅的东西我全都给你带过来了啊,你回头看一下有没有少。”
许安然看过去,大大小小的纸袋盒子成排放得很整齐,心里不由得泛了暖,但嘴上还故意说:“哟沈东驰,我那台缝纫机哪儿去啦?一台缝纫机可值不了多少钱,你还想贪了不成?”
“你也说了缝纫机值不了多少钱。”沈东驰打着哈哈,略微慵懒地说:“所以我早就扔了。”
许安然就瞪他,但想到原因之后也就悻悻闭了嘴。
在她住进别墅的第二天,因为必须要在医生和护士的监控范围之内,所以她索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这样一来便有些无聊了,思索再三之后让沈东驰给她弄了台缝纫机来,又例了一张清单让他帮她弄来上面的那些东西。
当然,这些事情沈东驰自然不是亲自去办的,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别墅里照看她,偶尔不得已还要回上海处理一些事情,所以他并不知道许安然要那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
直到有一日,许安然毒瘾发作,到处摔东西不说,还险些用剪刀伤了自己。吓得沈东驰立马勒令将房间里所有可能对她构成伤害的东西都撤走了,包括那台缝纫机。
“那……那我用那台缝纫机做的东西,你不会也一起扔了吧?”许安然小心翼翼地问。
沈东驰用鼻音“嗯哼”了一声,紧跟着便看到许安然的脸色变得极快,他吓了一跳,一下子想到了许安然现在的状况受不得刺激,赶忙说:“没有,我跟你开玩笑呢。除了缝纫机,其余的东西都给你带过来了。哦不,剪刀啊针线那些我可不敢带,我怕律凌辰把我……”他用手隔空在脖子上划拉了一下,比了一个杀头的手势。
许安然这才松了口气,看他这样又忍不住笑了,“啧啧,那多好啊,正好你给你自己验个尸。你说你这么高的造诣不能给你自己验尸多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