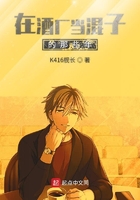我天天在元城的大街小巷奔走,眼睛不停地搜寻。遇到几个熟人,问我找什么呢,我低着头,没好气地说,我在寻找一棵树。
今年春天,我盘算着回乡下老家看看。我想念哥哥,更想念哥哥院里的大槐树。哥哥今年60多岁,厮守着大槐树。大槐树像我的腰一样粗,据说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有100多岁了。
元城一带有个风俗,孩子生下来,要把孩子的胎衣埋到一棵树下,孩子就会像这棵树一样茁壮成长。我爷爷、我爹、我和哥哥的胎衣全埋在了大槐树下面呢,你说,我跟大槐树能没感情?
乘班车风尘仆仆赶回老家,推开那两扇熟悉的大门,我愣住了。大槐树呢?仔细瞅瞅,房子没变,猪圈没变,院里的那口红薯窖没变。哥哥迎出来,一头白发、一脸沧桑也没变。我确认没有走错门,手里提着的小包裹滑落地上,给哥哥买的营养品像花朵一样绽开。哥哥弯腰捡起花花绿绿的营养品,拉着满脸惊讶的我向屋里走,给我端水喝。我一把甩开他,第一句话就是:哥,咱家的大槐树呢?
哥看看我,又把头低下,嗫嚅着吐出两个字:卖了。
我一听直跺脚。哥啊,你真是老糊涂了,缺钱花找我要啊,怎么能卖掉大槐树呢!咱爹死的时候没钱发殡都没舍得卖啊!
哥说,不就是一棵树嘛,值得发那么大脾气?你不在农村,不知道村里的情况。不是我缺钱花,而是村长出面,不卖也得卖啊。
我理解哥哥的难处,可是我不甘心我的大槐树被卖掉,就来找村长。
村长正在跟别人喝酒,看见我,给我倒了一杯说,二叔,您老回家看看?我说你们把我家的大槐树卖到哪里去了?我想赎回来。村长嘬嘬牙花子说,这事儿不好办,你赎不回来了。
我说我加倍出钱,哪怕是他们把我的树做成了家具,我也要赎回来。
村长摇晃着脑袋,吐一口酒气说,实话告诉你吧,那棵大槐树真是有福气,不仅活得好好的,比以前还风光呢,跟你一样进城去了。
我的大槐树进城了?我转身就走,把村长的招呼抛在身后。我没顾上吃哥哥为我做好的饭就回城了。
我的大槐树,你在哪里?我的脚步踏遍了元城的每一个角落,我的目光摸遍了路边的每一株花草。三天后的傍晚,我落魄地走在新建成的元城宾馆门前,望着金碧辉煌的门面,不由得眼前一亮:我看到了我的大槐树。尽管它被伐掉了半个树头,我还是能认出来。一搂粗的树身上有我童年摩挲的手印,有我用牙齿啃掉的树皮,变作了圆圆的疤痕。还有我骑过的枝干,光光的,滑滑的。
我抱着大槐树哭了,引来好多人围观。一个穿着不俗的贵妇用睥睨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真是什么人都有!这是哪来的疯子。
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半夜里醒来,大槐树身上爬满了霓虹灯。我感觉脸上湿湿的,用手一摸,原来是大槐树的泪水滴在我脸上。
天亮时,两个保安把我架走了,还把我送到家里。保安跟我儿子说,实在不行就把你老爸送精神病医院去吧。
儿子的脸色铁青,劈头盖脸跟我说,刚才领导找我谈话了,你再去宾馆闹事儿,我被提拔的事儿就泡汤了。你说我打拼这些年容易吗?闹不好工作也保不住。老爸啊,我求你了,给我们留点面子吧。儿子扑通一下跪在我的面前。
后来,我经常坐在宾馆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远远地望着抽出新芽的大槐树在风中摇晃着枝头。我知道那是大槐树跟我招手,我就泪流满面。不时有行人把我当做乞丐,把一张张纸币扔到我脚下。我不去拣,任凭纸币被风吹得七零八落,蝴蝶一样飞舞。
原刊责编 韦露 本刊责编 申平
【作者简介】 赵明宇:河北省小小说艺委会副主任,迄今已在多家报刊发表元城系列小小说千余篇,多次获奖。出版小小说作品集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