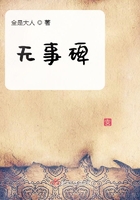我腿一软跪倒在客厅里。我不知道怎么离开的,只记得文老师说了句“你走吧”。声音冷冷的,很硬。接着一声叹息,那叹息深长吐出,绵延了很长。文老师从来不这样说话,也从不这样叹息。即便是对公认的“坏学生”,文老师的话也是柔柔的,带着抚慰。至多也就会说:文老师生气了。然后叹息一声。那叹息从心底深处发出,出口却轻柔地消化了,只是那悠长的余力会抵达听者的心里。我想,在文老师心里,我是完了。躺在床上,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这两个字:完了完了完了。直到学校院墙外传来阵阵鸡鸣,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我今辈子不会忘记那个星期天下午文老师的那番话。昨天的事不怪你。她说。语气柔柔的,一如往常。我一下就哭了,哭得一塌糊涂。我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回家。文老师叹息道:那你就会一辈子待在你那个小山村里。郭校长说你会有大出息,他看人总不错的。我哭得更凶了,我说我是个坏孩子,老师。昨晚上……文老师拍拍我肩膀,打断我的话:像你这样年龄的孩子,大都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我惊愕地抬起头来,泪眼模糊地看着文老师。她的目光像母亲:这是成长的标志,不是罪过。文老师跟我谈了好长时间,直到我情绪平稳下来。临走出办公室时,我不知咋的就咕哝着叫了声“妈”。文老师的脸一下红了:你就在心里叫我姨吧。有啥话都可以跟我说。几十年后,我在博客里多次写到关于对小姨的思恋和崇拜,写到那袭雪青色的薰衣草气息,其实都是写的文老师。
汽车突然剧烈颠簸了几下。我胃里一阵翻滚,急叫停车。没等停稳我就推开车门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完后我按下门玻璃,让凉风灌进车里,脑袋慢慢清亮了。
文老师是从江南的一所大学一路追着郭校长来到清平县一中的。郭校长是那所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文老师是中文系刚留校的青年教师。郭校长为照顾生病的妻子调回老家。不久,比郭校长小十多岁的文老师也调了过来,帮着郭校长照料了三年病人。郭校长妻子病故后,文老师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他。文老师教我们时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刚用了不长时间的语文课本被扔到了一边,语文课又变成了“语录课”。文老师独辟蹊径,从毛主席的文章诗词里挑选那些牵扯到文化人和经典作品的篇章作教材,把注释里的只言片语扩大掘深,介绍作者分析作品。学校里几个沉寂了多年的造反派指责文老师在课堂上贩卖“封资修黑货”。文老师不急不躁,笑吟吟地反问:您倒是说说,从毛主席著作里咋就弄出黑货来了,你什么意思啊。这明显是强词夺理了。可文老师问得那样温和,笑得那样温润,被反问的倒不好发作了。其实老师们都心知肚明,县革委主任是郭校长的学生,在“文革”闹腾得最厉害时就明里暗里地保护着他。没有一击致命的把握,那几个人也不好跟文老师彻底撕破脸皮。文老师就照常以她的方式优雅地上语文课。文老师教过的学生,在恢复高考时语文成绩大都比其他班的高出不少。听说“文革”刚爆发那阵子,学校造反派曾给文老师剃了阴阳头,她也不急不恼,给自己织了个很漂亮的绒线帽子,帽子前沿上镶上一枚硕大的像章。她戴着这样一顶时尚的革命帽子,依旧优雅地笑着,优雅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曾在博客上写过这段陈年旧事。一中的一位老教师跟帖评论道:“当时,文老师这样的小故事很多。经过十年‘文革’,我们学校的那批教师中,没被彻底改造的大概也就只有文老师了。真个是其淡也如菊其韧也如菊也。”我就没法相信,连在“文革”风暴中都能保持住优雅的文老师,会为了几个大钱成为上访的老太太。
停车!我猛地喊了一声:拐回清源市。司机点住刹车回头瞪着我:这就快到省城车站了。回去!我用力往后挥挥手。我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必须见到文老师,马上。
学校的小独院早就拆迁了。清平县由原先城市远郊的一个小县城升格为区,清平一中已嵌进城市深处。车停到文老师住的楼下。我爬到三楼,手指放到门铃上犹豫了一会儿。出来接我的文老师不会是广场上的样子吧。
开门的是郭校长。他头发全白了,但仍慈眉善目的,一身泛黄的书卷气。他略为打量了一下,就喊出了我的名字。说如今你可是个大明星啦。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揶揄,笑笑没做声。
郭校长给我冲上杯茶,见我看着卧室门,就有点解嘲似的“呵呵”一笑,说你文老师躲出去了,又跟她那帮人呛咕上访去喽。她说上午在那种情形下碰到你,她连一头撞死的心都有。嗨,连我都没想到事情会弄成现在的样子。我知道你心里在想啥,就跟你聊几句你文老师的事吧。清源市这几年也跟其他地方一样,各种名目的校外辅导班培训班遍地开花。一中的很多老师也都被裹挟了进去。你文老师退休前最看好的一个得意弟子,才二十多岁就在清源市英语教学大赛中多次获得一等奖,属于省厅里挂名的人物啦。他却为了办班忙得连晋级、上全省公开课都顾不上了。你文老师就沉不住气了,劝他不要为挣钱丢了前途。没想到他毫不客气地说:老师,啥叫前途?像你这样的全省特级、全国优秀,退下来还不就这样。看看人家那些行动早的老师,连小汽车都买上了。市场需要,我出卖知识有啥不对?顶得你们这位优雅的文老师“咯啦咯啦”地半宿喘不出口匀和气,害得我半夜起来给她拍后背。不料你文老师这次真是动了气也动了心。她跟我说,要是一个老师刚在讲台上讲完大道理,转身就召集起学生来,一手交钱,一手卖课,成何体统?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就毁了,学生的心灵就毁了。第二天她就去串通差不多跟她同时退休又不愿去民办学校上课的老师,要人家跟她一起免费办课外辅导班,顶顶这股风。大家反正闲着没事,乐得凑在一起热闹,就都应承下来。正好学校有闲置的教室,辅导班就很顺利地办起来了。第一次开班,教室就全挤满了。一个月下来问题就来了。你文老师,呵,大半辈子就靠诗情画意活着,什么时候都不会去掂一张人民币有多重。办学是要有成本的。资料要买吧,打印练习题要交费吧,家远的老师,中午总要吃份工作餐吧。来了,快餐店的,文印社的,书店的,都跑到家里要钱来啦。你文老师这才开始拍脑袋,噢,原来免费的是学生,欠债的是她呀。欠债还钱,这没说的。真金白银就点给人家啦。你想想,我们老两口子都是靠退休金生活的,不是大款。可是,能让其他老师凑钱吗?人家是志愿者。这年头不拿报酬,觉悟就够高了。大家就商量啊,收点成本费吧,家庭困难的继续免,有钱的多交点。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这么多学生都跑到你这里来了,断了人家的财路呵,而且对人家构成了极大威胁,文老师那里都免费了,你们凭啥高收费呀。人家早就盯上你啦。这下好了,利用公共资源,无照办班,私自收费,打得很准。你文老师的傻劲又上来了,我们没得一分钱的好处,我还往里垫呢。听兔子叫还不种豆子啦。人家一看,好哇,文老师不怕,政府不管——政府管什么,穆云很清楚真相,她太了解她文老师了。人家就找媒体去。现在的媒体,你是知道的,他们根本不管那么多,有新闻卖点就行呵。于是乎,报纸电视网络一起上。穆云先架不住了。她身在官场,有她的利益考量,何况今年是换届年呢。没说的,取缔吧。你文老师那个恼呀,就坐在这里抽抽嗒嗒地哭了半天。也难怪她恼。本来是要顶一顶那股风,却让风给吹倒啦。而且是政府是她的学生帮着人家把她打垮的。那些无证办班高收费的多了去了,为啥就只取缔她这个不收费的。她觉得受辛苦费力却落了个里外不讨好,脸面丢大了,就去教育局讨个说法。穆云是从办事处调任教育局的,她只想平安无事地挨到换届再上一步就行。你文老师却拧巴上了,教育局不行就找政府,区政府不行就找市政府。可上边根本不处理问题,一次次把她又踢回教育局。踢来踢去就斯文扫地了。越这样你文老师就越要把斯文找回来。她不明白啊,知识分子的斯文是社会给的,不是自己能讨要得到的。你知道,你文老师有多爱面子,一想到她遍布天下的学生看到他们的文老师竟然变得如此不堪,就成宿睡不着,一圈一圈地在客厅里转。郭校长顿了顿,眼睛里忽然闪出泪花。我赶紧低下头喝茶,慢慢地把涌到鼻腔里的酸涩咽了下去。
出门时,郭校长紧紧拉住我的手,用力拍打着我的肩膀说:别怪你文老师不见你。她是觉得无颜面见她昔日的学生啦。其实,她常说起你的。我赶紧抽出手,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匆匆跑下楼梯。不料郭校长又喊住了我,说:我并不赞成你文老师这样上访,人的优雅很脆弱,经不起这般折腾的。我仰头望着他那满头白发,不知该说啥好。
回到北京不久,穆云往我的微博发了条私信:我帮老太太注册了一所民办辅导学校,她把自己提拔成校长了。等着吧,你心目中的优雅女神很快就会成为财神啦。我回复道:你简直是……(我不想用那个词),这就是你用鸡对付老虎的高招吗?清平一中几代学子的偶像毁在你手中了。今后你怎么有脸再说你是文老师的学生。点了发送后,我毫不犹豫地把她放进了黑名单。春节前,我又接到穆云的手机短信:这次换届我没有进入市级班子,在局长位置上离岗了。闲下来使我明白了许多,我确实愧对文老师。我没理她。春节后,我赴德国做了近半年的访问学者。回国后杂七杂八的事情不断,手里还压着一项研究课题。等到再回清源市已是又一年春节了。
我先找到另一个在区教育局任副局长的同学,打听文老师的近况。他连连摇头:文老师咋能适合干这差事。人家那几所民办学校早就划分好了势力范围,并且用利益关系围上了篱笆。真难为她老人家了。不过现在好像好一点了。听说,穆云在暗中给文老师当顾问呢。如今的事,真是不可思议啦。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去文老师的学校看看。
学校位置不错,坐落在青花湖畔一片居民区边上。但校舍破旧不堪,不知是什么单位闲弃不用的二层小楼。我悄悄上了二楼,靠近楼梯拐角处挂着校长室的房间。见文老师正背对窗户横坐在椅子上,跟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说话。看到她那一头有些凌乱的白发,我心中一热,刚要推门进去,却见文老师把一份表格往桌上一摔,不满地训斥道:那你还等啥,人家咋办咱咋办,该请就请该送就送,招生才是硬道理呀。我心里着实一惊,便收住脚步。听那人嗫嚅道:您不是说,咱们要规范办学吗。文老师重重地叹息一声,声音忽然就浸透了疲惫和无奈:先顾眼前吧。等咱们有了实力再从头规范。现在,再规范下去就是等死呀。我愿意,人家投资的老板也不愿意呀。沉默片刻,文老师果断地吩咐:你今晚就去请八中的校长,告诉他,就说你文老师说了,你那里的生源咋就舍近求远,都跑到其他辅导班去啦。别以为他们那些猫腻我不知道,逼急了,谁也别想安生。说完,文老师猛然扬起巴掌,“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大腿上。我看着她那只伸开五指落在大腿上的手,心里一阵刺痛,没来得及多想,转身就跑下楼去。
走出好远了,我回头望去,太阳的强光和湖水的反光接在一起,岸边那座破旧的小楼明晃晃地混淆在一团光晕里。二楼阳台上有一个身影正在向这边张望,风中的白发瑟瑟地在光晕里蓬散开。我感到储藏在心底深处的那袭雪青色薰衣草气息,被硬生生地揭了下来,揭得血肉模糊。
原刊责编 张启智 本刊责编 郭蓓
【作者简介】 牛余和:山东章丘人,在《中国作家》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小说《姚爷》被多家报刊连载,并改编拍摄成电影《黑白往事》公映。出版小说集《玻璃底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