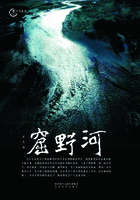良叔脸色难看闷闷不乐,独自端起酒杯饮了一口。我看出良叔不高兴,是希望我有所回应。我想了想说,欢哥一笔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捞,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小气那么抠门呢?良叔叹了一口气,纠正道,不是小气抠门的问题,而是他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的问题。我跟了他十几年,风里雨里,火里水里,舞刀弄枪,挥棒出剑,“灌窑”给他看场子,“霸市”给他守摊子,“扩充地盘”给他出点子,“强占工地”给他挡枪子,把他弄成了亿万富翁,省城买了五套房,县城拥有八套房,另外还有两个坐收租金的市场。而我,今年将近不惑,落得个什么?存款不到三十万,县城没房,省城就甭提了。做人,要将人心比自心,自己吃肉,分块骨头下属啃,自己喝汤,给点羹下属尝。不然,谁还那么死心塌地地给你卖命呢?我安慰道,良叔,谁叫咱们寄人篱下受管于人呢?要是咱们自己为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良叔的眼里闪烁出希望之光,他摘下眼镜,呵了一口气,用大拇指擦擦镜片,说,顺啦,叔找你来喝酒就是想和你商量这件事的。我想带着你脱离欢哥,投奔东哥,在开发区那块干!东哥那边的政策很优惠,挂他的名,他只收百分之三十的挂名费。那样的话,咱叔侄有赚的了。良叔脸上的那种阴郁和沉闷一扫而去,瞬间像涂上一块暖色的油彩,给了我极大的感染。行啦,我听您的。我又不无担忧地问,咱们叛逃过去,欢哥会放过咱们吗?良叔琢磨了一会儿说,曾经有一个心腹想脱离欢哥,被欢哥追杀得背井离乡两年,后来这个人回到县城组织人马,现在的势力远远盖过欢哥。凭我这十几年对他作出的贡献以及和他的交情,他应该会放我一马。这件事议到为止千万保密。春节期间,我找机会试探试探。
我举起酒杯和良叔的酒杯相碰,“嘣”的一声快要溅出火花。干!两人异口同声,继而一饮而尽。
春节前的一段时光,相对于平时要清闲许多。我的班子组织了几场“灌窑”,再就是帮助欢哥在城区收了几笔烂账,没有组织大的行动。
小年那天,我买了两份烟酒,先去拜了良叔,接着赶往县城拜了欢哥。欢哥很高兴,随手从包里掏出三万元现金递给我,让我去给父母买点礼品给自己添点衣物。
怀揣三万元钱出来,我的心里荡漾着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虽然只有区区三万元,但我的父母劳作一年未必有这个收入。找到欢哥这座靠山大半年,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吃喝穿都不在话下,我还有了自己的存款。作为一个不到十八岁的青年,我还有什么不知足呢?何况,春节过后,跟着良叔单飞出去,前方还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向我招手致意咧。
带着这般美丽的心情,揣着这份美好的憧憬,我来到商城,在进旋转门的刹那,我的眼前一亮,黄倩倩竟然在我前面的门格里。我们为这种邂逅喜出望外激动不已。我说,咱们到隔壁“罗兰咖啡”去叙叙旧吧。她一脸羞红地答应下来。我真想凑上前去,啃一口她红扑扑的苹果一样娇美的脸。我们手牵着手来到“罗兰咖啡”,找了一包房。
我问她,你还好吧?她噘起樱桃小嘴,小声道,好什么?你逃走后,我在学校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到省城父母身边,帮助他们守摊子。我有些愧疚地说,连累你让你受苦了。她毫不在意地说,没受啥苦?就是想你想得很苦的。说着,眼睛向我放了一次电,勾得我魂魄出窍。我反锁上门,走过去抱住她,在她脸上狂吻。一边吻,不安分的手从她的内衣里伸进去一边摸,一丝不苟,步步为营,摸遍了她的全身。我难以自制地说,我要!她理智地说,我也想要!但我们得遵守约定。等到你十八岁那天吧,我会毫无保留地献给你。说完,莞尔一笑。那一笑甜到了我的心里。
吃完饭,我从兜里掏出一万元递给她,你去买点衣服和化妆品吧。她愣了一下,惊问,哪来这么多钱?我得意地说,跟着欢哥赚的呗。她饶有兴趣地问,跟着欢哥一定赚了不少钱吧?我点了点头。她抱住我的胳膊,撒娇道,我也要跟着欢哥去干。我摇头否定道,你一个女流之辈,怎么能干这个?她反驳道,女流之辈怎么啦?女飞侠、女特工、女间谍多得是,比你们男人干得不会差。我坚持道,反正不行。她摇着我的胳膊嗲声嗲气地问,为什么不行吗?我解释道,这里面很复杂,一时说不清,春节以后再谈吧。她很不高兴地站起身,眼泪汪汪道,我都是你的人了,你却什么都隐瞒我。你不让我加入欢哥的班子,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吧。算了,看来你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说完要走。我拦住她,抽张纸巾给她擦去泪水,劝慰道,你别耍小性子了,我告诉你。她破涕为笑,歪倒在我怀里。我有些迟疑,因为那个秘密是我和良叔不可外泄的绝密,要死人的,能告诉她吗?正在我犹豫不决时,她那只柔软的小手伸进我的内衣,在我胸前轻抚,我盛装秘密的宝盒不攻自开。我小声道,我和良叔准备脱离欢哥,挂靠东哥,自己单干。她并不惊讶,劝我,欢哥对你不薄,为什么一定要“叛逃”呢?我说,欢哥的确对我不薄,但我要赚钱。良叔提醒我,跟着欢哥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我今后怎么养活你,让你过衣食无忧的生活?说完,我在她的脸上嘬了一口。她追问道,离开欢哥投靠东哥是良叔的主意吧?我不置可否没有回答。
晚上,我陪她到“飞歌夜总会”疯了大半夜,把她送回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5
正月初二早上,父母督促我给良叔去拜年。我拎着别人孝敬我的礼品来到镇上良叔家。良叔把我拉到书房,告诉我,已经和东哥接上了头,东哥非常高兴“收编”我俩,还愿意为我和你提供一切保护。我急不可耐地问,咱们什么时候过去?良叔说,我和欢哥约好了,明天下午去给他拜年,顺带说一说这件事。我欣喜地说,等着您的好消息。
回到家,我和同村的几个同学玩牌,从初二下午一直连轴转地玩到初三晚上十点。回到家,人疲惫不堪,刚要睡下,手机响了,是表婶的。她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良叔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出车祸了,正往县人民医院送,让我迅速赶过去。我睡意顿消,让父亲骑着摩托车驮着我往县医院赶。在快上开发区的大马路时,快速行驶的摩托车被一根电线绊住,父亲和我摔在地上。刹那间,两个蒙面人直奔我来,在我左小腿上狠狠地砍了一刀,痛得我昏死过去。
我躺在省城医院里,不敢回忆那恐怖的一刻。幸亏我父亲送我到县人民医院及时,县人民医院没有耽搁又用救护车把我送到省城医院,医生很快安排了手术,才保证我快要砍断的腿能够移接上,保住了腿不落残疾。想到良叔的离奇车祸,想到我突然遭到砍杀,难道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连环行动?良叔初三那天在欢哥处喝完酒后,欢哥派车送他回镇,良叔坐在副驾位置,行至半路,司机避让一辆大巴车,便一头将小车撞向路边的一棵大树,正好将坐在副驾位置上的良叔撞成“肉饼”,而司机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最为蹊跷的是,怎么会有蒙面人守在路口,好像早就料到我一定要通过那里一样,并且蒙面人没有动我父亲,只是砍断我的小腿……
住院期间,父亲一直陪护在我的身边。父亲只有四十多岁,长得太过于“着急”了。头发花白,好似下雪天掉在头上怎么也抖落不掉的雪花,脸上皱纹密布,棱角比搓衣板还要明显,整个人变得更加沉默少语。母亲既想照看我,又要顾家里,心惊两头慌,人变得像祥林嫂一样,神神叨叨落魂掉腔似的。我知道父亲母亲心里哑急哑怄。他们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珍贵,把虚荣看得比身体还重要,但我的受伤让他们的面子赊光虚荣掉尽。他们本以为宝贝儿子找到欢哥这座靠山后能够顺风顺水一路风光下去,没想到这种风光短暂得昙花一现,只维持了大半年时间。还有一点,他们从良叔的悲惨人生结局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我的未来。所以,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惊惧、愧疚、担忧、迷惑等。他们在我面前想说又不敢说,说深说浅都不好。他们不说,我也懒得搭理,反正每天躺在病床上,我能心无旁骛地对着白墙壁发呆,一待可以几个小时,思考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