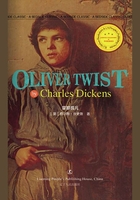我杀人了!这个声音一直在我脑际萦绕。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兴奋,抑或还有一种新奇。我茫然无措,像一只无头苍蝇瞎撞乱飞,漫无目的地蹿到东顺河边,才停下脚步。
我杀人了,学校是不能回的了,公安机关肯定会缉拿我,我得逃走!前路漫漫,往哪里逃?逃回家里吧?不啻自投罗网。逃往外地吧?身无分文,又没身份证,只要网上通缉就会露出原形。没有别的路径,我只能投靠良平表叔。
我失魂落魄如丧家之犬一样一路狂奔回到镇上,敲开良平表叔家的门,随他走进里屋。我单膝跪地,双手托着那把水果刀,邀功讨赏地表白道,叔,我用这把刀杀人了。良平表叔接过刀,看过刀尖上残留的血渍,不相信地问,你敢杀人?我鸡啄米似的使劲点头,唯恐他不信,便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经过。良平表叔把我扶起来,指正道,顺儿,你没有杀人,只是用水果刀刺伤了人。我说,我别无选择,只能投奔您和欢哥了。良平表叔欣然道,一年多前,我小看你了。不错!不错!今天我代表欢哥正式接收你。这把刀就是你进入欢哥班子的“通行证”,刀尖上的那片血渍就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见面礼”。
我紧张不定晃荡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想到自己已经成为欢哥班子里的一员,我的心像爆米花一样炸开了花。我终于不再受人欺负,终于可以为所欲为地做我自己了。
睡到第二天早上十点,良平表叔从外边回来叫醒我,告诉我那个马天磊没有报警,腿上缝了几针在医院躺着,他已经找人打点好了。我的心里一阵暗喜,原来拿刀捅人也不过如此,花点小钱就能摆平了断。我像卸下了枷锁一样感到浑身轻松,诚恳地向良叔表达了感谢之意。接着良叔特别交代:这几天你给我避避风头,老实在家待着,读点法律书,多记点刑法知识,再看点破案的书。我噘起嘴,小声咕噜道,还要读书记东西呀。良平表叔很严肃地教诲说,不仅要读要记,还得认真地读用心地记。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踩着法律的红线,或者说在钻法律的空子。知道什么违法什么不违法,对于你今后为人处事会有很大帮助。我瞪大眼睛,似懂非懂地回答道,是的。
昏睡中的我发着梦呓:是的……是的……连续重复了多遍。
顺子——顺子——母亲坐在床边,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过来。我望望窗外已是夜色密布,恭喜道贺的人群已经散去。
我怎么睡了这么久?我爬起身,问道。父亲走进来,有些不满地责怪道,你不该喝那么多那样猛。吃完晚饭,客人离开时找你打招呼,不见你人影,弄得我和你娘很没面子。母亲端来一碗糖水荷包蛋,递到我的手上,饿了吧,快吃。我真的感到腹内空空,接过碗筷,仰头喝光碗里的糖水,没歇一口气,一连吃掉了碗里的八个荷包蛋。
母亲接过空碗和筷子,立在那儿,似乎有话想说,但欲言又止。父亲朝母亲使劲眨眼睛,母亲没理会。父亲下定决心豁出去一样,小心翼翼道,顺子,咱们罗家历来规矩本分,你跟着你良叔到欢哥手下做事,千万不能做犯法祸害百姓的事,更不可杀人放火欠下血债。我埋头没有吱声。母亲接着补充道,我们允许你进欢哥的班子,只是希望你在那个环境里混混,借那个名声和那股威风不让我们罗家受到欺负。最多跟着他们干点小偷小摸鸡鸣狗盗的事,切切不能动刀动枪走私贩毒。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我缄默无语没有表态,因为我没法表态。
2
我虽然正式成为欢哥班子里的人,但我还没见到过欢哥。我很渴望见到他——我心目中的英雄,哪怕晃一眼都行。可是良叔就是不给机会,让我满足一下如饥似渴的好奇心。将近两个月,良叔只让我待在住地。我们的住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老巢,算上请的那位大师傅,一共住着八个人。临街面一幢三层楼房,供我们吃住。楼房后边便是一小院,约七八十平米,水泥地面,供我们活动。走进小院,最为醒目的就是钢管架上吊着的两只沙袋,像两个吊颈鬼,深夜起来小便时让人看得心惊肉跳。良叔给我安排的活动是上午看书学习,下午练功夫。名曰练功夫,不过是不厌其烦地从各个侧面或拳击或脚踢沙袋,单调乏味得只想一头撞沙袋死过去。晚上,更无聊,另外几个都领命而去,只留下我一人值守,可怜我只能翻来覆去地换台看电视。
那天吃过晚饭,我的几个同伴放下碗后就出去行动了,又留下我独守住地。我带着怨气问,良叔,您到底安不安排我工作呀?良叔答道,安排你上午学习下午强身,这就是你目前的工作呀。我充满期待地憧憬道,我希望和他们一样,马上投入到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去。良叔瞟了我一眼,苦口婆心道,顺子,让你上午半天学习,是希望你熟记法律知识,知道什么是违法什么不是违法,这样你就可以在行动中能不违法处理的就尽量不违法。需要违法才能处理的,你就知道哪方面违了法而尽量不留证据。至于让你下午练习拳脚,是因为你虽然长了一副男人的皮囊,但肌肉松垮骨骼脆弱,根本经受不住剧烈磕碰和高强度对抗。如果要想在搏击中赢得主动且立于不败,必须具备钢一样的体格铁一样的意志山一样的力量,你准备好了吗?良叔的话把我问得羞愧难当无言以对。良叔用心修炼锻造我,是希望我成为行走江湖的“东方不败”,而我却懵懂无知不予配合,真是太令人失望了。良叔窥察出我内心的反省,鼓励道,不要泄气,加油!今后参加行动的机会多的是。
机会说来就来了。和良叔谈话后的第三天,吃完晚饭,良叔召集我们围成一团,小声布置道,老大组织了一场“灌窑”,八点钟开始,现在我们就出发。大家关上手机放在宿舍。我有点像听天书似的摸不着头脑,“老大”不用猜一定是欢哥。“灌窑”是什么?还有为啥要把手机搁在住地,等会分散开来怎么联系?带着一肚子新奇,我低声问了小胖。小胖把嘴贴近我的耳窝,用一只手遮着,小声告诉我,“灌窑”就是赌博。把手机关着搁住地,是警方的GPS定位系统太厉害,怕暴露。为了便于联络,等会到达现场后,良叔会发给我们每人一部新手机。
原来如此!
我们专用的交通工具,一辆小型五菱面包停在门口,小六子负责驾驶。良叔坐在副驾位置,我们其余六个人像堆人肉似的挤在后厢里。行驶约摸一刻钟,五菱车在进入芦生湖的路口停下来,良叔下了车,让大家坐在车上待命。我们坐在车里闲得无聊,小非便提议由小胖讲个笑话。小胖抹了一把充满喜感的“幽默脸”,努力睁开怎么也难睁开的篾片眼,润润鸭公喉,绘声绘色地讲道:一对夫妻闹离婚争孩子,妻子首先说,孩子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应该归我。丈夫听后,驳斥道,胡说八道!那银行的柜员机里出来的钱能归柜员机吗?妻子问,那归谁?丈夫得意洋洋地说,归插卡的人!
我们哄然而笑。
良叔接了一个电话,迅即回到车上,给每人发了一部新手机后,便给大家做了分工:小胖和黄黄负责收缴入场人员的手机。憨憨带老八、小奇和小非当“钉子”,也就是放哨。小六子负责运送人员进场。我陪良叔照护场子。
分头行动吧。良叔发话道。
一班人下车后四处散去。
我跟着良叔,随几个拎着红色拉杆箱的老板坐上五菱车,小六子花了五六分钟把我们拉进“场子”里。
所谓的“场子”,原是一个渔行老板在湖河密布的湖心垒起一块干地而建造的两层楼房,准备对外经营农家小吃的,没想到交通偏远乘车不便,来消费的人寥寥无几。渔行老板经营不下去,提出转让,被欢哥低价收购,成为了欢哥组织“灌窑”的主要场所之一。
“场子”外边没亮一盏灯,黑黢黢的,隐没在漆黑一片的湖河中间。
推开厚重的木门走进大厅,富丽堂皇的大吊灯把大厅照得金碧辉煌。几名老板在皮沙发上坐下,很快就有服务小姐为他们送上茶水。
约摸一刻钟工夫,十二名老板到齐,良叔把他们引上二楼。二楼一分为三,左边是按摩松骨室,右边是喝茶休息室,中间为“灌窑”室。一张直径约两米的圆桌摆在屋子中央,聚光灯呈扇形射在圆桌上,亮如白昼。窗户被黑色天鹅绒窗帘遮蔽。两排箱形换气扇刺破屋顶,吸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圆桌周围,摆放着十几只颜色各异的吧台转椅。
一位老板从一百多颗骰子中挑拣出两颗,其余的老板便轮流拿在手上掂掂,相继又查看了碟子和摇筒,接着十二位老板推选出了一位“宝倌老爷”,也叫“庄主”。“庄主”也不客套,马上订下了许多规矩,十一位老板点头称是表示没有意见。
良叔让我专门负责抽“喜头”。所谓抽“喜头”,就是一注赢万元者,开场子的吃五百元的“红”,由我把五百元丢进旁边的一个圆形不锈钢的缸子里,行话叫“打缸子”。
随着赌注从两千元涨至五千、一万、两万,“打缸子”的钱越来越多,缸子一会儿就装满了。这个时候,我再把缸子里的钱倒进旁边的一只柱形铁皮桶内。
两小时后,一个秃头老板红色拉杆箱里的四十万输完。良叔把他拽到一旁,劝他到隔壁休息室喝杯茶静静心。秃头老板笑道,没事。手一挥,叫道,来二十个。坐在一旁“放码”公司的小青年立刻送上二十万给他。他打了一张欠条,又返给小青年一万“水钱”。秃头老板拿着十九万,换了一个地方坐下,观察几宝后,便五万一注地下,连续赢了几宝,面前的钱堆得像小山一样。
离十二点还差两分钟,良叔提醒道,时间快到,抓紧押宝。话一落音,老板们便开始收拾桌子上面的钱。有几个老板提议加时一小时。良叔笑道,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为保险起见,今天只能到此为止。老板们有些依依不舍地下到一楼,乘车而去。
趁两位放码的小青年清点“码钱”之机,良叔从柱形铁桶里抓出一大把钱顺势塞进我的裤包里,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若无其事地走到洗手间,把鼓鼓囊囊的裤包捂平。
“打缸子”攒了大半桶钱,良叔将盖儿盖上,并反扣好,又拿来透明胶反复绑了几个回合后,交到放码的两个小青年手上。其中一个小青年交给良叔一个纸包说,犒劳犒劳弟兄们吧。良叔接过纸包,在手里掂掂,说,谢谢老大。
两个小青年抬着战利品被一辆悍马接走,一楼大厅里只剩我和良叔。好多疑惑像蜘蛛网绑住我的脑袋,让我理不出头绪不知道从何问起。良叔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说,“打缸子”弄了大半桶钱,为啥不理出个数来?告诉你,如果数出具体金额,今后说出来就成为无可辩驳的铁证。还有,十二点时,有些老板提出加时一小时,你当时看我的眼神好像也希望我顺应老板们的想法延时一个钟头,觉得“打缸子”又会增加一大笔钱。但是“灌窑”四个小时,输的没输很深,赢的没赢很多,反正都没尽兴没过足瘾。他们马上会提议组织第二场第三场,就像一个没吃饱的孩子,心里总惦记着那块食物。这样,欢哥的“场子”就可以长盛不衰地开下去,“打缸子”和放码的“水钱”就能细水长流源源不绝地涌进欢哥的口袋。我愈发感到好奇,忍不住地问,这一次的收入就是几十万,一年下来欢哥得赚多少钱?良叔说,为啥都要出头当老大?还不是因为财源滚滚“钱”途无“量”。接着叮嘱我,你今后少打听这些,知道多了不好。
突然,警笛声响,一位矮矮胖胖身着警服的警察大摇大摆迈着八字步推门而入,开门见山地斥责道,胡良平,你狗日的胆也真大,敢在我的管辖地带聚众赌博。只可惜我接到举报晚来一步,要不然老子抓住现行送你去劳教。我被吓得大惊失色,心蹿得老高,快从喉咙口蹦出来,命悬一线啦!要是他们早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良叔不慌不忙地安顿那位警察坐下,递给他一支烟又用火机给他点燃,心平气和道,汪所长,一帮朋友在一块聚聚,乐和乐和。借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在你的地盘上聚众赌博呀。良叔给我一个眼色,示意我离开。我拉开门走出去,但我留下一手没合上门。从门缝隙里,我看到良叔从荷包里掏出一沓钱塞进那位汪所长的荷包里。汪所长推脱几下,但被良叔按住了。
良叔殷勤备至地送汪所长上了车,警车耀武扬威而去。我很不解地问,他们是来抓赌的吗?良叔摇摇头,低声道,欢哥同汪所长是铁哥们,他怎么会抓赌呢?他此时来,传达两层意思:第一,我接到举报出警了,对社会对上面有个交代。第二,让你知道他给了你保护,你吃了盐酱得晓得咸淡,给他好处。联想到良叔塞给汪所长的那沓钱,我明白了个八九分,汪所长是欢哥开“场子”的靠山。
坐上五菱面包车,在返回途中,良叔发给我们每人五百元钱的辛劳费。想到铁桶里为欢哥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而落到自己手上的只有薄薄稀稀的五张,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巨大的落差,但迅即我自找台阶地宽慰自己,毕竟你还赚了五百块钱呢。
回到住地,关上房门,我掏出良叔塞到我裤包里的那堆钱,一张一张地抚平叠正,并用报纸包好,送到良叔的卧室,递给他说,一万零七百元。良叔打开报纸,抽出七百元递到我手上,告诫道,欢哥赚大头,我们逼一点沁水,赚一笔小利。你今后放精明些,手脚要麻利。像我们这种人,是没有未来的蚂蚱,得见缝插针能捞则捞,为自己留点后路。我恭顺地回答道,谨听良叔教诲。
我第一次拥有了一千二百元钱,夜晚睡得很香,感觉到自己被一张一张的票子包围着。
良叔对我第一次行动颇感满意,隔了几天,他又分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带着小胖和小非去处理镇工业园区一起征地纠纷。我只来了两个多月,参加行动次数极其有限,但良叔指定由我带队,我心里没多大的谱。为了打有准备之仗,我便独自一人提前去摸摸情况。其实事情很简单,镇里引进了几个工业项目在园区落户,需要征用铁湾村的一千多亩地,村里同意了,大多数老百姓也签了字表示认可,但以赵大勇为首的一小撮不仅不在协议书上签字,而且还占领工地阻挠施工。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将近半年。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几个投资老板向镇里通牒:再不处理下来,撤资走人。镇里没办法,便把这个“包袱”甩给了承建园区工程的建筑老板,限令他一个月之内搞定。建筑老板只能效仿其他地方的做法,花钱雇请黑道干预。
赵大勇是“重点目标”,我便着手对他进行全面调查,得知他今年六十二岁,从镇水管所退休,生有一子一女,均在外地工作。赵大勇也叫“赵大胆”,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敢说敢当。他带头挑事的主要原因认为镇里每亩地给农民的补偿款太少,只有六百元,提出每亩至少补偿到一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