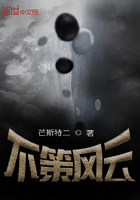1
我叫罗太顺,今年十七岁。不,应该是过了十七岁,虚岁十八。
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在我家门前的禾场上,架起了彩虹门,搭建了戏台,宴请亲戚、乡邻及朋友,一共摆了六六三十六桌。那热闹的阵势和喜庆的氛围,丝毫不逊色于前几天我隔壁田大头的结婚场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种风俗,一年四季除农忙的那几天外,几乎天天都有喜事请客摆酒。婚丧嫁娶自不用说,像田径举重射击等传统体育项目一样,最早被列入奥运比赛项目。满月十岁六十大寿,外加当兵和考学,也像游泳和篮球排球足球一样,逐步被列入奥运比赛项目。接受邀请去吃喜酒,是要赶情的,早先时只赶两块钱的情,就可以去撮一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情钱从三块到五块再到十块再到三十块五十块,现在连一般的乡情已经翻到一百块了。不过出一百元人民币,可以拖家带口到请客人家去蹭一天的饭,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妇女同志解放一天。由于家庭不同,成员有异,在赶情中就出现了差别,有的家里一年请几次客摆几次酒,而有的家里几年也轮不到请客摆酒的机会。比如我家,爷爷奶奶过世得早,父母只生有我这一个独种宝贝儿子,完全没有由头请客摆酒赚情钱。一年赶成千上万的钱出去,几年没有半分钱回收,所以有些家庭便突发奇想,设立了订婚筵、乔迁筵、五岁筵、七十八十寿筵,像乒乓球羽毛球一样,半路挤进了奥运比赛项目。还有的家庭连这些也排不上,干脆就自出心裁地把母牛生下牛娃、母猪产下猪崽等,只要是沾上一点喜庆的边,都成了请客的理由。就像奥运会在哪国举办,该国便把本国的优势项目列入奥运比赛项目中一样,可以多拿金牌呀。你知道我们乡下现在什么职业最赚钱吗?整酒席的厨师以及他一条龙的团队,光我们村上就有十二家,连喂了一生猪的康老头,在他六十岁时也自学成才改头换面,网罗几个人敲起了整酒班子。
既然是我的喜事,那就该说说我自己了。父母为我摆酒请客,不是我考上了大学,也不是我验上了兵,更不是我要订婚。那是什么呢?说实话,我真有点茅厕里拣张纸——开不了口。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对比那些靠牛下娃猪生崽等动物之喜请客的人家来说,我可名正言顺多了,我毕竟是人啦!我毕竟是加入进了欢哥的班子呀!何况加入某某班子请客摆酒并不是什么稀罕之事越轨之举,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多好多家了。
欢哥是何许人也?欢哥就是欢哥,在我们这一块名气很大,如雷贯耳。小孩哭闹,大人只要说欢哥来了,小孩顿时停止哭闹,比注射麻醉剂还管用。因为欢哥声名响亮,所以我们这里的人只知欢哥而不知他姓甚名啥了。欢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共产党内的人。你说他是黑社会团伙头目吧,好像够不到边,因为他没什么组织什么纲领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垄断什么行业。你说他是黑道老大吧,有点牵强,他没有走出自己的那条“道”,同时也没看出他有杜月笙、黄金荣那样的气魄和势力。准确定义,欢哥至多算是一个黑帮小头目。但镇上的人都说,欢哥是道上的“镇长”,说话比镇长管用多了。
彩虹门上的对联是我表叔良平做的,上联是“红道黑道白道,道道互连”,下联是“水路陆路公路,路路相通”,横批是“殊途同归”。表叔良平三十多岁,戴一副眼镜,人瘦瘦的,一看就是猴精相,他是欢哥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因为在“四大金刚”中他的年龄居首,大家都尊称他叫“良叔”。
戏台上唱着传统花鼓戏《十三款》,嘉宾们各找位置坐了下来等着开席。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作为支宾先生的良叔还是用麦克风宣读了欢哥写来的致辞。应该说,欢哥的致辞信提升了我家请客的档次,给我以及我的父母长了很多脸。致辞念完,掌声雷动,锣鼓齐鸣,鞭炮轰响,礼花绽放。
父母带着我到各桌去敬酒。父亲有些佝偻的腰板终于挺直,一副扬眉吐气的模样。母亲不知笑为何物,成天挂着一张苦瓜脸,今天也终于滤掉苦汁展露笑颜,比那铁树开花还要神奇。我生性有些羞涩,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羞于见人难以开口,只能像跟屁虫似的尾随在我父母之后。当听到宾客说“你们的儿子有出息了”的赞许以及“你们罗家终于翻身,再也不用低人一等”的恭维时,我的内心充满自豪,脸上写满荣耀,在大伙的吆喝声中,我不说一句话,仰脖抬头,一口一杯地喝。每到一桌,敬人一杯,接受回敬一杯,一桌喝两杯,待三十六桌敬完,我用“肚脐眼酒杯”喝下去七十二杯酒,少说也有一斤儿八两。一会儿,肚子里翻江倒海汹涌澎湃起来,我感觉到自己有些支撑不住了。
我踉跄地走进堂屋,自持不住,“哇”地吐了一地。一只小狗跑进来,呼啦呼啦地把我的呕吐物照单全收。不一会儿,便躺在我的脚边。我用脚踢踢小狗,它却醉得狗事不省了。
头有些疼,要开裂似的。按说,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热闹欢乐的酒席上不能缺少我这个“主角”,即使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我也得硬着头皮陪到客人散席。但是,我实在灌得太多,只能失礼了。我趔趔趄趄地扶着墙摸进房里,像扳木板一样把自己扳到床上。迷糊之中,恍惚之间,我像那插上翅膀的天使信马由缰腾云驾雾地穿越开来。
小学六年,我不是品学兼优的“五好学生”,但也算是规矩本分的“红花少年”。初中开始,我就开始变了,变得不爱学习,变得顽劣,变得叛逆,时不时地逃半天课和几个调皮生到集市上游逛,隔三差五地打一场群架,动辄就躲到网吧消磨半天。我们这个地方,古代是驿站,交通便捷,离县城近,加上有贯穿几县的东顺河,码头文化也颇有渊源。所以,商贾集聚,富豪扎堆,随之而来的是劫富夺财的土匪、草寇应运而生。土改时,政府镇压土匪草寇达十人之多。1982年“严打”,一口气枪毙了六个流氓团伙头目,还有五个小头目被判死缓,至于被判十年二十年刑的虾兵蟹将不计其数,数都难得数过来。按说,杀也杀了,毙也毙了,判也判了,政府能用的法律武器都用上了,这里应该会变得“天下无贼”,清泰平安。差矣!这里的帮派、团伙不仅没有绝迹或减少,反倒像割韭菜般越割越多,好比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去了一拨又来一拨。这些年存活下来的“漏网之鱼”混到省城和县城,当上黑帮头目的不乏其人,他们将黑钱漂为白金,生意做得出奇地大。活生生的事例让有些老百姓认识到:原来做这行走这道也能脱贫致富发财发家呀!帮派林立,黑恶盛行,遭殃受罪的是老百姓。为了寻求保护,也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许多老百姓纷纷送小孩加入到黑帮之中。以至于我们这个地方流传这样的民谣:“上学苦,读书累,不如参加黑社会。”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之中,我从本分学生逐步演变为“问题少年”,初中学业基本荒废。
中考我只考了180分。其实,凭我肚子里的“货”,应该考不出这等水平,但我会蒙,也会偷看邻座的,会抄。父母看到这个成绩,并没有过多地责怪我。二老叹息半夜,最后作出一个重要决定:送我到镇里当通信员。早上,父母从鸡笼里捉出两只母鸡,从积攒鸡蛋的罐里拣出五十个土鸡蛋,带着我到镇上去找我的堂舅。堂舅当时是镇里管财经的副镇长,正在办公室里和人说事。父母到访,堂舅起身问:你们有事?
我不善言辞的父亲把我往前一推,有些结结巴巴地说:这娃儿好吃懒做,调皮捣蛋,不求上进,干活身子不壮,当兵体格不行,考学成绩不好,只能跟你一样,到镇上当——当——干部。父亲说完,坐在屋里开会的几个干部嘻嘻笑了。
堂舅脸色很难看,又不便发作,摆摆手推却道:我现在忙,你们先回去,以后再说。
哪里还有什么以后呢?老实木讷的父亲怎么也没想到,他实话实说的几句话,后来被社会上传讲,成为嘲讽镇干部的经典笑话段子。
谁家父母都望子成龙,我的父母亦不例外。显然我不是成龙成才成大事的料,但这不是我的错呀。用我们这个地方的比喻,砖坯子不正,窑壳子不好,又欠缺火功,烧出的砖理所当然又泡又松还不规则,既受不得重压,也经不起磕碰,只能混在众多砖块中,滥竽充数地占一地儿。我就是一典型的烧过了气的砖。父母经过半夜密谋,准备送我到欢哥的班子上去。进班子需要人保荐,父亲的舅老表胡良平就在欢哥手下,混得人模狗样的,还不错。我们罗家在村上是小姓,加上父母怯懦窝囊,所以在村上不仅没有“话语权”,而且还处处受人欺凌,地位比改革开放前的地富反坏右高不到哪儿去,只算没有捆绑上台插上标签被批被斗。父母认为,既然孩子读书读不出个人样,那就让他到“班子”里去争个一席之地。家里出个有狠的“锤把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至少可以重振家声保证罗家不受欺辱。
父母这次吸取教训,没有贸然唐突地领着我去找我表叔良平,而是把他从镇上请到家里,安排他坐上席,好酒好肉招待,好烟好茶侍候。临了,父亲指着坐在桌子下席的我,推荐道,你表侄儿今年十五六岁了,没长读书的脑袋,没有种田的身骨,但有一个优点,就是人长得还算机灵。我和你表嫂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交给你,让你带着他到欢哥的班子里去干,兴许还能干出点名堂。良叔看了我几眼,摇头道,这孩子好像还没发育全呢。加入欢哥的班子,今后要有出息,必须具备三样特质。首先,要有一副凶相。这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细皮嫩肉的,长相不够格。第二,要有一种血性,他这副样子,无精打采怏怏垮垮的,血性不够强。第三,要有强健的体格。他瘦瘦弱弱文文静静的,人家吹一口气就可以把他吹出几十米远,体格不够壮。听到这里,母亲苦着脸提醒道,孩子正在发育着咧,身子骨说长就长起来了。良叔喝口茶,解释道,到欢哥班子里去干,也是要有天分的,不是人人都能进去混的。你们家太顺眉清目秀瘦弱斯文,缺少霸气和匪性,即便进去也混不出啥名堂来。还是让他去读书吧。
父母精心为我做的两项选择,一个被堵上了门,一个被封死了窗。父母最后只能无奈地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送你上高中。虽然我痛恨念书,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我那分数不够高中录取线,父亲通过人找人,最后交了三万元的调节费,让我成为县城一所普通高中的“议价生”。
上学后,我冲着那三万元钱,夹着尾巴老实了几天。
那些数理题目深奥难解,让我生厌。英语单词繁杂难记,让我烦躁。沉重的学业负担,尤其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连轴转的劳累,让我受不了吃不消。唯一有一个征兆令我欢欣鼓舞:我开始发育了,身高从一米六猛地蹿到一米七还多,体重也由不到一百增至一百一了。我不再是“鼻涕虫”,也不是“少年身”,我成了堂堂正正的小男人:喉结鼓了,胡碴儿长了,声音也变粗了。最为重要的是,我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很快和班上一小撮入学分数考得比我还低的男生女生搅到了一块,并结成“同盟”。我们集体逃课后,到网吧上网,到KTV唱歌,到郊外游玩。班主任老师拿我们没辙,除了打电话通知家长到学校给我们一番批评劝阻外,再没有其他管教办法。家长一走,我们旧病复发回归原样。
在“同盟”中,有一个叫黄倩倩的女孩喜欢上了我。她比我大一岁,父母在省城做小生意,把她交给姥姥照顾。她长得很白皙很漂亮,是看一眼就招人喜欢的那种。我生在农村,或多或少地有些自卑,而她是我心里的“白富美”,我岂敢有那种非分之想。但她很主动,经常拉我单独行动,大方地给我买这买那,身子故意和我挨挨擦擦,亲昵地拿手给我捋头发扯衣角,有时还双眼带火地电我一下。我表面冷漠无动于衷,但内心滚烫快要发狂。我自惭形秽,故作冷漠地回绝:我配不上你。她嘿地一笑,说有啥配不配的,我喜欢你!你略带忧郁的气质,快要把我迷死了。
她的直率告白和漂亮可爱彻底征服了我。我无药可救地爱上了她。下午,她就带着我跑到她的家里,趁着她姥姥出去打麻将的当口,我们躲在她的闺房里,抚摸、接吻、嬉闹。当我情到深处难以控制强行要她时,她拼命抵抗死活不从。看到我闷头不语的样子,她劝慰道:我也想,也许比你更想。但我的这朵生命中最最珍贵的莲花,至少要等到你十八岁了才给你采撷。说完,瞅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强调道,十八岁成人了,你就会有担当能负责任了。细细一想,她说得不无道理,我也就慢慢死了那份强制夺岛的心思。
在我们爱得如胶似漆死去活来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个第三者。他叫马天磊,是隔壁班上的,和她同岁,长得比我高,身体比我壮,而且家里是开工厂的,明摆着,他属于“高富帅”。马天磊厚着脸皮向她表白,被她拒绝了,但马天磊贼心不死,又接连向她表白几次。烈女怕缠夫,她有些动心,并且瞒着我和马天磊约会了两次。
我是一个醋缸子,眼里容不下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其他男生厮混。我不能想象马天磊那双脏手摸她冰清玉洁的身子和他那张臭嘴吻她香气如兰的嘴巴的情形,比刀剐火灼还要让人心痛。我的自尊受到严重伤害,大声斥责她为什么要水性杨花脚踏两只船?她反唇相讥还击道:你还有脸责怪我?你要是强大一点,他敢纠缠我吗?有本事你就灭了他!我气吞山河豪气冲天地发誓道:行,你通知他,我要收服他!
她安排我和马天磊见面的时间定在晚上九点,地点在学校后边那片林子里。想到“情敌相见分外眼红”,想到“决斗场上方显真爱”,我的胆儿迅速膨胀到无限大。为了打有准备之仗,为了不重现普希金那样的悲剧,我跑到街上五金店挑选了一把长约半尺的带把水果刀别在腰间。表叔良平说我没有血性,我连刀都敢佩戴,并且准备拿情敌“开刀”,怎么没有血性呢?
我九点整准时到达操场边的林子里,刚一站定,马天磊从林子深处走过来,对着我的脸啪啪就是两记耳光,比大人打小孩的光屁股还要利落还要脆响。我捂着有些肿痛的脸,措手不及地质问道,你怎么能随便打人?马天磊理直气壮道,老子从来都是搬着拳头横着走路,就是要打你这个从农村来的“小土包”。谁叫你狗胆包天,居然敢和老子争抢女人。我毫不示弱地说,黄倩倩和我先认识的,是我的女人!马天磊不由分说一拳直击过来,我躲闪不及后退倒地,前胸像被捅出个窟窿似的疼痛不已。马天磊暴跳如雷地说,你这个“小瘪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告诉你,黄倩倩是老子的,盖了“钢印”。你再敢靠近她一步,老子就让你消失!马天磊一边说一边奔到我身边,在他那双穿着皮鞋的脚即将踏上我的身体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之时,我霍地从腰间抽出水果刀,用力刺向他的小腿。我听到了“啊——”的一声惨叫。在他弯腰去捂伤口之时,我抽出水果刀,迅速爬起身,跑到观战的黄倩倩身边。她惊慌地推了我一把,说,你杀人了,快跑!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机警地跑出学校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