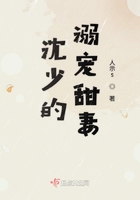史国说:“如果传出去,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咱们就会有大麻烦,当下正是你我的关键时期,虽然现在到处都说作风问题不是问题,但对于咱们官员来讲,作风问题依然是重要问题,而上面对于这类问题是从不需要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样的证据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储贤达点点头说:“明白,市长放心,翻不了天,压得住。”
储贤达盯着史国,心里窝火极了。倘若在平时,史国和他说话说到“咱们”“你我”这个份上,那他会感激与欣慰的,可现在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史国调到云水市时,他已经做了一任办公厅主任。史国做了代理市长后,却表现出了想换他的意思,曾暗地里物色过几个人选,和书记沟通时,书记说不急么,马上换届了,到时候一并调整。新官上任更换老的班底,把譬如秘书、司机,包括秘书长、主任等贴身的人换成自己人,在政界这像法律法规一样正常。但是,史国调到云水市起初是常委、常务副市长,作为办公厅主任,虽然史国不是他服务的核心,但史国将来接市长的势头很明显,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明白。因此,在史国身上他投入精力可以说超过了市长,竭心尽力,小心呵护。可史国做了代理市长却要换他,这说明他赤诚忠心地几年服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能不窝火?但他窝火也只能窝火,官高一品压死人,等级森严的官场就是这个样子。
史国说:“贤达,这事不简单哩,你必须给我一个圆满的交代。”
储贤达说:“明白,市长放心,我会处理得让您满意。”
史国挠挠头说:“这事不可以掉以轻心,风起青之末,尤其是如今的微博可不是一片净土,更是不可小视。”
储贤达已是两届的办公室主任了,马上要换届,肯定是要动,可是动得好与坏,史国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可史国至今未跟他谈过,这时间史国说“当下正是你我的关键时期”,显然是一种暗示,却又带着胁迫的味道。他也只能表现得更诚恳和虔敬。
史国站起来说:“山区农民嘛,小农意识,你去处理处理吧,不要太强势,要笼络他们。”
储贤达说:“明白,明白。”
回到办公室,储贤达自言自语骂出一句“娘稀屁”,抽了一根烟,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程玉清打了电话。能管奶牛场的部门很多,之所以选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因为程玉清是他的妻弟,这种事当然还是需要亲信去办。要说他亲自跑一趟也行,大黄奶牛场是叶明川的,多年交情了,只是一方面他不想纠缠得太深,像史国这样善于运作的领导干部,是可以用前途未卜来形容,一旦倒台,难免会把他牵扯进去,虽然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但粘上了就是个污点,竞争对手就会拿这事做文章。官场就是这样,只要你在场,永不缺对手。市长牛八玉栽了跟头就把办公厅主任刘远达带进去了,因为有几个关键的暧昧的场合,刘远达都在。要说也真是滑稽可笑,主任本就是领导的跟班,职务所在,职责所在,但事出了,人就有话说,刘远达就落了个失察失职监督不力处分。这听上去就像是笑话,可到了现实中就是事实,一个跟班去监督领导,除非脑袋让门夹了。用人们的话说是上床打老婆,不想干了。尽力配合还尚嫌不够默契,你监督试试,不要说是监督,就是不同意才说了一半,人家就打发你走路了。只要刘远达一有机会,竞争对手就拿这处分说事,匿名信雪花一样,搞得刘远达很是郁闷,原地踏步一直踏到退休。另一方面叶明川至少有半年多没跟他联系了。叶明川以养奶牛起步,后来进入房地产领域,发展得如日中天。去年圈下一块地,想修改一下用途,通过他想请史国吃饭。他请过史国,史国却没给他这个面子,说过段时间再说吧。但凡这种事本就很敏感,史国以后不提,他也不好再说。可这个家伙竟然这么长时间不跟他联系。
程玉清来后,储贤达说,大黄奶牛场有一个送奶的瘸子叫徐富贵,拦了市长调研的车队,搞得市长下不了台,市长很生气,你告诉奶牛场老总,快点打发瘸子回乡下去。
尽管程玉清是自己的小舅子,但他也不能告诉真相。针尖大的窟窿进来斗大的风,少一个知情人就降低一个传播点,一个风源点,少一只蝴蝶的翅膀。一个事件能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了一个人。这件事对他无疑是一个考验,事关他下一步前程。他不能马虎,官场是高度敏感的,敏感得都有些小心眼儿。所有史国才用了蝴蝶效应。
程玉清要走的时候,储贤达对程玉清说,带上点钱,尽管他采取的方式有些偏激,但终归是农民,一个农民从山里来到城市讨生活,委实也不容易,怪可怜的,不要威逼强迫,别生事端。又说,不过,大黄奶牛场是该给点教训,出了这种事,他们是难辞其咎的,找个三聚氰胺什么的借口,搞出点声势来,对市长也有个交代,市长可是盯着这事哩。
4
就像那电视名儿——《幸福来敲门》,徐富贵已经听到幸福的敲门声了。他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已经看到天光了。儿子徐鹏明年参加高考,按老师说的,重点大学没大问题,要是发挥得好一点,上北大、清华甚至是拿个状元也是很有可能。这就意味着再有一年,他也就从苦水潭底爬上岸来了,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段大段的好日子。徐富贵心里说,水秀啊,你看着吧,我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真真的。
徐富贵一头扎进南窑肚儿里就是五年,正如那歌唱的,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从南窑肚儿里爬出来,从银行取出五沓新崭崭老人头,他就直奔章家台去了。任福娶媳妇时请他催箱娶人。任福媳妇的表妹水秀是陪娘,他就盯上了水秀,也把水秀家里的情况摸了个清楚。水秀哥哥强子娶不上女人,又好吃懒做的,不出去打工,就在家里祸害,在镇上耍小姐让警察捉住了,捎回话来让拿钱赎人,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找对象就更难了,水秀爹又羞又气,决定用水秀给强子换个媳妇安顿了事。水秀一直在城里打工,捎话带信叫不回来,水秀爹上吊抹脖才把水秀从城里逼回来。换亲还没探访到合适的茬口,他背着钱上门提亲,水秀爹是杠木做的擀面杖,直来直去,说强子把媳妇娶到家得五万,我多你一分钱都不要你的。他把五沓票子压在了水秀爹眼前。水秀爹怕夜长梦多,说就这个月吧,翻黄历看个日子,把亲事抓紧办了。这样没出一月,他就把水秀娶到了家。新婚之夜,他知道水秀有多么的不甘心,在城里打过工的女娃谁甘心嫁到这里来,或许哪天就不见了,这几年村上跑了媳妇的不少。因此,他是既要扒光阴,还得守着水秀,过得提心吊胆。两年后,水秀生下了徐鹏,他心才落下来,就想着水秀不会跑了,要跑就不会给他生娃了。娃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疙瘩,是最能拴住女人的。儿子生下的第三天,他就宰了一只公鸡,烫拔煺洗,开肠破肚,拾掇干净,提着去找小先生给儿子起名。村子里许多娃都是要上学念书了,才寻先生求大名。
小先生是来支教的,年纪不大,名牌大学生,学问大着哩。小先生问他想要个啥意思的名儿。他说和别的娃不一样,有点意义的,想想又说别老是富呀福呀财呀宝呀贵呀的,我爹给我起名叫富贵,光村子里就有五个大名小名叫富贵的,日子都过得寒寒苦苦的。李庄、周滩、芦花台叫富贵的也不老少,有一回我去草鞋镇赶集,听得有人喊富贵,我应了声,不远处也有人应了声,结果,人家喊的还不是我们两个。又说我徐家一辈两个字一辈三个字,这娃轮到两个字了。几天后,小先生就把名字起好了,徐鹏,给他解释说鹏是传说中最大的鸟,一展翅膀就是几千里远,有一个词叫鹏程万里,就是说前程远大,不可限量。他扑棱扑棱着一双眼睛听着。小先生又说,李鹏知道吧。李鹏他当然知道,总理,大人物。这样,儿子就是村里最早有官名的,儿子的名字也让他有了一份寄托。
一天晚上,他正在吧嗒吧嗒抽着烟,水秀坐在一边给鹏鹏打毛衣,鹏鹏就在他们中间爬来爬去,他就说砸锅卖铁也一定要把鹏鹏供养成个读书人,书读下了,鹏鹏就是城里人了。水秀手里的竹签儿停顿了一下,他得到了鼓舞,继续说,鹏鹏的书啊一定要到城里去念,咱这旮旯儿能念成个啥书,多少年了考上了几个?水秀从儿子身上收回目光看了他一眼,他就说不能老待在家里了,有个苗儿就不愁长,你看娃一眨眼长一截,一眨眼大一圈。你在家里带鹏鹏,我得出去揽活挣钱,攒点钱。这么说着他心里就很冲动,一翻身坐起来说,我想还是到煤窑揽活,苦虽是大了些,可来钱快么。煤窑背煤一年下来咋也落个一万块,除了咱们一年的搅销,咋也落个七八千,从现在到鹏鹏念完小学咱就当十年算,也七八万哩。有七八万垫底,鹏鹏就是考到外国去,咱们也供养得起。
这么说着他用眼拐拐观察水秀,水秀打毛衣是有一针没一针的,显然是在听。他就接着说,等鹏鹏把书念成了,在城里有了工作,咱们在城里就把根扎下去,那时候我五十出头,正是揽活的好年纪,到时候,我揽活,你就在家里做饭、领孙子。像我揽活揽到六十多岁没麻达,咋也能攒下十来万,咱们不靠儿子养活,两个人么能吃多少,能穿多少?日子也就改换了。
话虽然是说给水秀听的,却把自己也说灵醒了,也说急了。日子就该是这么个走法,不能再在家里待下去了,得像以前铆足劲儿挣钱娶水秀那样扑腾日子。再这么守着水秀,日子可就真要落后了。他跳下炕去,翻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人造革小黑包递给了水秀,家里所有的积蓄、土地证、户口本,还有水秀的身份证都装在这包里。外父怕水秀守不住逃跑了,把身份证给他压着。过日子么,就过得个互相信任。再说城里啥假证办不了?身份证扣下就能把人扣住?反而把心弄生分了。
水秀没有接那包,却噗地一口吹了灯,钻进他的被窝。这是水秀第一次钻他的被窝。他心里一漾一漾的,眼泪流出来了,搂着水秀一个劲儿叫着我的天神我的水秀啊我的水秀我的天神啊。
日子就这么顺溜了,鹏鹏一岁生日到了,水秀做了很丰盛的一顿饭菜,还备了一瓶酒。徐富贵心里熨帖啊,嬉笑着说娃过生日,你还给我准备啥酒么?水秀不喝酒,一股劲儿要他喝。结果一瓶酒让他喝光了。第二天早上,鹏鹏在哭着喊着叫娘,他睁开眼四下看看,就知道水秀走了。
要不是有了儿子,他会去城里找水秀,找着了,要回来一起好好过日子,要不回来那就都别活了,要人的命还不容易。可有了儿子,事就不能这么做了。两个月后,他背着徐鹏上了外父的门。外父见到他哆嗦着在院子里转圈圈,双手就像两片干裂的榆树皮,搓出哧啦哧啦的声响。他并不想和外父起事,说到底老汉也是个被日子逼在墙旮旯的苶障人。那五沓子一弹一甩“咯咂”“咯咂”的新崭崭的票子已经变成了强子的媳妇,想要回一分钱都没可能。他是来续这门亲戚的,他把事情想透了。如果水秀没给他生下鹏鹏,水秀一走,这门亲戚也就断了,说不定他还会生出事来,拉牛赶羊吆猪装粮的事也做得出来,理在他手里攥着。可是有了鹏鹏就不一样了,水秀走了,是不是他的女人说不清,但是鹏鹏的娘这点改变不了,老汉是鹏鹏的外爷也改变不了,对于鹏鹏来说这是这辈子钢刀割不断的血缘。
水秀走了,把他的筋骨全抽了,也就把日子的筋骨全抽了。以前日子是站着的,走着的;现在的日子是躺着的,爬着的。带着鹏鹏过着孤儿光棍的日子,再没啥负担,日子也悠闲着哩,可老这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日子过得不得劲,不得劲其实就是恓惶。白天没人做干粮,黑夜没人搭声腔,歌里都这么唱哩。除了风摇门穗子,小鸟儿找不着窝叫两声,再就连个声响都没了,咋能说不是恓惶?酒倒是个好东西,日里多喝点,一天就晕晕乎乎过去了;晚夕多喝点,一夜就晕晕乎乎过去了。鹏鹏倒不孤单,学校就在旁边,成了鹏鹏的天堂,迟早喊鹏鹏,鹏鹏就从学校里冒出来。
那年,唐家坪来了个女先生。女先生是考上特岗分配到唐家坪小学的。有一天,女先生跟他说你儿子就像上过一年级了。说着让他看几页纸,他一看密匝匝写了整整三页,说都是我儿写的?女先生说我让他写的。他迫不及待地问徐鹏将来能考上大学么?女先生笑笑说好好念考个重点也不成问题。他跑到小卖部买了书包、铅笔和本子,说让鹏鹏也上学吧。女先生说,才几岁啊,上学前班的年龄都不到。他说你说这字一笔一画写得差啥,上一年级保险跟得上。女先生说书不是这么念的,一旦上了学,就得一级一级往上跟,年龄太小总有跟不上的一天。女先生又说就像你种地,到了种啥的时候种啥,总不是啥时想种啥就啥时种吧。他一想也有道理。女先生说就让这么跟着吧,当上学前班。他回去提来十几个鸡蛋,女先生要掏钱,他说你都是鹏鹏的老师了,拜师得有礼,以后园子里的菜,树上的果子,想吃啥你随便,反正我爷儿俩也吃不完。女先生说你现在就得给鹏鹏攒念书的钱了。第二年女先生就走了,临走给他说一定要培养徐鹏读书,考上大学你们父子命运改变了,你总不希望徐鹏以后走你的老路吧。这是掏心窝的话啊,他诚恳地点着头。
第二日,他就把儿子送到外父家,又下了煤窑。下过煤窑的人就再不愿揽别的活了,别的活挣钱少,没劲。下煤窑背煤当然危险,那五年出过三次事,有次他给埋了几天几夜,给挖出来就剩下皮包骨了。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不后福他不敢奢望,但他相信事不过三。然而,事不过三只是一句话,又出事了,这次老天爷没眷顾他,他被煤块砸折了一条腿,胯骨粉碎了,在医院养好就成了瘸子。不过,老板很爽快,拍给他三沓老人头,加上两年挣下的,他又揣着五沓老人头回来了,正赶上开学,就把鹏鹏接回来送进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