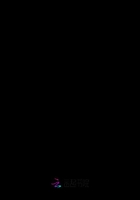“这裕王府怎么这么大啊……”
月明如水,天色如墨,而这花朝月夕之景,花袭月却快步走在凉风中,而且,她非常幸运地。
迷,路,了。
呵。
真不知道是该说自己笨,还是说自己……蠢。
刚才自己出来的时候还有几个婢女小厮的,这怎么出来之后就没了……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
难道自己今天要睡花园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啊!
但是我要怎么回到自己的小破院。
花袭月试图想找一下聂北裕,于是乎就在这里绕啊绕啊绕,到最后发现自己是在原地打转。
花袭月已经要绝望了,这怎么越走越糊涂啊……
“早知道刚才就应该跟着聂北裕了……”花袭月吸了吸鼻子,夜里的冷风带着一股浓重的湿气,花袭月穿的单薄,没走几步道就冻得受不了了。
“聂北裕……我记住你了!”花袭月蹲在花丛后面,委委屈屈地怨怼着。
“好,好冷……”花袭月不停地搓着手,想借此汲取一丝温暖,看着高高挂在夜空中的明月,眼底氤氲出一层水雾。
阴冷渐渐绕满了全身,意识开始模糊,
落慈睡不着觉,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花园。
“王妃,夜里凉,我们早些回去吧。”婢女婉儿将雪貂大氅轻轻披在落慈肩上。
落慈淡淡笑了笑,“我不冷,我只是……想出来走走,透透气而已。”
婉儿闻言,只得乖巧地点点头,跟在落慈后面。
“王妃!你看那里有一个人诶!”婉儿惊讶地看着躲在花丛间的花袭月。
“嗯?”落慈温润的眉眼染上了一丝不安,和婉儿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冷……”花袭月喃喃呓语着,眼前的景象也模糊了起来。
“你没事吧?”落慈一看,也顾不得其他了,急忙上前问道。
“嗯?”花袭月迷迷糊糊睁开眼,落慈温柔的眉眼映入眼帘,不由得抓住了落慈的手,颇有些神志不清的样子:“冷……”
“啊?”落慈手上一阵冰凉,花袭月的手握着她的手,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落慈摸了摸花袭月的额头,烫的吓人。
听清了花袭月说的话,将披在自己肩上的大氅解下。
婉儿着急了,拦住落慈的动作:“王妃你这是要干什么?”
落慈皱了皱眉:“她冷啊,这夜里风这么大,你难道要让她就这么冻着吗?”
婉儿不情不愿地说:“外一这人手脚不干净呢?我们又不认识她,说不定她是进府偷东西的,王妃我们快走吧!”
落慈眉头紧蹙,挣开婉儿的手,将大氅披在花袭月身上,裹了裹:“婉儿,你怎么能这么想,快帮我一把,她好像有些受风。”
婉儿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过去,帮着落慈将花袭月扶起来。
花袭月迷迷糊糊之中,身体暖融融的,一股馨香在鼻尖萦绕着,但是又好像漂浮在空中,无所着落……
“爹!爹……”
一时之间,火光冲天,嘶嚎声,打斗声,不绝于耳。
一帧帧鲜血淋漓的画面在自己眼前飞速略过,血流成河,白骨如山,凌乱的脚步声,嘶吼声交织成一篇禁忌冷漠的咒文。
“锦儿,活下去……”
滚烫的鲜血溅了年幼的华锦半边脸,眼泪好像都是血红色的,手起刀落之间,爹的身体死死护住自己,鲜血染红了自己的衣裳……
“爹!”花袭月从梦靥中惊醒,额头上满是汗珠,后背湿了一片。
落慈靠在一旁睡着了,听到声响也悠悠转醒:“你醒啦?”
花袭月身子仍是有些虚软,看着这个温雅润玉的女人,莫名生出了几分好感,想起貌似自己昏迷的最后一刻看到的人就是她,勉强支起身子:“谢,谢谢……”
落慈急忙扶住她,浅浅笑着:“快躺着,我已经找大夫给你看过了,你身子虚,又受了风,所以才会发热的。”
“谢……咳咳咳!”花袭月还没说什么,嗓子便泛起一阵阵的痒意,咳起来还有着疼。
啧,这床也太软了,可比自己那小破院好多了……
“王妃,药来了。”婉儿端着瓷碗走来,递给落慈。
“来,这是大夫给你开的驱寒的药……”落慈将药接过来,用勺子搅弄了几下,笑意盈盈地看着花袭月。
花袭月看着色泽……一言难尽的汤药,咽了咽口水,又看着落慈温柔的眉眼,咬了咬牙,接过来一饮而尽。
落慈嘴角的笑意更大,将帕子递过去,花袭月也就顺便擦了擦嘴。
手帕也好香啊……
“说,你究竟是何人?为何深夜出现在裕王府花园!”婉儿疾言厉色,给花袭月问得一愣。
“我……”“婉儿!”落慈眉头一皱,“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王妃教训的是!”
婉儿草草行了个礼,心不甘情不愿地站在一旁。
花袭月一怔————
王,妃?
“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这几日,你就在此安心养病。”落慈站起身,笑意晏晏道。
“王……”花袭月叫住了落慈。
“嗯?”落慈回头,依然笑着。
“您是……裕王府的……”“王妃!”婉儿抢先一步道。
“聂……二皇子的正妃?”花袭月试探地问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婉儿不耐地说。
“婉儿!休得无礼!”落慈温润的脸上浮现了一丝愠怒。
“王,王妃,您别多想,我就是问问而已。”花袭月知道自己冒然开口很是冒失,但是……聂北裕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有个王妃啊!
“没事,好好休息吧,养好伤再走。”落慈不在意地道。
花袭月的脸色有些复杂,我到底该不该跟这么善良的女人说我就在最偏僻的小破院里住着啊……
“唉……”花袭月呈“大”字形躺在床上,放空自己。
……
“二皇子,陈太后……”管勒眸色复杂地看着翻阅账本的聂北裕。
“划拉划拉……”
空荡的房间里回响着翻纸的声音,聂北裕的侧脸更显冰冷。
“这次江南布匹的事情,太后很认真。”聂北裕眯了眯眼,盯着账本上的每一笔账,最终停在了“江南布匹”的上面。
“那,结果如何?”管勒心里竟然有些紧张。
“啪!”聂北裕把账一合,靠在椅背上,头疼地揉揉眉心。
“这事儿和秦家有关系?”管勒看到聂北裕的神情,心里也猜出了七七八八。
“秦家?难道是……”管勒心下一惊。
“这也许,是一个扳倒秦家的一个好机会。”聂北裕挑挑眉。
“但是这上面写的不是秦尚书的名字啊,交接人不是秦尚书,这人,我还从未听过……”
“嗯,而且,还是花袭月的老相好呢。”聂北裕说到这里,嘴角不禁勾起。
“花小姐?”管勒又一次吃惊。
“秦,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