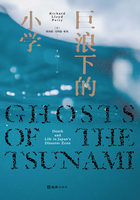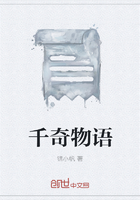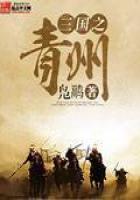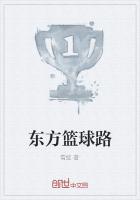现代高等学府中,校园风景可谓层出不穷,然而随着时光流逝,能成为永恒映像的,当属名师高徒的背影。从与李步云教授的交往到对他的几次采访,我更加认定了这一想法。
华灯辉映,晚风吹拂,静谧的大学城里,一位学术老人的谈笑风生给这座崭新的学术殿堂增添了另一番景致。接连3节课,近3个小时,72岁的李教授一直站着,在学生与黑板之间来回走动,讲起他耕耘大半生的人权法学,滔滔不绝、神采飞扬。这一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在正式上课之前,我要感谢大家对我这门课的支持……”拳拳的情意、谦逊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大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人文学院一名女生课后对我说:“开头那几句话让我很感动,想不到一名大师竟是如此谦和。”一家媒体的记者专程来学校听了一次课后深有感触:“70多岁的老人还能这样给学生讲课,真是令人敬佩。”
作为一位被誉为“中国人权法第一人”的大师级学者、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李教授本可以只做学术研究和带博士生而不需担任本科教学任务,但他主动提出给学生主讲人权法学课,从桂花岗校区到大学城校区,晚上授课,不辞劳苦。是什么促使他走上讲台?在他两年前所写的《七十述怀》一文中,我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诠释:“教育部只要求五十岁以下的教授必须上本科生的讲台,不少人也劝我不要太劳累,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因为我从课堂上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神中能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我先后担任过十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为省部级和地市级单位的领导干部作学术演讲一百多次。我不会忘记那一个个连续三小时不休息、上千人凝神静听演讲的感入场面;不会忘记那一阵阵掌声中所传递出来的渴望法治的信息。我感谢那成千上万听过我上课和演讲的满脸稚气的学子和白发苍苍的将军,让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追求法治理想的勇气和力量。”翻阅这段话,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在讲台上的风采,我对这一问题有了另一种顿悟:那是一名老教授对学生的无私关爱,一名大师对自己专业的无尽追求。
李教授一生经历坎坷,颇具传奇色彩。他曾在朝鲜战场上身负重伤,退下战场后考入北京大学,走上法学研究和教学之路,50多年来,硕果累累,桃李飘香,享有盛誉。翻阅他70寿诞时学界同人、同事友人、门下弟子为其撰写的纪念文章,让我更感动的是其中对他为人为师的崇高情怀的诸多赞誉。现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的信春鹰教授写道:“熟悉他的人谈到他的为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那是一个大好人’。”曾于1979年与他联名发表文章《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的著名学者徐炳先生评价他说:“‘人’在他心目中,始终是大写的,不能马虎的,在人权理论上如此,在实践中也是如此。”
关于大学,梅贻亭先生的一句名言大家都很熟悉:“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想起那天晚上去大学城的路上随车采访李教授时,他不嫌烦琐倾心而谈的情形,想起准备离开大学城时,他不计亲疏嘱咐司机送我回家的情意;想起去他家送稿时他倒水沏茶热情招待的情景,想起他惠赠大著时亲手题签的专注,心中油然而生感激和敬意。如果套用上述名言的句式,我想说:“大师者,非仅大学问之谓也,有大情怀之谓也。”
有这样的大师,应为“广大人”的自豪,能与此大师往来,实乃吾等后生之幸事。
(2005-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