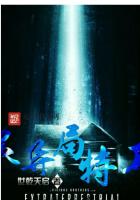所长走马上任的时候是那年的八月。满市场百十户商家四五百口人,来来往往的数不清道不明的男男女女就都成了他的管理对象。
一桌、一椅、一个没有了盖的鞋盒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桌子是坏了一条腿的小方桌,那条坏腿用铁丝箍着,放在地下总也放不稳当。桌面没有漆过,但因为年代久远了,也黑的发亮;椅子是缺了几张竹片的躺椅,夏天了把椅背放下去就是凉床,冬天了把椅背板上来放个棉垫子就是沙发。那个放在桌面上的鞋盒是装钱用的,里面总可以看到五毛、一块的毛票。
我们看到的所长个子不高,走路弓着背,喜欢穿一件长过膝盖的黑色皮上衣,大西服样式,上面总是蒙一层细细的灰。灰白间杂的头发下是一张沟壑纵横的脸。这张南瓜一样凸凹不平的脸上总是很严肃的样子,从来没有见到如油画里老人灿烂的笑容。
准八点,所长就用那辆短把的架子车把他的桌子、椅子、垫子、盒子、扫帚、铁锨拉来。先喊一句,女的那边有人没?没人应声,就拿了扫帚进女室。往往就有女人锐声叫,你是瞎子嘛!没看见有人?所长就讪讪的退出来,嘴里叽咕,我喊了的——其实那天早上他忘了喊。退出来的所长就没有了话,进男室,把废纸篓全部恨恨的倒过来,用扫帚把那些脏纸按进蹲坑前面的脏水里,一下一下的扫到门口,再用铁锨铲出去倒进垃圾箱。有时候,化粪池满了,厕所里的污秽物就出不去,上厕所的人就喊,所长呢?所长眼睛瞎了!光知道收钱不知道打扫卫生。
所长眼睛没瞎,所长年龄大了,掏化粪池这样的活所长干不了。干这个活的是所长的儿子,那个蹬人力三轮车的小伙子。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给父亲面前一站,整整高了父亲半截。说话嗡声嗡气的,放到解放前,也许是个当兵的好料,现在只能蹬三轮下苦力了。用所长的话说那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来到厕所前的化粪池,用一根刚钎插进预制板的缝隙,嗨!嗨!只两声,预制板就乖乖的挪位,不到半个小时,问题就解决了。
大多时候,所长就坐在竹椅上,放钱盒的桌面上是一副花花绿绿的扑克牌。所长对面坐的是穿黄马甲的老女人,负责这一片马路卫生的。另外两边坐的人就常换,有市场的闲人,也有退休干部。一毛、两毛的注,小赌打发了时间,买个乐和。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吧,所长变成了老所长后,人们却再也见不到那个矮个子老头了,听说他去东街小学当了门卫,有人就叹息,这个老头,这个所长的官衔虽然不大,称呼虽然不雅,可收入不菲啊?一天五十,十天五百,一月一千五,一年一万八,抵得上一个小干部的工资呢!
老头听到人们背后喊他老所长时就意识到有一个小所长诞生了。老头有一个孙子,上小学三年级。孙子放学替换爷爷回家吃饭时就坐了爷爷的椅子,叼了爷爷的烟,拿了爷爷的牌……俨然是一个小所长,时间长了,竟染上了赌瘾,学也不好好上了。
那天老头吃过饭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亲眼目睹了小所长的做派,本来就黑的脸更是气的乌黑。老头走近他的小方桌,没说一句话,就抓了桌上的牌,也不看那个穿黄马甲老女人的惊讶的脸,转身进了厕所,把花花绿绿的牌仍进粪坑。老头再回到桌前时,那三个大人已起身离开,老头只一脚,小方桌的那条断腿就彻底的断了……
市场没有了老所长,也没有了小所长。当然了,所长还是会有的,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