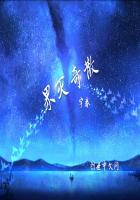大总管我们都叫他绑牢,他自己呢,喜欢写做永贤,当然是在需要用笔来写他名字的时候。比如,村里过红白喜事的桌面上,二指宽,一乍长或红或白的纸条上就是“吴永贤”三个字。
大总管的父亲在世时,也是我们吴洼村红白喜事的总管。在我们吴洼村,结婚盖房、老人过寿,孩子满月、周岁是大喜事,是红事;老人过世,头周年、三周年是白事。常言说得好,娶媳妇盖房,大家帮忙。可这帮忙的事总需要一个着头的人啊!这个着头的人就是总管。这总管也不是从村里随便拉出来一个人就能当的,能做了总管的人在村里要有一定的威信,要全村百十户人家服你才行。
那时候,人们生活都艰难,谁家过事了,来客就真的是坐“席”,拉几张用芦苇编的晒粮食的席子铺在院子,上几碗白菜萝卜、荤菜就是用萝卜丝炸的咸丸子,用蒸红薯炸的甜丸子。捞饭呢,是用高粱米做的黏饭。这样的总管好当,就是招呼个来客,安排个端饭上菜。
绑牢当总管的时候,已经到了上世纪末,过红事有彩车,有摄像,过白事有灵棚,有响器班子,来客再也不会席地而坐了,有四条腿的方桌和四四一十六条腿的四个条凳。
过事的头三天晚上,主家必要到自家屋里(爷爷的爷爷这一门里的子孙)家家门上,拿了烟,把男人都请到家里,备了酒,备了菜,边喝酒边说事。主人说,过事哩,要请自家人都来帮忙哩。绑牢就喝一口酒,接了主人的话说,太阳从家家门前都要过哩。过事就凭的是自家屋里人。咱都辛苦些,把这事过好,不要让人拨弹,也不要让吴洼村里人笑话。这几句开场白说过,就开始安排任务,自家屋里人每家都要拿来一张桌子,四个条凳,自家没有就去村里借;谁谁谁找八个上菜的方盘,谁谁谁找八个端饭的盆子,谁谁谁负责发烟,谁谁谁负责倒酒,谁谁谁负责担水,谁谁负责上汤……安排好了,绑牢就会用随身带的笔列出名单,拿在手里扬了扬,说,白纸黑字,到时候要兑现哩。
过事那天,绑牢迟迟不来。主人拿烟去请了,他才姗姗而来。只有在这天,绑牢才穿上他从县城买的四个兜的黑色呢子制服,左上兜里插支黄铜色笔帽的钢笔,头戴一顶深灰色的军便帽,给院子一站,威风十足。边上就有人就说,呵,大总管来了。
大总管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院子里的桌子贴纸条。红事用红纸,白事用白纸。谁的桌子贴谁的名,桌子、凳子要物人对证,然后就是检查方盘拿来没有,端饭的盆拿来没有……小学都没念完的他为了写给桌子上贴的纸条,硬是练出了一手能看入眼的毛笔字。
吴洼村的另一个人物是吴展鹏,不到五十岁就做了县上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吴县长的父母年龄大了,住在老家三间土房里,种三分自留地,常年有新鲜蔬菜吃,硬是不去县城住高楼大厦。话说这年的十月,吴县长要给他的父亲贺七十,厨子是从县城请来的,乐队也是县城最有名的双胞胎乐队,摄像是电视台请的专业摄像师,按说,这样气派的过寿是吴洼村从来没有过的,可过事那天,刚刚开始就乱了套。不是有桌子没凳子,就是饭都上来了,菜还没上齐。这时候,才有人说,大总管呢?咋不见大总管?
吴县长就纳闷,什么大总管?
本家叔父就问他,你没有请绑牢啊?他可是咱们村红白喜事的大总管啊!他来了,一切就都顺了。
吴县长就想,我堂堂一县之长,全县四五十万农民都是我管哩,竟管不了一个几十人的过事摊子?但面对这个一时失控的局面他还真是不知如何着手。
吴县长终于还是拿了烟去请了绑牢。
穿戴整齐的绑牢给院子里一站,大总管的威风就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谁谁谁的凳子没拿齐,赶紧给我回家取去,我知道是谁耍奸哩!谁谁谁做端饭的头,谁谁谁领上菜的班,给我好好看着席面上,出了事就找你俩哩!
说也怪,大总管给那儿一站,凳子也齐了,端饭上菜的也秩序井然了。
吴县长心里暗暗说,真是县官不如现管啊!
过了几年,村里有一个年轻人叫吴俊的,从南方打工回来,冷不丁成立了个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公司,桌登、乐队、厨子、服务员全程提供。吴洼村方圆几十里的人家过事都来他的公司联系,人们再也不需要请自家屋里人帮忙,也就再也不需要大总管了。
绑牢一下子失去了大总管的身份,那身呢子制服就不见他上身了。不到半年,绑牢就明显的老了,背驼了,头发花白了,说话也中气不足。
这一年的春节,已经从县长位子上退下来的吴展鹏轻装简行回到吴娃村老家。父母已经去世,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三间土房,吴展鹏回想自己一路走来的仕途,轻轻的摇了摇头。
绑牢恰好路过这儿看见了这一幕,心下顿时释然。他走过去,和吴展鹏打了个招呼,说,老弟啊,你回来了……回来了好啊!回来了好……言毕,大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