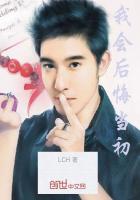高中时期唯一愿意凑上来亲近我的人,是我其貌不扬的后桌。
晌午,习惯了一个人用饭的我,一边看复习书,一边不专心地喂自己吃饭。这时有一个人把盘子端过来坐在了我对面。他八卦地说,听说你是我们高二出了名的坏脾气,独来独往,孤僻古怪。
一听此人说话,我连理他的欲望都没有。
我看着复习书,吃了一口随意舀起来的饭菜,却吃到了好几片瘦肉,我感到奇怪,把视线从书上挪开。才发现坐在对面的是班里的男生,还是个不怕被克,不怕晦气,偶尔会和我搭话的后桌。
他笑容和煦,又夹了一片瘦肉给我,分外自来熟。“我不喜欢吃瘦肉,而且戴过牙套,瘦肉卡牙缝,你的肥肉可不可以给我吃。”
我抖掉了他夹来的瘦肉,并且一调羹打飞了他企图伸过来的餐具。他把地上的调羹捡起来就着衣服擦了擦,继续若无其事用饭,他见我将肥肉都嫌弃地挑在一旁,便嘟哝道:“你又不吃,还不给我,浪费也不给我,太倔了吧。”
“我的东西,我有权选择处理方式,既然知道我脾气坏,不跟人相处,识相一点,端起你的盘子,左右随意。”
他愣了一下,赖皮笑了,“那这位置总该不是你的,我也有权坐吧?”他咧嘴的样子像一只呲牙的大嘴猴,他问道:“你怎么不爱笑呢?平常清清冷冷的,不怕把自己给憋坏啊?”
我不太耐烦,“我如果爱笑,你一定又要问我,你怎么这么爱笑呢?”
“以前我以为他们孤立了你,现在我发现是你孤立了所有人。”
“蠢货,是我远离了那些傻缺。”
他说一句我总能将他堵死一句,他渐渐没了话,终于还我一片清净了。我和后桌虽交集浅浅,但记忆有些深刻。
隔几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省城里拉起尖锐刺心的防空警报,听着那一阵儿一阵儿的警报响起,心头慌慌的,虽不能亲眼目睹祖国历经沧桑的过去,然防空警报带给了我身临其境的惶惶感。
全班站起来默哀时,一个绰号叫大马猴的男生仍在最后面嘻嘻哈哈,没有丝毫敬畏心,始终沉迷于自己讲得低俗荤笑话。
除了班主任几声提醒,没人制止他,甚至有废物与他同流合污,笑啊,闹啊,在这肃静庄重的气氛里,他们脸上却盛开比鲜花还要灿烂的笑容。他们也许根本不明白何为九一八,又为何要纪念,为何要默哀。
我转过去对他们说,把你们的嘴闭上,把你们瘫痪抽筋的丑脸给控制好。
其他同学纷纷看了过来,大马猴似乎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看了看同学们,迅速挪几步过来,抬手响亮地扇了我一巴掌。
班主任气得连拖带拽将大马猴拉出去之前,后桌已先制住了人。
我当时没有立刻还手,直至防空警报响完,默哀结束以后。见窗外的大马猴不知悔改,拽模拽样推搡着班主任。我提起一把椅子出去拼命地砸他,为了九一八事变里的中国亡魂,为了老师被践踏的那份尊重,也为了连爷爷也舍不得动我一下,而遭受渣滓的那一巴掌。
大马猴疯了似的扑上来揍我,我何曾怕过谁?也不要命地撕打他。
班里统共几十个男生,除了后桌和班主任,没有一个上来拉架,皆一副看好戏的态度。他们差不多都是一类的蛆虫,一起孤立我,编造我克夫,时时开玩笑恐惧的将我推给彼此做老婆。这其中有偷拍女生换衣服的,进女厕所的,嚣张抢钱的,嘴里说要捅老师的。我并不觉得不合群的我是异类,只是身处混浊的环境,我也不愿意和他们相处,总有一天我会因为自身的坚持而被上放到我想要的环境里,那些人也会像泥垢一样被漏网过滤掉地下道里,流入更黑暗肮脏的地方。
然而这么一架,落实了我坏脾气的外号。一位高姓女生甚至谴责我思想极端,不能理解我以暴制暴。老实说我也不理解默哀时她不制止大马猴嬉笑,事后不去谴责他,而是马后炮来与我说教。她想要说教,监狱里一排排罪犯多的是,谢谢她,请放过我们当事人。
我愈加凄凉了,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和粗暴的我做朋友,平常也不敢和我多说一句话。
至于大马猴的后续有些戏剧化,他跟我打完这场架,又在学校里施暴和后桌打了一架,加上之前有几次聚众斗殴的案底处分,他在我的盼望里顺顺利利的被学校无情开除了。
我热爱母校。
后桌那一次的恩情我记下了,愿意以友好的态度同他做朋友,并且餐盘里从此以后的肥肉,尽数赠予他。然后我得知,他初中因为戴昂贵的牙套被没见过世面的同学孤立过,绰号钢牙哥。换了新学校,终于摆脱了厌烦的绰号,他也不喜欢跟俗不可耐的大众相处。他向我普及了牙套的好处,喜欢将整齐的一排牙露出来给我欣赏,刷一下笑得格外标准,那洁白的八颗牙真真儿闪着光亮。
整牙这样的小整形,使我联想到八喜曾经吵闹着要整容,她从一个时髦的魔都人那里听来整容这件神奇的事情以后,向家里闹了有两年了,而这个寒假里,竟不想她果真大胆做了整容手术。
八喜妈成日唉声叹气,在我家做客的时候,不停的用手背拍着掌心,与我爹磕话说,把八喜惯坏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死丫头如何也不听啦。大人的烦恼也就孩子那点儿叛逆,可他们从不去了解一个孩子的内心。
他们聊天时,我不经意间记下了医院的地址,也就百无聊赖的时候,晃去了那家医院瞧瞧鲜,终于寻到她的病房后,我并没有进去笑她,只是贴墙侧站在门外,无声无息地挪挪眼睛看看她。
她果然割了双眼皮,眼睛水肿得跟女鬼一样,似乎也削尖了下巴,整一个猪头形象,又肿又血淋淋,白纱布上渗了些血迹,也有发黄的药物。她眼睛几乎不能睁开,仍忍着剧痛,低头看看以前的照片,盯向自己原本的模样,忽喃喃道:“什么特色?”
她又自言自语地说:“特色二字太深奥,庸人哪里懂,我只知道,不符合大家的审美,他们会说我又胖又丑,背后叫我眯缝眼,大脸,肥婆。”
也不知她看清了原来的自己没有。
接着,她不舍地放下了照片,过一会儿,手里又眷恋摸索着什么,没摸到,她便转头对那光线微弱的窗外虚弱一笑,笑容里却好像有一种空洞的幸福。
这时候,我进去捡起了那张被风吹到地上的照片,行动仍然悄然无声的,我看了看照片上圆而不肥的小姑娘,又看了看病床上的少女,一时昏了头,恍惚起来竟认不得八喜了,也想不起她最近的模样。
她眯着可怖的眼睛,侧头努力感受光明。
我将她小时候那张照片安静塞到她手里,便一声不吭地走了。
她朝着我的背影问,谢谢你,你是谁?
我顿了一下脚步,继续出门。见我未吭声,她又开始碎碎念的自言自语了。是西西吗?看不太清,有点儿像,不对,她来不笑我才怪。一定不是她,她根本不会来看我。是护士吗?护士会回答我的吧。奶奶?买饭回来了吗?还是生气的妈妈?到底是谁呢?真奇怪,为什么不说话呢?喂,你走了吗?
嗯,我走了。我在心里回答了蠢不可及的她。别人是庸人,你就要做庸人了么?
整容后的八喜,被一个本身并不太好的男生给甩了,她那位名不经传的男朋友,好像是狐狸介绍的,没有正当职业,吃软饭的小白脸,靠一张有几分姿色的脸,喜欢骗骗学生妹的钱。阿昕告诉我,软饭男常常向八喜索要钱财,八喜连手机和寻呼机都卖了,爱得不可自拔。软饭男这一次分明是想换下一个女朋友,还冠冕堂皇嫌弃起八喜来。
要不是阿昕气愤找不到人说话,和八喜站在一个阵营上的她,大约不会来找我发牢骚。软饭男背着八喜,还和她那些姐妹暧昧来电,阿昕也被勾搭过,她委婉暗示过八喜,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哪里能听忠言。软饭男的出现,令阿昕意识到,围绕在八喜身边的阿猫阿狗是何等货色。
我说,你跟我说有什么用。
阿昕苦恼地说,她这种小角色的话,八喜压根不会听,其实能骂住八喜的人,只能是让八喜感觉比自己气势高的人。
我摇摇头,自嘲地笑了,不准备参与她们的俗事。这种情况,往往惹一身骚。八喜说得对,老死不相往来,我做得好像很容易。
回头我反反复复想了又想,八喜的确是不容易轻言放弃的人,想起那天在病房里见到的她,心不知不觉软了一些,可是这一点廉价的柔和,我想她也不会在意,她在意的始终是自己能否威风。
情伤过后的她,终于将戾气发泄到了不相干的人身上。她学起了狐狸以前关照别人的姿态,那日在食堂的我不止从头看到尾,也变成了事件中人。
八喜领人落座,不怀好意围住了一个厚嘴姑娘,她们其中一个餐盘里盛的是从泔水桶内捞上来的剩菜剩饭。其他人将她吃到一半的餐盘换成了泔水盘,八喜掐住她下巴,强行喂她吃潲水。一边粗鲁硬喂,一边齿冷笑道:“鸭嘴婆,你嘴巴不是很会说吗?不是很喜欢说三道四吗?吃什么治什么,以毒攻毒,多吃点!我亲手喂你,全给我一粒不剩的吃完,吃完后给我记住,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我搁下餐盘,当即上去一巴掌挥掉了八喜的勺子。我一字一顿地说,别再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别人了。
对于我激烈的态度,她反倒平静许多,示意人捡起肮脏的勺子,继续喂那人吃潲水,只留给我四个字,与你无关。
我忍无可忍,迫使八喜抬头看我,似毒舌吐着信子般说道:一日是狗,终身是狗,别说你当了我大半辈子的狗,这么快就想摆脱我跟班狗的身份?
她也抓住了我的头发,眼睛发红地问,在你眼里,一直是这样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是!
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会这样恶狠狠相待。
她们前进一步,欲来帮架。八喜咬牙切齿地说,这是她和我的私事,不需要别人插手,她真要打架,也是单独和我打。
八喜的话点燃了我如开水般沸腾的怒火,我蛮力将她按到了长桌上,失望透顶地啐了她一口,火冒三丈道:“我现在就是见不得你这种仗势欺人的样子。”
她淡然抹掉了脸上的口水,不痛不痒反问我,“这些难道不是你教我的吗?”
我勃然色变,也哑口无言。这种恼羞成怒,转化为不可控的戾气,我们在食堂里纠缠在一起打架,算是朋友之间最后一架。她没有使扒女生衣服那种阴招,我也没有真把她往死里打,只是按住她,忽轻忽重地掐架。
直到八喜从长桌上摔下去撞到板凳上后,她忽然一动不动了,我微微踹了踹她,嘲讽道:“你刚才欺负人的力气不是很充足吗?现在怎么没劲儿了,还跟小时候一样没用,还装什么大姐,我劝你,放下杂念,回头是岸,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八喜仍然纹丝不动,过一会儿,她慢慢捂住肚皮,整张脸惨白,额上汗珠渐凝,疼得嘴里哼哼唧唧起来。我又想嘲笑她弱不禁风,倏然便见她身下的裤.裆那处缓缓渗出刺目的鲜血,那股血越涌越多。她一顺不顺望着我,真真实实倒在了血泊里。只对我说了一句简短的话,西,我疼。
刹那,我心里轰然一跳,立马脱下外套包住她身下,已筋疲力竭的双臂突然气力猛增。我将娇小的她打横抱起,吼了一句呆掉的她们,把地上弄干净!
便抱着八喜不管不顾地冲出学校,我累得支撑不住时,后桌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我身旁接过了八喜,我也没和他多话,赶紧打了一辆计程车送八喜去医院。
后面跟来的保安和老师气急败坏极了。
八喜做紧急手术,我手抖着给八喜家里打了电话。
在漫长的等待时间里,我坐立不安。翻墙跑来的阿昕提起我的衣领劈头盖脸一阵骂。阿昕愤愤不平地说,小八为了你,真是不值当!!她神经兮兮在意你的看法,从来没有欺负过人,让我们装神归装神,不许欺负人。她今天教训的那个女生,是当初知道你家庭情况后,到处乱说的人,你被孤立的始作俑者!小八最初只是好心跟她们说,你父母离异,后娘也才去世不久,性格难免差一点,如果跟你发生摩擦,希望她们能包容你一点。哪里知道出了变数,你被爱嚼舌根的人传成那样,小八当时气得还和她们吵了一架,她见那股碎言碎语愈演愈烈,期间犹犹豫豫多次要不要收拾鸭嘴婆那几个,后来,还是想不通的她,就决定给她们点颜色看看。
一下听到事情真相的我,后退了几步,退到抵墙不能再退,也持续退着。不知是不敢相信八喜,还是不敢相信我如此一叶障目,于是喃喃自语,不是八喜造谣的吗?
阿昕不可置信地说,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她,喂,你们相处了十几年!
我坐在长椅上将双手穿入发丝,无尽愧疚顿然涌上心间,我沉浸在这些事实里,懊恼自己的鲁莽与不信任,更为受伤的八喜感到难过与自责。
后桌安抚我,难受就哭出来。
我不在一般人面前掉眼泪,因此摇摇头,颓然抱头,硬生生将眼泪忍了回去。
八喜父母慌慌张张来时,第一时间不是关心八喜的身心,而是大发雷霆女儿的丑事,也更担心自家的脸面。
八喜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以后,她的脸色依旧苍白不减,紧紧闭着双眼和嘴巴,如枯枿朽株,失了所有的生机,我几乎感受不到她的呼吸。
她艰难一睁眼,也是暮气沉沉的,她第一抹笑给了我,仿佛在安抚我。见父母只是狰狞着脸孔无情唾骂她,她平静微微一笑却那样死水微澜,继而无力阖眼。
这时候,我响彻云霄的几句话,震慑住了只会责怪孩子的那对父母。已经出了事,你们要做的是把她当做女儿来保护!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推卸责任!最大的责任人是你们,无能的父母才会把错误全部归于自己女儿身上!
我对着八喜妈,食指朝地而质问,你了解过她内心吗?!你知道她想要什么吗?!这么多年来,你只知道逼她!逼她!逼她!!你对她,难道只有一个逼字惯彻你伟大的母爱吗?
我又指向一心想赚更多钱而忙到脚不沾地的八喜爸,义正言辞地说,在自己父亲身上都找不到爱的人,才会去依赖外面不能分辨的败类!我求求你们反省反省自己,别一昧怪八喜!
八喜躺在病床上,泪水从眼尾如泉涌,一行接一行,浸湿了混杂消毒水的白枕。她明明流着泪,却装昏睡,我们如何叫她,她也不能从争吵声中醒来。
我也有责任,作为朋友的责任。在心中如何骂自己,依旧不能消除任何一点愧意。阿昕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叫我好受多了。她说,如果她是我,也不一定能处理得多好,也许会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