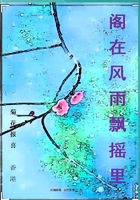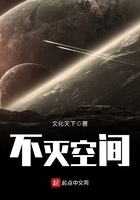厉止戈不知道死后有没有鬼魂和地狱,或许是有的,因为啊,死后的她终于挣脱了枷锁,没有阴谋,没有杀戮,可以安宁地沉睡下去。
她似乎是圆了个梦,那场梦华丽得不真实,金戈铁马,大漠孤烟,有酒有兄弟,沉重却也轻快,她一袭嫣红的苏绸锦绣扶桑罗衫,张扬地倚在城墙上。
边境安宁的时候,他们三五成群纵马去江南,调戏过江南如水的姑娘,尝过江南的清酒,赏过杏花春雨,小桥流水,嬉闹着追逐夕阳回去大漠。
死后真的很好,做梦都要笑醒了,如果能投胎转世,这样也好。
宋雍之看到她睫毛微微颤了下,以为是幻觉,霎时怔住了,浑身都要炸开一样,心跳声一声比一声剧烈,如闷雷轰响。
他看着一片死寂的山,使力抹了把脸,七手八脚带人回了山谷,往里走了一段距离,在枯草掩盖下找到个山洞。
他们是想把她带到这里吧,怎么会让她抛尸荒野,只是连这点距离都坚持不住了。
宋雍之在地上铺了几层衣裳,小心地放下厉止戈,消失在黑夜里。
他搜刮了些未烧尽的东西,支了火,给厉止戈包扎好伤口,烤上马肉,疲惫地指头都抬不起,眸子却是亮的,比天上最亮的星还耀眼几分。
他紧紧抱住厉止戈,喂她喝了口水,大口撕咬马肉,“你说,我要怎么谢他们?”
胡玉那四个人替她扛了大部分伤,一个个不成人样,所以才保住她一线生机。
宋雍之小心地不触碰厉止戈被火灼烧的地方,手烤一下火给她暖一下,热了水给她擦了擦血垢,露出她惨白的面容。
手指放在她心口,许久才感受到一点细微的心跳,轻到仿佛是他的错觉。
如果再晚点找到她,如果没有死死盯着她……
宋雍之歪头吐了口血,凄惨地笑笑,“止戈,咽血的滋味真不好受。”
他严严实实地将人拢在身上,在身边点了一圈火堆,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被噩梦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依旧没有见到人影,宋雍之吻了吻厉止戈,又烤了些马肉。
他们恐怕以为他陷在敌军中了,他又不是傻子,她想破釜沉舟,肯定会选穆朗山。
又或者说他们以为山上不会有活人,他在山里游荡几日也无妨,等他死心了再来接他。
她是真真没有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倘若沈浮山不是那副样子,他也会以为是她自己的选择。帅帐里的人就是最好的证据。
他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就那么清醒,大概是哀大莫过于心死,沈浮山恐怕也是,没有希望才会那么平静。
“我知道我们止戈最厉害了,再等几日,求你了,山下情况未明,我不敢带你下去。”
“欺负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哪怕是父皇,你不要怪父皇,都算到我头上好不好?”
“这一仗打完,以后再不会有战乱了,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没有为你做,你才清闲了几日?你舍得我一个人啊。”
宋雍之点了点厉止戈脸颊,“冷不冷?很快就热了,乖啊,再等一日,我们就回家。”
“你还没看看你亲手打下的江山呢,我以后不胡闹了,会当个明君,青史留名。”
“是父皇做了让止戈不能原谅的事吗?有我,父债子偿,无论什么我都赔给你,这辈子,这条命。”
“止戈想必舍不得对我动手,我自己动手,止戈不理我也好,我死皮赖脸缠着你。”
“我是止戈的夫君,什么事我都向着止戈,不管什么都有我,你信我好不好?”
“我啊,真的很爱你,拿命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这么重要了,你要是没了,我要天下血流成河。”
“就算老天抛弃了你,所有人都算计你,还有我,往后天塌了我也哪都不去,就守着你。”
“对不起止戈,对不起,我食言了,等你醒了,我跪青石板,跪到你气消,要我跪一辈子也可以,我本就离经叛道,跪给止戈我乐意。”
“你早点醒好不好?止戈,小祖宗?早就想这么叫你了,你可不是我祖宗吗。”
“我还没把你养成娇娇,你瞧瞧你,穆朗山一战死了四十万人,从古至今谁有你的手笔?这一战在史书上也必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倘若他们知道止戈是个女儿家,不知会多震惊,再也不会有另一个止戈了,我啊,老天何等眷顾。”
“我以后每年去护国寺祈福,闲着没事给老天烧烧纸,把世间风景都搬到京城,别说江南了,海我也能挖一个。”
“以后只要不涉及你,我事事听你的,止戈发话了我绝无二话,把你当祖宗供着,止戈想怎么玩我都可以。”
…………
宋雍之絮絮叨叨了一日,染了哭腔,语气越来越轻,生怕扰了她,厉止戈连呼吸都近乎没有,一点反应没有。
他看着外头昏暗的光线,低低笑了声:“我是真没用,父皇这次倒也敲醒了我,父皇该退位了。”
“你不用担心我会为难,父皇不曾想过我会为难,止戈,回家了,要下雪了。”
他将厉止戈包成个球,将炭火装在捡到的水壶里,放在两人中间,“止戈猜猜,这场雪会有多大?”
“下得久一点才好,最好下个十天半个月的,等你醒了,整个边境都是雪白的。”
宋雍之舔了舔嘴唇,明媚的笑容下是无尽的杀气,风雪为墓是什么滋味,他要亲眼看看。
他不疾不徐往山下走去,月光如寒雾,清清冷冷,映亮了穆朗山,漫山的血腥仿佛在无声送别。
渐渐下起了雪,宋雍之咳出口血,嘴角的血迹无声滑到脖颈里,“止戈,求你了。”
看着厉止戈惨白的面容,苦笑起来,逐渐加快了步伐,才出山谷不久就听到前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
他不动声色绕过一波一波残兵,迂回地往山下走去,越往下残兵越多,宋雍之靠在一块岩石后,敲了敲头。
换做是她,千军万马也能带他杀出来,一群残兵他都畏首畏尾。
“止戈,我们赌一把,我赌遍京城还没输过。”
“要是赌输了,我陪你,要是赌赢了,回头我带你去赌场玩玩,人生百态都带你看看。”
他衔住厉止戈的唇描摹,吻走她唇上的血渍,足尖轻点,长刀割破一个敌军的喉咙,夺了匹马朝山下冲去。
这边的动静很快引来敌军的注意,宋雍之紧紧护住厉止戈,尽可能地匍匐在马背上,周围的喧闹似乎都消了,四方皆空,万籁俱寂。
有利箭从他们身边射过,箭刃反射着冰寒的银光,宋雍之随意地挥舞着长刀,手臂被箭刃划了数道伤痕。
有支箭斜斜射中马腿,马儿哀嚎着摔倒,他踏着马背朝前飞去,几个呼吸间躲进林子里。
宋雍之并未走远,小心地撑在一棵焦木上,没有惊扰到蓬松的积雪,索性没有人想到往上看,也没有猜到他并未逃窜。
他缓缓垂头碰了碰厉止戈的额头,再等等……止戈,再等等,现在像不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耐心地等到这边的敌军稀疏起来,咬牙又抢了匹马,没有着急往山下走,而是横着绕了圈。
敌军士气全无,追逐他的人象征性地追一追就半途而废了,饶是如此他也浑身是伤,眼前发黑。
他在赌,赌沈浮山不会看着他死,止戈拿命换来的天下,沈浮山不会交给那群致使止戈去死的人手里。
不知道抢了几匹马,流了多少血,只知道怀里的人快不行了,经不起颠簸了。
宋雍之费力地爬起来,步履蹒跚地朝前奔去,所有人都在逃命,只有他不要命地纵马往回跑,就算披上敌军的衣裳也无用。
不能再骑马了,目标太大,再受几次伤,他也得死在这,嗓子火辣辣地疼,眼睛却比天上的弯月还亮。
黑沉沉的夜色里渐渐融了些光亮,雪渐下渐大,宋雍之分不清是雪的颜色,还是天就要亮了。
他一步一步走在雪地里,在莹白的雪上留了一行鲜红的颜色,隐约看见前边有几个黑影,夜色都没有他们身上的甲胄黑沉。
宋雍之倏的笑了,他赌赢了,止戈,我赌赢了,止戈……
他扑通倒在雪地上,双目无神,空空洞洞,血泪潸然而下,冰寒彻骨的雪地都没有怀里的人凉,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