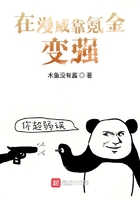入京之人,谁也不会忘记他第一次映入眼中的京城景象。
那时,我从家乡晋京的入口在“前外”东侧的老车站。
那时,由津至“京”(还叫北平)的火车,疏疏爽爽,清清闲闲,自自在在——没有多少人,也用不着纷争拥挤。及至车到京城终点,从车窗看见了真正的老北京的城。这不是个“名词”,是个实体。它那么古老,而又那么完整、现实;它那么峻伟,而又那么亲切近人——你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它,并无任何阻挡隔阂。
车缓缓停住了,乘客们从从容容下了车,脚踩着了北京的地面。我的感觉很奇异,但难以文词传达。
出了北京(老)车站,回头一望,见那是一座弧形顶红砖建筑,当时那是个很洋气的物色了。但一朝前走,“北京味儿”就扑面而来,令人立刻置身于一个异样不同人间的境界中。
出站是向西行,右手就是一排带廊子红柱的房屋,已与别的地方两样。走到尽处,接的是城墙旁门——此墙是连接在正阳门楼的。进了这门,才是真正的内城——老北京的主体:内城。
进了内城,入眼景色全新。这新,是外地人初见京城风貌的新。本地的老年人也会说新,只是意味不同:我所见的早非明清之旧观,因为辛亥革命后把皇城拆了,天安门外六部口内衙署消失了,只剩下皇城正门还有残痕可寻,已改名“中华门”。门内直到天安门外这一片,满栽了各色灌木小树,十分茂密,散步者都在此处游憩。这一景观,到新中国成立后仿苏联红场而建天安门广场,即又归于无有。
我这儿说的是一九四〇年的进城路线,前一年投考燕京大学时却与此不同,那是先在前门外“西河沿”去住旅馆。外城的事,容后另谈,因为我与北京的因缘是西郊海甸[2]与内城东城。
如今且先说明:我早年学程十二分坎坷,也说不清经过了多少次的失学(四大原因: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日寇侵略,水灾困阻),直到一九四〇年之秋,方得在京西郊读书。谁知只有一年半,燕园便被日军封闭解散。抗战胜利后,几经努力,又得重入燕园——到我毕业于西语系,已是一九五〇年。然后进入中文系研究院。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五月,入蜀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自一九五四年春夏之交,我正式落户于内城的东城,直至于今。
却说一旦定居东城,那么若从外城或外地回家,则必入正阳门东之侧门,循灌木空场的东侧而北行。此东侧是老洋式楼房样式,记得有一所北京最大的邮局,当时若寄海外信函,须到此局(因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之旁也)。此侧并无民居——不像西侧还是老红墙,一排民户的门巷风光。倘若不循东侧直走,拐入一个小弯处,就是通往使馆街(原先翰林院等文化衙署所在),转而北,便还看得见残存的(八国联军炮火的罪迹)带琉璃瓦的某种叫不上名字的栏柱,——仅仅这一点点入目,立刻令你感到这是皇都,这是帝城,这是“日下”“春阳”,真是迥然与“尘凡”“俗世”境界悬殊了。
这样走不多远,眼前就是一座雄伟的“三座门”,此“门”像是一座城门楼,楼阁之下分列三个“洞门”,以通车马。它是跨“满”有名的长安街的特色古建筑,别的城市尚未见过。循此长安街往东不远,就到了街东口,那儿又一座金碧辉煌的牌坊(原长安街只到“东单”,以东全是窄密衔聚的民居,巷亦很狭。今日此街往东延伸,是新中国成立后拓宽展长的)。牌坊,本名“就日坊”(与西城对应的那一座叫“瞻云坊”),具名“东单牌楼”,而北京口语则只叫“东单”。
从“东单”往北行,笔直的大街(北京的街皆可用此语形容)忽到一处大十字街口,只见交叉之处,四面分峙四座大牌坊,其规制又大胜于“单”坊,真是美不可言——我每到此际,总是自愧“词穷才尽”,笔下写不出一句“像样子”的“文章”来足以稍表其美境,心里对不起它,惆怅而悲悯。
这叫东四牌楼,口语又只称“东四”。
从“东四”起,东侧的胡同(巷之专名)便排次起来,叫“东四头条”“……二条”……直到“十二条”为止。再往北,不排行了,有条胡同名曰汪家胡同,进去再往北,则一巷二名:西曰“辛寺”,东曰“门楼”。
这个门楼胡同,便是我定居北京的第一处“巢痕”了(巢痕是陆放翁诗中用语)。
诗曰:
长车缓缓驻都门,十丈崇墉古未昏。
帝里皇州成旧语,中华文化宝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