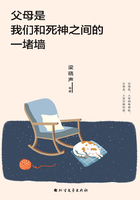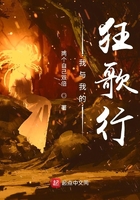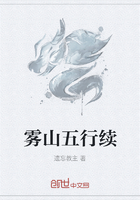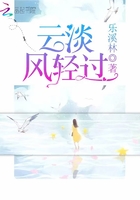正午的蝉声正闹时,全连开始进入午休。突然传来一声很刺耳的哭声,是一个女人的哭声,接着,另一个孩子的哭声也加盟其中,一高一低,此起彼伏。听声音,这哭声音量高,但不惨烈,不紧不慢,像是一场刚开锣的戏,一下把营区笼罩在哭泣的氛围之中,连那闹人的蝉声也多了一分悲鸣的成分。
安静的营区原本有些空旷。在这清一色的男人世界里,这女人和小孩的哭声像一堵墙,横亘在我们的睡梦边缘,让人睡意全无。我很惊讶,大中午的,谁在楼下“诉冤”哪?我想起来看个究竟,寝室的老余制止了我,他说:“一分队老王家的事,你凑什么热闹?”
我军校毕业刚回老连队才三天,连队的情况我陌生得很。但老余的话,让我想起午饭前楼下的那个胖女人——她两腮酡红,脸给人感觉很大,都是肉,一个平面似的,鼻子、眼睛、嘴巴都被肉包围了,就成了几个点点缀在脸上;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那件碎花衬衫穿在她身上明显显得小,紧紧勒住腰间那坨鼓鼓的肉。这件衬衫薄而透明,那白色的胸罩很扎眼。她一脸呆滞地坐在水泥条凳上,身旁坐着一脸邋遢的小女孩,小女孩只有六七岁模样。我熟悉这样的形象,这对母女就像是我乡下的大嫂。
小别胜新婚,印象中,连队那些干部、志愿兵,凡是家属来队期间无不一脸春风,整个人掉进蜜罐一样,说的每句话都蘸着蜜透着甜味。这时的老王一家三口子应该沉浸在其乐融融的幸福时光里才是。老婆孩子为何会在楼下大哭?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还是起来看个究竟。我从三楼走廊朝楼下探头看,只见老王在一旁拉着孩子,劝她不要哭,却被孩子的母亲拽在怀中,不许她父亲碰。指导员在一边劝老王的家属,却怎么也劝不好,她母女哭声越发高亢,二楼和三楼的走廊上,越来越多的人探头观看,指导员朝大家一打手势,又各自回到房间里。
老余知道这场哭没个把钟头不会收场,知道午睡泡汤了,老余干脆坐起来,不睡了,他和我聊起楼下的事,聊起老王的这桩婚姻。老余和老王分别来自安徽和苏北的农村兵,老王比老余还早入伍一年,如今他俩都是马上面临转业的老志愿兵了。老余说,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不上军校,转志愿兵就成了农转非的唯一出路,转上志愿兵就是鲤鱼跳龙门,那是命运的一次大转折,是人生的大喜事。为此,谁不为自己拼一个农转非而竭尽全力,多少人当了半辈子的临时工,就想转上一个正式工,成为国家工人,从此告别一个农民户籍。当时老余和老王都是这个心思,才转了志愿兵。但当时老王在转志愿兵时有个麻烦,他入伍前谈了一个对象,就在他转志愿兵当口,老王想和对方断绝往来,他不想拖个农民户口的过日子,他想重新找一个城里的,起码是居民户口的,他想和农民身份彻底告别。可是对方不愿意,她哥在部队当过兵,知道部队情况,就告诉他妹说,像老王这样想当陈世美的人,只要把情况告诉部队,他就转不成志愿兵。这个妹妹听了哥的话,到部队一闹,老王就有一道选择题:要么退伍;要么转志愿兵,但前提是他必须和这个女子结婚。老王选择后者,同时也吞下了一颗苦果。今年老王要转业,不知为何,老王在这节骨眼上旧事重提,还要和对方离婚,对方不同意,又闹到部队来了,这出戏和当年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孩子参与其中。
我也正处在谈对象的年纪,老余的讲述,让我陷入沉思。我觉得这桩婚姻一开始就是错,错就错在他们原本不该相识,才不至于一错再错。错就错在这个女的认死理,一辈子只认老王一个,非要一条道走到黑;错就错在老王一心想鲤鱼跳龙门,更错在跳了龙门后的老王有新想法,错在老王当初有新想法后还首鼠两端,鱼和熊掌都想兼得,错在老王到转业当口又有新想法;错在这个女的有个当兵的哥哥,对部队的情况太熟悉。
正当我大发感慨时,老余说:“你这小年轻知道个啥?婚姻是一条船,没到岸,谁敢说对与错。”老余的话提醒了我,对他人的婚姻,知道得再多也是隔帘看戏,我们只清楚台前看到的那一出,幕后还有多少精彩大戏你是无从知道的。但老王家这台台前大戏实在精彩,甚至发展到把我们都搅入戏中,以至于我们都成了戏中人。
后来那个女的,几次横躺在楼梯中间,每到开饭时间就躺在那里。老王住二楼最里间,她可能是想堵住老王的去路,却把我们二楼和三楼的几十人全堵死在楼上。我几次走到那里都不得不停下脚步,跨过去也不是,跳过去也不是,看到她,让我左右为难。要是他俩不闹,见了她,我还得毕恭毕敬地叫她嫂子,可是现在,这个嫂子成了我难以跨越的一堵墙,挡住我的去路,挡住大家的去路。好在我们和四中队同住一个大楼,大家还有一个“退路”。二楼和三楼的人只好绕道走,大家决定从四中队的楼梯走。
我们可以绕开她这个人,却绕不开她的声音,待大家从食堂回来,正当午休时,她又在楼下号开了。而且只要一开腔,绝不会一时半刻有刹车之势,整个连队又被她母女俩的哭声包围了。后来,发展到早中晚都有哭声,只要开饭铃声一响,她母女俩就开始哀号,那声音拉起腔调来,很是悲惨。我想起农村的哭丧,三餐开饭时都要放开大哭,这对母女多懂得利用习俗呀!她用哭声把全连的人心都搅乱了。
这可苦了指导员和老王,每次都得苦劝,却均无效果,就不劝了,任她哭。她可能发现自己的哭声效果不明显,只好回到二楼和老王闹。这次她改变了策略,她清楚自己的问题不在其他人身上,而在自己家老王身上,其他人不可恨,可恨的就老王一个,她不想就这么便宜了老王。那次,她趁老王不注意,一把抓住老王的命根子,像武打片那样,牢牢抓住老王的命门不放。她觉得男人最可恨的最不牢靠的就是这玩意儿,你变心,不就这玩意儿想造反吗?“哼,我干脆废了它。”那女人当时可能就这么想的。听老王同寝室的小赵讲,只听老王惨叫一场,当时一脸铁青,豆大汗珠瞬间从额头冒出,整个人呆在那里,那场面惨不忍睹。所幸他在场,并及时上前施救,才使老王幸免“被废”。后来,老王对她也加强防范,她很难袭击老王,正面进攻又占不了便宜,又在楼下哭开了,碰上机会也会打一仗。
双方闹到这份上,部队不可能不管,再不管就真的出人命了。她和老王的家事就成了连队的事,成了部队的事。那段日子除了老王,最苦的当数指导员。指导员是政工干部,他就管这些军事训练之外的犄角旮旯之事。他知道自己无力劝解这对“冤家”,就向营团领导反应情况。团里派个股长来帮助他一块儿做老王家属的工作。每到楼下哭声响起,那位股长和指导员一起,把老王家属劝进值班室里,还从食堂端来热腾腾米饭,在一旁轻声慢语地劝:“嫂子,你先吃饭,天大的事,先吃饭再说……”我看他们配合默契,一板一眼地把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可是老王家属不配合,她不领这个情,始终一口饭不吃,坐在一旁哭个不停。她对自己的困境无能为力,只能用哭泣表达。被掐之后的老王对离婚问题更不松口,她拿老王没办法,只好用哥教的方法,继续闹下去。在连队闹不出大动静,她干脆跑到师部大楼门前闹。大中午,她一人横躺在大楼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这下可把指导员吓坏了,师部大楼是首长进出的地方,若把连队的糗事闹到那里,那可如何是好?他赶紧派四名战士去把她硬请回来。分队的彭茅回来说:“那手上脚上都是厚厚一层灰,我们都抓一把树叶垫着才敢抓上去。”听了这话,我倒不觉得她脏,身上的灰都可洗去,心灵的锈却难以除净。
部队也受不了她的闹,决定派人把送她回家,可送她回去的那位股长刚回部队交差,她也回到连队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此三番五次下来,就像一个老上访户一样,她和部队之间展开拉锯战。
对于她,婚姻就是她的全部,她绝不放过老王,她手里还捏着老王一张牌——孩子。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孩子就成了她最后的手段。她当着老王的面,抱着孩子要从二楼跳下去。老王可以不理她,却不能不理孩子。他不能拿孩子来下赌注,谁也不敢把一个孩子的生命压在一个失去理智的女人身上。为了孩子,双方在连队上演一场又一场大戏。
看到老王家闹到这份上,同住一个寝室的老兵陆正冲说了一句引人深省的话:“婚姻是一件湿衣服,穿上身容易,脱下来就费劲了。”
从老王的情况看,他穿上这件湿衣服不但费劲,而且还很被动。老王一直在被动应战,他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他觉得家事就是私事,就应该坐在家里协商解决,坐在房间里静静地协商,而不是把所有人都闹得鸡犬不宁。但他又不能和她一道回去,他知道回家更厘不清他的婚姻,她一人就这般厉害了,何况她还有娘家一帮人做后盾,老王一直躲在部队,想躲过这段纠缠,好让他俩的婚姻无疾而终。而对方想法正相反,她就是要把自己和老王的家事闹大,闹到老王无地藏身,闹到他回心转意,闹到他乖乖跟她回家。
我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变惊得目瞪口呆。看着这只剩下一个空壳的婚姻,竟还继续以命相搏下去,让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给婚姻戴上一具双人枷锁,她愿意为它扛一辈子。这具枷锁没有钥匙,从结婚那天,她把钥匙丢进风里,一生无解,无论对方怎么挣扎。
老王无奈,坚决躲在部队,直到他转业那天他都没回家,而选择去深圳打工。这和他当初转志愿兵时的初衷,希望当一辈子的国家工人的愿望南辕北辙。
2014-08-15于平和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