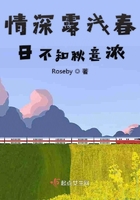我看着哥哥,他转过了头。父亲朝窗口那边走去,就在那时我再一次看到了戈兰先生。但这一次,他躺在地板上,双腿并拢,一只手臂向外伸直,另一只弯曲在胸前,看起来就像死于练习跳探戈舞的瞬间。我想要靠近一些,哥哥试图阻止我,但我躲开了他的手。
“他的号码哪儿去了?”我大声问。
屋里的人都转过来看着我,我母亲也放下了话筒。
“离远点,埃莉。”父亲朝我伸手。
“不,”我后退了两步,“他的号码在哪里?他手臂上的号码哪儿去了?”
埃丝特看着母亲。母亲把头转向一边。埃丝特朝我张开双臂:“过来,埃莉。”
我走向她,站在她面前。她闻起来有股甜蜜的气息。我想,是土耳其快乐糖[13]。
“他从没有过什么号码。”她温柔地说。
“他有,我看到过。”
“他从没有过什么号码。”她轻轻地重复了一遍,“他过去常常在身上画些数字,当他感到难过的时候。”
那会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看上去仿佛就是昨天才画上去的数字,很有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该明白。”父亲有些生气。
“但关于那个恐怖的营地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埃丝特将双手搭在我肩膀上:“噢,那些营地是真实存在的,恐怖也是真的,这些我们从不会忘记。”
她把我拉进怀里,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亚伯拉罕没在那儿待过,”她摇摇头,“从来没有。他只是精神错乱。”她随意地说出这句话,就好像在谈论一种新的发色,“他在1927年来到这个国家,一直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也许有些人会说那是一种自私的生活。他带着他的音乐到过许多地方,也曾获得过极大的成就。如果坚持服药,他还会是我熟悉的亚伯;可一旦停下,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他都会是一个问题……”
“那他为什么对我说那些事?”我的泪水流过脸颊,“他为什么要撒谎?”
她忽然停下来看着我,欲说未说。我相信我在她眼里看到的与她从我身上所领悟的事实一样——恐惧,她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伸出手,给她看我的掌纹生命线。
她把脸转了过去。
“为什么他会对你撒谎?”她仓促地说,“罪过,仅此而已。有时生活给予了你太多美好的事物,你却视而不见。”
埃丝特·戈兰的话将我淹没。
* * *
母亲将之归咎为惊吓,是突然失去父母之后的延迟反应。她说,自己就是这样长了肿块,同时将贝克韦蛋挞[14]端上桌面,并将盘子递给我们。她说,像是有股不寻常的力量在体内触发,不断旋转、积聚,有一天,当你洗完澡准备擦干身体时,你感到那股力量就在你的乳房里。你知道它不该在那儿,但起初你不会太在意。过了数月,肿块渐渐变大,恐惧滋生。最后,你会坐在医生面前,解开羊毛衫说:“我长了一个肿块。”
我父亲确信这是癌症肿块,但不是因为母亲有易于患癌症的基因。他向来悲观,总是留心提防破坏美好生活的事物。他认为美好不能久存,甚至一个半满的玻璃杯在他眼里也会变成半空。看着他的理想主义迅速转变为胡说八道颇有几分怪异。
母亲要做活组织切片检查,但她不会离开太久,最多几天,她沉着冷静地收拾着行李,就好像要去某个地方度假。她只带了几件她最好的衣服、一瓶香水,还有一本她最爱的小说。衬衫与压在棉花和纸巾之间的薰衣草香囊叠在一起,也许医生很快就会惊觉:“你很好闻,是薰衣草香,对吧?”她便会向围在她病床边的医科学生们点头,他们正一个一个地针对在她体内偷偷增长的细胞提出自己的诊断意见。
她将一套新睡衣放进她的格子呢旅行袋里,我伸手摸了摸。
“是丝绸的,”母亲说,“你姑姑南希送的礼物。”
“她很会挑选礼物,不是吗?”我说。
“她会过来陪你们住一段时间,你知道的。”
“我知道。”
“替爸爸照顾你们。”
“我知道。”
“你很高兴,对吧?”她说。
(又是那本书。叫作“如何告诉小孩子不易开口的事”的那章。)
“是的。”我轻声说。
母亲要离开了,这感觉很奇怪。在我们年幼的生命里她的存在从不含糊,一直可靠。她一直在这儿。我们就是她的事业,在很久之前她就放弃了另一种生活,选择日夜守护着我们。未来某一天,她会告诉我们,她所屏蔽的,是门外的警察、电话里的陌生人,和宣告生活又一次分崩离析的阴沉声音,来避免心头遭遇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坐在床上,深知她的种种品质是大部分人宁愿留到碑文上的那种。我的恐惧,如同那些增长的细胞般沉默无声。我的母亲很漂亮。当她说话的时候,她可爱的手使谈话变得很愉快;即使她听不见,她打出的手语也会像诗人念诗一样优雅。我凝视着她蓝色的眼睛:蓝色,蓝色,蓝色,和我一样。我在脑海里歌唱着这个颜色,直到它像深海一样将我淹没。
母亲停下来,轻轻伸出手捂住胸口。也许她在尝试与肿块道别,或是想象着伤口。也许她在想象手术时伸进来的手。也许,只是我在想象。
我浑身战栗着说:“我也有一个肿块。”
“在哪?”她问我。
我指着喉咙。她将我拉进怀里抱住,我闻到了从她衬衫上飘逸出来的薰衣草香气。
“你会死吗?”我问。她笑了,就好像我讲了个有趣的笑话,那笑声对我来说比单纯地回答“不”更有力。
南希姑姑没有小孩。她喜欢孩子,至少她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常常听母亲说南希的生活里没有给孩子腾出的空间,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她一个人住在伦敦一个相当大的公寓里。南希是一名电影明星,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她算不上什么大明星,但她仍然是个电影明星。她还是个同性恋。她的性向与她所拥有的天赋构成了她。
她常常说我父亲得到了智慧与俊朗的外表,而她得到的则是除此之外的所有。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当她露出电影明星那种职业微笑时,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爱她,因为事实上,我们都有点爱她。
她活泼机智,总是匆匆来访。她就是突然现身——有时也不知是从哪里来——像“神仙教母”般,只是想将事情引往正确的方向。她过去在我们家的时候习惯同我睡在一起,每当她在身边我便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妙。她为我们这个阴沉昏暗的乡镇带来一丝温暖和光明。她大方得体,善解人意,身上散发着美好的香味。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反正那是她。人们说我长得像她,尽管我从未对此有所表示,但实际上我很高兴。有一天我父亲说南希长大得太快了。“你怎么长大得那么快?”我跟着问。父亲让我别再提,但我一直都没放下。
十七岁的时候,南希加入了一个激进派电影剧团,坐着一辆陈旧的货车游走整个国家,去不同的酒吧和俱乐部即兴表演。她曾在一个谈话节目中说戏剧是她的初恋,我们挤在电视机前大声叫喊:“骗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凯瑟琳·赫本才是她的初恋。不是那个影星凯瑟琳·赫本,而是一位厌世且魁梧的舞台经理。在《往返地狱》和《没关系》这两幕没有前途的话剧合作演出之后,她向南希表白了。
她们当时住在楠特威奇[15]的一个小村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条叫“母鸡松鼠”的小巷里。人们通常都去那个地方小便,但在那个晚上,南希说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她们搬着表演道具,肩并肩走回货车,突然,凯瑟琳·赫本将南希推到卵石墙上,狂热地亲吻她的唇舌及其他部位。南希手里的一盒刀具掉在地上,女人味十足的猛攻和狂吻让她惊讶得喘不过气。事后她说:“那种感觉很自然,很迷人。就好像与我自己亲吻。”——这是一个获奖女演员发出的至高赞赏。
父亲以前从未遇见过女同性恋,很不幸,凯瑟琳·赫本是他遇见的第一个,他被揭去了自由主义的外衣,流露了过多的偏见。南希说她感受到凯瑟琳·赫本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美,父亲对此难以赞同。他说那必定是极其隐蔽的,即使像考古学家一样长时间日夜挖掘也未必能有所发现。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凯瑟琳·赫本确实有所隐瞒,隐瞒着她的真实身份:卡罗尔·本奇利。她自认是个超级影迷,对电影知识的了解仅次于精神健康的知识。她常常悄然跨线——那条使多萝西走在黄砖路上[16]而我们只能安逸地坐在床上欣赏的“电影线”,分不清虚幻和现实。
“抱歉,我来晚了!”有一次南希急匆匆走进餐馆,与凯瑟琳·赫本见面。
“坦白说,亲爱的,我不在意。”凯瑟琳说。
“那就好。”南希便坐下来。
凯瑟琳环顾四周,提高了音量:“世界上有这么多城镇,城镇里又有这么多酒馆,而她偏偏走进了我的小酒馆。”[17]
南希注意到餐馆里的客人都在看她们。
“要三明治吗?”她低声问道。
“哪怕让我撒谎、行窃、欺骗或者杀人,上帝为我做证,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忍饥挨饿了。”[18]
“我对此表示赞同。”南希说,随后拿起菜单。
大多数人立马会意识到这些对话有失常态,但南希没有。她年轻,爱冒险,她只是对她的第一次同性恋情感到兴奋。
“她是个不错的恋人。”南希常常说。每当这时,父亲或母亲就会站起来说:“总之……”哥哥同我一直等着他们要往下说的话,但什么都没有,直到我们长大,总之……
我以前从未看到过父亲哭泣,母亲离开的那个晚上,父亲第一次哭了。我坐在楼梯脚偷听南希与父亲的对话,我听见他哭得语无伦次。
“要是她死了怎么办?”他说。
哥哥沿着楼梯爬下来坐到我身旁,用一张还带着余温的毛毯裹住我们。
“她不会死的。”南希坚定地说。
我与哥哥相互看了一眼,他没说什么,只是将我抱得更紧,我能感受到他加快的心跳。
“阿尔菲,听着,她不会就这么死去的。有些事情我清楚。你必须相信。她的时间还没到。”
“上帝啊,我会做任何事,”父亲说,“任何事。我会做任何事,只要她能平安无事。”
就在那时,我见证了父亲第一次与他从不相信的上帝谈条件。第二次是在将近三十年之后。
母亲没有死,五天之后她就回来了,气色看起来比前些年都要好。活组织检查很成功,那个良性肿块很快就被移除了。我让母亲给我看看——我曾想象它与煤炭一样黑,但哥哥叫我住嘴,他说我的行为很不可思议。母亲走进门的那一刻,南希哭了。她哭的方式很奇怪,我想那就是她能成为一个好演员的缘故。但当天晚上,哥哥在他的房间里告诉我,那是因为南希第一次遇见母亲的时候就悄悄地爱上了她。
他告诉我,南希在念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与她的哥哥(当然,就是父亲)去布里斯托尔度假。他们沿着门迪普丘陵[19]散步,路上寒风刺骨,于是他们走进一家酒吧,在烈火熊熊的壁炉前茫然地坐下。
南希正在吧台点一杯啤酒与柠檬水,这时,一位浑身湿透的年轻女人,穿过门口,朝她的方向走来。南希仿佛被钉住了一般。南希看着年轻女人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看着她一口气喝光,看着她点燃一支烟。南希笑起来。
她们很快就开始交谈。南希了解到女人名叫凯特,那一刻,她感到脉搏疯狂跳动。凯特在校念大二,英文专业,上个星期才跟男朋友分手。真是个笨蛋,她说,同时仰头大笑起来,展现出脖颈的柔韧。南希紧抓吧台,脸颊泛红,双腿涌起一股微弱无力的感觉,并渐渐向上蔓延。就在那一刻她决定,如果她不能拥有这个女人,那么她哥哥应该得到她。
“阿尔菲!”她尖叫,“快过来见见这个美人儿!”
就这样,是南希在大学最后一个假期替父亲追求母亲。是南希送花给母亲,南希打的电话,南希预订的烛光晚餐。到了最后,是南希替不知情的父亲写了情诗,让母亲爱上了他并“发现”了他迟钝表象下隐藏的深情。新学期开始之后,父母已经陷入了热恋。而南希正处在十五岁的迷茫年纪,受伤的心让她黯然离去。
“她现在还爱着母亲吗?”我问。
哥哥叹息道:“谁知道呢?”
* * *
“早上好。”在一个十一月的阴暗的清晨,南希醒来时对我说道。
“哈喽。”我说。
“怎么了?”她翻过身子面对着我。
“今天是话剧试演。”我静静地答道,并将红蓝相间的学校领带从头上套进去。
她很快坐起来:“什么剧?”
“《耶稣的诞生》。”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
“本来是不感兴趣,但詹妮·潘妮说服了我。”
“你打算演哪个角色?”她问。
“玛丽、约瑟夫,通常那些,”我说,“重要角色。”(除去婴儿时期的耶稣,因为这是没台词的角色,并且我不清楚在说了他的出生是个错误之后,自己是否被原谅了。)
“你需要怎么试演?”她问我。
“就站在那儿。”我说。
“没有了吗?”
“没有了。”
“你确定?”
“是的,詹妮·潘妮是这么说的,”我说,“她说评委单凭这些就能判断你是否拥有明星气质。”
“好吧,那么祝你好运,小天使。”她撑起身,拉出床头柜的抽屉。
“戴上这个,”她说,“祈求好运。它能激发你体内的明星气质,至少在我这儿,它一直奏效。”
我从未听她用过这个词,激发。后来我也尝试用上这个词。
我步履轻快地走到道路尽头,那里有一座房屋,外围用水蜡树结成栅栏。我跟詹妮·潘妮总是在这儿碰头,一起走去上学。我们从不会在她家里见面,那是因为对她来说不太方便,与她妈妈的新男友有关。当她妈妈在家,她跟他相处尚算可以,她说。但她妈妈并不总是在家,最近迷上了葬礼。我猜她妈妈只是比较喜欢哭吧。
“大笑?哭泣?其实都一样,不是吗?”詹妮·潘妮说。
尽管不太认同她的观点,但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很清楚我们的世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