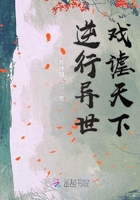两人举起酒杯颔首,说了几句后便离开了。接下来,便是长晏云陵一月的四皇子,晏云晋。
柳疏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一紧张就容易出汗。不过片刻功夫,鼻尖已经冒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
“恭贺陵王殿下新婚。晋王殿下还未到,我先替晋王殿下敬二位一杯。”
柳疏烟握着酒杯的手一下子收紧,她垂着眼眸,掩住那里面刮起的腥风血雨。还是这样细细柔柔的嗓音,还是那般稳重低调。
以前,人人都说虞将军府上的两位小姐一人红衣张扬,一人绿裳浅淡;一位天资聪颖,武艺超群,潇洒恣意,乃巾帼不让须眉;一位蕙质兰心,知书达理,稳重低调,乃大家闺秀之典范。都城中多少年轻豪杰为之倾倒,只是姐姐早已与晋王殿下两情相悦,订下婚约。上门求亲的人将门槛都踏破,妹妹却一直未嫁,如今已过四年,虞府早已不复存在,她却仍旧未嫁。
若不是已经死过一次,她怎么也不会相信,与她流着同样血液的妹妹会将她的姐姐,母亲,父亲,折磨致死,却还要博得众人同情怜悯。
她不止要问问她为什么,还要让她也坠入地狱,永世不得轮回。既然生前为姐妹,死后也要为姐妹。
饮下酒,柳疏烟唇边浮起一丝淡笑,眼眸中那阴冷的目光一瞬即逝。
虞桑,许久未见,别来无恙。
红色的喜堂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外面刮起了风,吹得堂中红布飞扬。红烛跳动着在墙壁上落下诡魅般的影子,阴冷刺骨的寒风中,翻飞的红布,舞蹈的烛火,飘忽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哪里是大婚的喜庆,分明是来自地狱的召唤。
今日一场大婚,人都齐了。大婚的红,红到极致,便是血的颜色。今日之后,这点红会慢慢的,浸染整个晏都,如同那日。峡谷中,自己,母亲,父亲,那千千万万忠心为国,无辜惨死的将士,那染尽天地的红,悲泣鬼神的红。
晏都里,所有沾染过这红的人,她要用他们的血,他们的膝盖,去祭奠,去忏悔。
柳疏烟回到房中,眼见阮郎马上就要来,山海等三人先关上门回去休息了。她坐在床上,屋内有烛火被风吹动,明明灭灭的声音,也有前厅传来的嘈杂声,呼吸一下,也能听见自己弱弱的呼吸声。
她有些累了,头上还戴着沉重的凤冠,试了几次她也不知如何取下,只好乖乖戴着不动。闭着眼睛昏昏欲睡,烛火摇摆的频率快了些,突然,呼啦一下子灭了。
柳疏烟猛地睁眼,她听见了门被轻轻推开又关上的声音,还有剑尖划过地面迸出火花的哧哧声。
好熟悉的香味,柳疏烟抠紧了床沿,高阳青衣。
她的伞不在身边,也没有人在身边,她的眼眸沉了沉,开口:“高阳小姐。”
声音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响起,等再次停下时,一道声音从柳疏烟头顶传来:“你真美。”
高阳青衣一边微笑着一边挥起了长剑朝她天灵盖砍去。同时柳疏烟摸到自己发髻上的簪子,当感觉一道劲风落到头顶时她毫不犹豫的拔出簪子狠狠抵住。当啷一声,尖细的簪子稳准狠的抵住了狭窄的剑面,高阳青衣竟然被逼得退了一步。
她喃喃道:“杀了你,云陵哥哥便会娶我。”她似魔怔一般,再次挥剑砍去。
这一次距离有些远,柳疏烟全神贯注,侧耳听着脚步声,她的发丝轻轻扬起。来了,她弯下腰,躲过她的一剑,右手握簪子用力刺下去,看不见她,但能感觉到她就在身边,不管刺到哪个部位,伤了她就好。
高阳青衣惨叫一声,柳疏烟抓住机会,抬手握住她拿剑的手用力一撇,剑飞弹而出,撞在墙壁上,碎成了两段。
“高阳小姐剑法实在是不精湛。”柳疏烟微微喘着气,右手发酸,她这副娇弱的身体真是让她无语,才这么简单的几招就用尽了力气。幸好是高阳青衣,她根本就不会用剑,否则早就死了,但她的能力有限,也抗不了多久。
高阳青衣没再进攻,她去捡起断剑,捂着小腹被刺伤的地方,眼神诡异的看着柳疏烟:“你不是柳疏烟!我虽与她不熟,但也有过几面之缘,她不会这些招数。你到底是谁?”
柳疏烟危险的眯起眼:“高阳小姐,不要随意窥探别人的秘密,会招来杀身之祸。”
高阳青衣一怔,那个娇弱又残疾的小姐露出一个森然的表情,那毫无焦距的眼神杀意渐浓,她的嘴角却含着微微的笑,美而危险。
那就只能在她动手之前杀掉她!
高阳青衣不敢再靠近她,对她来说,远距离进攻才更安全。没有听见脚步声,柳疏烟猜测到她的意图,但她忘记了,一个眼盲的人耳朵就是她的窗户。远距离的进攻她可以听声躲避,近距离她就必须肉搏,但体力是她的致命缺点。
高阳青衣迅速拿起断剑掷向柳疏烟,却在刚刚飞出去时便被从窗外飞来的不明物击中,那断剑瞬间便碎成了好几块。高阳青衣脸色苍白的看着把她的剑击成碎片的不明物,竟然是一片竹叶。
她转过头去,迅速拉开门,一阵狂风扑来,飘舞的竹叶从她身边飞落,她感觉脸上手上有些刺痛,再看看那些柔软的竹叶,有些不敢相信是这几片叶子伤了自己。
脑海里突然想到什么,她将门彻底打开,怒吼:“晏云晋,你为何三番四次与我作对!我与你何仇何怨?”
柳疏烟连忙摸索到盖头,胡乱盖在自己头上。
门外站着一个白衣男子,青青竹叶在他身旁飞舞,慢慢落在脚边,他仿佛是来自远山薄云处的仙人,容貌俊朗,风姿飘逸,有七分不问世事的超凡脱俗和冷傲,三分的凛凛霸气。
他星眸一扫,冷淡道:“走。”
高阳青衣冷笑着后退:“你凭什么抓我?你既不是刑部的人也不是府衙的人,管的哪门子闲事?”
晏云晋懒得和她废话,掂了掂手中的绳子伸手便要将她捆了。高阳青衣见逃不过便耍起了无赖,高声叫嚷:“晋王殿下非礼新娘啦!快来人呐!”她把衣服一扯,露出半边肩膀,对晏云晋道,“你要再过来我就把衣服脱光!”
柳疏烟咬着唇憋笑,晏云晋头次见这么不要脸的女人,神色越发冷漠,他垂着眼,手掌中几片竹叶翻飞,瞄准了高阳青衣。
“我救陵王妃有功,想必他们不会介意我将凶犯就地正法。”他用余光瞄了瞄坐在床上的柳疏烟。
高阳青衣咬牙瞪着他,又恨又怕,她突然笑了笑,转身便捡了地上的碎剑掷向柳疏烟。她剑法三流,却使得一手好暗器,那些碎片破风而去,速度极快,让看好戏毫无防备的柳疏烟措手不及。
晏云晋手中的竹叶比她的碎剑快了两倍,刷刷几下便将她的剑化作了灰尘。他迅速的跃起,抓住高阳青衣的手将她捆住,顺着手又将她的双腿捆了,将她像麻袋一般随意丢在了地上。
他的动作干脆利落,带起一阵轻风,将柳疏烟本来就没有盖稳的盖头吹了下来,露出她的脸。
他侧身而立对着她,正要拖了高阳青衣走,却看见余光里有一抹艳色。他回过头去,沉寂的眼波忽地动了动,那女子的眉间有一朵淡淡的彼岸花。
他记得,她以前说,如果有一天她不小心战死沙场,来世投胎成人,便要在眉间画一朵彼岸花,以免他找不到她。
晏云晋回神,眉头皱起,眸色深深,神情有些颓然,但她终究是不在了。
柳疏烟知道他在看着自己,却不似想象中难以面对。她满心荒凉,第一次相遇,他身着喜袍,他们擦肩而过,那迎娶的却是装着她骨灰的黑棺;第二次相遇,她坐在轿中,听见“晋王”才知道是他在;第三次,她孤身陷入险境,他走时,听见他的声音,才知道他来了;第四次相遇,她凤冠霞帔,坐在红烛暖帐中,却不是嫁给他。
造化弄人,若不是那场变故,他许诺的十里红妆,他们的白头偕老,长相厮守就不是她日日的梦。
他忽然见她深邃空茫的眼睛里滚出几颗泪珠,浑身发抖,有些莫名。听见她道:“让晋王殿下见笑,小女刚刚被吓着了。”
晏云晋点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又忽然想到听属下说这位柳小姐有眼疾,又停住脚步,说了声:“没事了。”
他走了,柳疏烟心头绞痛,她恨自己看不见,也不知他如今是瘦了还是胖了,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刚刚见到她,是什么表情。
即便万般思念,千般想见,他还是晏云晋,她却早已不是虞卿,是柳疏烟。在他眼中,柳疏烟,是皇弟的妻子,与他,再无关联。
晏云晋前脚刚走,阴媚就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柳疏烟听见声音,道:“高阳青衣不能活着。”
阴媚挑了挑眉:“是,小姐。”说完她幻化为原形,走出喜房去了。
紧接着,阮郎也进来了,他见了柳疏烟那苍白虚弱的样子,皱起眉头,给她服了一粒药,在床边坐下。
“你那前夫也不怎么样嘛,也就是长得精致些。”他给柳疏烟顺了顺气,又问,“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柳疏烟弱弱的翻白眼:“托您的福,死不了。你早知道高阳青衣来了吧?”
阮郎点点头:“是啊,阴媚那鼻子可灵了。我们这不是为了让你们好好重逢吗?”
“行了,我累了,要睡了,你出去吧。”柳疏烟把凤冠拆了放在他手里,又脱了外衣和鞋子,往床上一躺,拉了被子就要盖。
阮郎一把将被子扯住,她拉了几下没拉动,他说:“你让我去哪?我是新郎,这会儿要是出了这个门外头那些婆婆丫环……”
柳疏烟放了被子:“那你不会真要和我睡一张床吧?”她指着地上,“地下不脏,自己抱着被褥铺一铺。”
阮郎放了被子给她盖好,伸了个懒腰往床脚处一屁股坐下。柳疏烟听着,一下子没了声音,也没听见关门声,试探着对着空气喊了一声:“你走了?”
没人回应她,她努努嘴,翻了个身,打了个哈欠,不一会儿便睡过去。
睡到半夜,阮郎忽然听见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他迷蒙的睁开眼,抬头往床上看去,脸色一沉,忽地清醒了。柳疏烟紧紧的裹着被子,满头大汗,几缕头发紧贴在额头,极其痛苦的皱着脸,急促的呼吸。
不知道是做了多么可怕的噩梦,他叹息一声,将她被子拉开,给她扎了妙手针。她突然呓语:“救我,别烧我……”
阮郎的瞳仁紧缩了一下,他只知道她受了不少苦,但从未过问都是些什么苦。他连忙起身去点了安神香,又拧了湿毛巾,给她擦脸。她的手紧抓着被角,阮郎试了好久也没能将它掰开,只能等安神香和给她扎的妙手针慢慢起作用。
小半刻后,柳疏烟松了手,面容平静,呼吸浅浅,像是安稳的睡熟了,他才抹了抹额头的汗珠,松了口气。他忽然笑自己,只是做个噩梦而已,他为什么这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