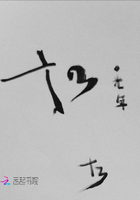在离开曲阜,返回济南的途中,我的思绪久久难以平复。汽车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急驰,我合上双眼,开始梳理一天的观感,解惑缠绕心头的一个疑问:孔庙、孔府、孔林,它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历史遗存呢?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一座孔子长子嫡孙居住的府第,一座孔子及其后世家族的墓地,造就了一座驰名中外的东方圣城;一部名垂青史的《论语》宏著,书写了享誉千年的东方圣经!
这里,有着中国最为古朴的教育思想。这里,积淀有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精华。我只是来此朝圣人流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这座圣城,这座圣城里的孔子,留给我的将是永远的膜拜。
走近大水井
屈指算来,我有十多年没到利川了。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利川是《龙船调》的故乡,是八百里清江的发源地,是一个生息繁衍着以土家、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自治的小城。从古到今,土家的情歌、号子、唢呐、木笛、茅古斯、锣鼓渲染着这方土地浓郁的民俗风情。
今年四月来利川,我听说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地名——大水井。乍听这个名字,满以为是一口水井,没往心里去。后来当地同行告诉我,大水井坐落于深山老寨,是建造于清代晚期至民国的李氏庄园,整个建筑群落由李亮清庄园、李氏宗祠、高仰台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20000多平方米。于是,我寻着土家秀丽的山水和袅袅弦乐,径直去领略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深山古堡。
山路蜿蜒,草木飘香,远处的大水井虽经几百年风雨侵蚀,依然不失为一道奇观,宛若一幅古朴凝重的水墨画,镶嵌在利川市柏杨坝镇绵延起伏的山峦之中。待我走近它,才觉得这座豪华庄重的古建筑是如此精粹,完全打破了古朴乡村原始的单调和朴素。一个土司家族荣辱与兴衰的真实写照,浓缩了土家文化的心智和建筑文化的底蕴,小家族、大世界的变迁,拨动着中国民族史和近代史凝固的音符。
在龙桥绝壁映衬下,李亮清庄园显得古朴沉寂。庄园按风水、八卦及地理条件巧妙设计,不仅与自然非常和谐,而且融合了巴人建筑风格,汉族文化因素和西洋建筑特色,堪称中西合璧,土汉结合的典范。庄园主体建筑采用传统南方吊脚楼法式,典雅脱俗,美轮美奂,凸显鄂西地域的自然特色与文化神韵。园内有24个天井,170多间房屋。沿一条青石板路拾级而上,可见高悬于门楣上“青莲美荫”的匾额,四个大字苍劲洒脱,翘角凌空,气度不凡。问及匾额为何人所书,寓意何在,随行的导游居然没能给我一个确凿的答复。导游告诉我,“青莲美荫”为何人所书至今无从考证,其意也各有说辞,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借唐代大诗人李白“青莲居士”的名号。如此自诩的表白,听来让人颇有附庸风雅的感觉,进而也有了一些神秘莫测的意味。
庄园四周的院坝采用花瓶造型围栏,围栏上装饰古典的白菜石雕,据说是象征“百财”和家世“清白”。我站立院坝前,细细观察那些敦厚的墙基,轻轻抚摸那些久经风雨洗刷的青砖碧瓦,体味着根植于百年院坝中叱咤风云的岁月和李氏家族特有的文化内蕴。
庄园内布局也极尽创意。东为花厅,西为账房,后堂为庄园主人及其子女居室,两端分别为小姐楼及绣花楼。前廊拱卷欧式方柱粗壮挺拔,精美绝伦的各类雕刻遍布墙廊,令人叹奇。两侧吊脚雕梁画栋,可谓独具匠心。纵观房屋的豪华规模,可以想见当年庄园的奢华景象。
小姐楼和绣花楼的堂屋前有四只石凳,两大两小。据导游介绍,过去李家挑选女婿有自定的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谁能把大石凳抱起来,便可在小姐楼内任意挑选对象;谁能把小石凳抱起来,则可以由李家指定对象。那个年代,这样的标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兵荒马乱之时,有钱远远不够,还得要有力的勇武者完成保护钱财的重任。我试着抱住一只六十多公分高的小石凳,却感到力不从心,眼前的石凳依旧立得稳稳当当。
庄园西面天井的墙壁上,刻有一个“忍”字,笔力遒劲。两边楹联上书有“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字迹。说实话,这样的楹联出现在一个家族的庄园里,我很难准确的解读它,或许,它潜含了一代庄主立世的态度,或许,它折射出一个家族隐秘的哲学。无论怎样,它都印证了一种文化的渗透和支撑,我只能虔诚的拜读,在拜读中感悟那“邃密”与“深沉”的谆谆告诫。
时近黄昏,游人渐渐散去,加之部分殿楼面临修缮,庄园里显得空旷而肃穆。初春的阳光透过天井洒进幽静的院落,一位资深的导游领着几个实习的学生为我们作详尽的解说,只听见我们窸窣的脚步声回响在廊道之间,回响在百年历史的深巷。
大山深处的李氏宗祠建筑宏伟,修饰华丽,透着一种古韵悠悠的神秘。宗祠柱头及穿梁皆有雕花,飞檐和屋脊均有青花瓷碗碎片镶嵌成各种图案,彩楼、门窗都刻有工艺精巧的花鸟虫鱼等图案,天井内还有水池和各种精致的花坛。宗祠主体三进四厢,中路开大山门一栋,两边是用专门烧制的有高浮雕琉璃塑画砖砌成的屏形墙面,顶上是江南牌科门楼式的垛墙,上有彩瓷拼嵌的“十八学士登瀛州”和“洛阳图”,左右门额上分别书有“居之安”、“平微微福”等字样。
让我震撼的是,在现今大多数祠宇、庙堂可供欣赏和考证的文化遗产或已荡然,或已流散民间的境况下,历经烽火洗礼的李氏宗祠却保存了诸多朱底金字的楹联,引发后人苦苦思索:“门近清溪,晚晴喧石漱。窗舍修竹,永夜动秋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皇王土圣贤书可耕可读,天地德父母恩当酬当报”……仅我足迹涉猎之处,这样的楹联就有几十余幅。
我曾去过国内其他一些古建筑群遗址,譬如厦门的土楼,成都的文殊院,合肥吴氏家族明清古建筑群,湖南东安明清古建筑群,贵州省安顺云山屯古建筑群,尽管它们地域不同,造型迥异,各具本土文化特色,但像大水井这样以楹联形式来烘托广博深厚文化内涵的祠宇确不多见。作为湖北省楹联协会的会员,能在这窗棂断裂,楼板腐烂,残缺破损的墙壁上读到一幅幅如此精辟的楹联,我很惊讶,也很欣喜。我想,水井原本是带有人文精神的,而利川大水井展现给人们的除了精美的古建筑,更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时光如烟,一副副字迹模糊的楹联,一行行工整对仗的经典文字,作为大水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李氏家族耕读为本、家族和谐、诚勉感恩的处世理念和文化底蕴,也饱含着淡泊宁静、自得其乐的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闪烁着祭祀文化的光泽和天人合一的人本精神。
土家文化源远流长,记载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间流传的“龙归井,凤栖山”的传说,让我们了解到李氏家族的根底:李氏宗祠原为土家族黄姓土司的官衙和住宅。乾隆时期,李廷龙、李廷凤兄弟从湖南西迁入川,分别落业于利川大水井和重庆马鞍山,因两人精明能干,被黄土司雇为账房先生,从此逐渐站稳了脚跟,并拥有了自己的产业。到了“龙凤”的第二代,便同黄氏打起了家产官司。官司一打就是十年,在李氏兄弟拜县官为义父后,李氏竟赢得了官司,黄氏土司衙门从此变成了李氏宗祠。
一次迁徙,一场官司,一个土司衙门就此易主,我心里隐隐有几分震颤。我不想去考证李氏家族是否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印记,当宅子的主人通过某种手段把“原罪”清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过去的纠结早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来的“忍”的哲学还有告诫后人的“涵养”,俨然以一个大家规范的模板被后人尊崇。历史有时很健忘,历史有时也需要这样的健忘,否则写历史的人因为有某些忌讳放不开手脚,读历史的人也感到沉重压抑。
不远处,宗祠城墙高耸立于荒州野岭之间。城墙高8米,厚3米,长约400米,全部用整块巨石砌成。墙楼炮楼突兀,护墙上布设枪眼、炮孔,显得格外森严。春天里,墙院内生长的水杉和马尾松茂密葱郁,墙边开满了各色野花。
历史发展到今天,每一处遗址,都应该与它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关联。眼前这座古老的城墙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像一位久经沧桑的老者,面对绵绵的山峦,面对悠悠的白云,面对一群无衣食之忧的后生,述说着它的前世与今生。
战乱时期,这里曾是战旗猎猎,狼烟四起,经历过一场金戈铁马、生灵涂炭的征战。川军土匪头子贺国祥,为扩充军饷壮大实力,派遣千余人进攻李氏宗祠,李氏据险相抗,相持七日不下。后来,贺国祥经人指点,采用占据水井,断其水源的策略,方使李氏妥协。事后,李家汲取“围井断水”的教训,并采纳贺国祥建议,将水井围入祠内。建成后,李盖五在墙外亲书“大水井”三字,行书阴刻,气势狂放。“大水井”这响亮的地名便由此闻名。
人们今天看到的“大水井”,不过是区区一口一米见方,长满青苔的普通水井。井内泉水清澈,取之不竭。据史料记载,李氏家族一直信奉风水,深知水之金贵,其庄园的大门朝向东北,便是出于堪舆之术中“对水口”的考虑,因为庄园的东北方向,正与小河入江的龙口遥遥相对。我伫立水井旁,面对历史流逝的伤痕,展开了无尽的遐想:如果当初李盖五有先见之明,尽早把水井围入祠内,李氏家族的历史会不会得以重写呢?难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解释套路?李盖五将这个地方称为“大水井”,是基于李氏家族从岳阳湖畔逃难到清江岸边安家落户的150年间,高居山顶,对水源与家族生命息息相关的彻悟,还是体现了李盖五作为大水井最后的守护人,对这一方水土刻骨铭心的依恋?这些我都不得而知。能够知道的是,历史曾在这里演绎了一段辉煌,也演绎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悲壮。想到这里,我内心不由溢出一丝无以言状的怜惜和伤感。
走出宗祠,沿一条青石铺就的小路前行2公里,便是高仰台所在地。这片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宅院地原叫“葡萄翁”,李氏最后一任族长李盖五因兄弟分居,造豪宅于此,嫌其地名俚俗,取“高山仰止”之意,定名高仰台。豪宅占地2000余平方米,有房屋40余间。建筑飞檐翘角,精雕细琢,鬼斧神工,其匠心工艺丝毫不亚于与之遥相对应的大水井。宽阔的院坝,高大的正厅,壮观的绣楼,整齐的配殿,错落相间的厢房,以及精巧繁缛细腻的木核石雕,令人流连忘返。
李氏家族的荣光在末代土司李盖五的高仰台找到了证据。高仰台的落成,不仅从点上增加了该建筑群的密度,而且从左右进一步烘托出李氏宗祠的中心高度,从大画面上增加了该建筑群体的对称、协调,以及“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的气度。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李盖五后辈因兵匪之患,不得不举家重返大水井,凭借天险和固城挣扎着拒敌,以求守住和延续李氏土司王朝的辉煌与荣耀。然而,连年征战使这个家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高仰台最终只能吟唱一曲土司王朝的挽歌,一步一步走向没落。兄弟家族内部的分居,只是走向衰败的前奏,但也正是这样的前奏,为时代加重了变迁的筹码。两公里的距离,是一段不短的路程了,或许家族的荣光或者利益,此时都不再重要了。看来,家大口阔自然有本难念的经,李氏家族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宿命。
我登上南面的一座山峰,放眼望去,灵秀的庄园,凝重的宗祠,落寞的高仰台,互为依托,互为照应,井然有序,宛若大山深处的一串明珠,徐徐生辉。不远处,利川城日益呈现出现代化的气派,街道上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即便在这土家氛围浓郁的偏远小镇,也因为土家文化热的兴起显得人丁兴旺,生意红火。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碰撞,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座古老而时尚小城的美好远景。
天色入暮,一抹残阳染红了山寨。抖落一天的风尘,我默默地离开,把足迹和灵魂留给这片古老的群落。
东坡赤壁咏叹
从省城去黄州的路上,我一直与同行念叨,此行一定要抽空去东坡赤壁膜拜苏轼。因为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我对这位宋代的大文豪素有偏爱,仰慕他的诗文,更仰慕他的人生。
盛夏时节,黄州古城裸露在一片酷暑中。山色赭赤,岩壁垂直,一片红色。刚一下车,一阵阵热浪便扑面而来,让人有些猝不及防。然而,东坡赤壁内却是游人如织,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让我好生感念:在中国的版图上,黄州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城,一个鄂东大地上极其平常的一隅,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让中外游客痴热?我想,这大概是缘于这块土地上演绎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留下了苏东坡等一代文人墨客的精神足迹。
东坡赤壁位于古黄州城西北边,始建于西晋初年,距今约一千七百余年,历经多次修建,至清康熙末年始更名为“东坡赤壁”。大门外保存着一截黄州古城墙,在夏日的阳光照射下,愈发显得古朴和沧桑。城楼上正在举办各类书画展览、古石展览,楼内隐约传来箫笛和古筝的弦乐。岁月流淌,古风尤在,今日黄州文化氛围如此浓郁,真是令人欣慰。正当我沉浸在亢奋之中,导游的一番解说又让我顿生纠结:原来黄州古城有一条老街,曾立有四十八个牌坊,其规模和年代在全国均属罕见。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时牌坊一夜之间被毁,听来令人扼腕叹息。
站在江岸远远看去,赤红陡峭石壁直逼浩荡东去的大江,浊浪排空,阡陌纵横,不由在心里吟咏起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篇佳句。千余年过去了,我们在这块红土地上延续着历史的大浪淘沙,体味着苏轼的清纯和空灵,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旷达与豪迈。我徒然有一种感觉:与江南的那些名山大川相比,这里的风光说不上奇特与秀丽,却显得不同寻常,不同凡响。或许是因为心里有了苏轼,心里想着苏轼,才使眼前的景致流溢着千古不衰的魅力与光彩。
缓步走进东坡赤壁,不由安静下来,感觉小城黄州到处都氤氲着苏轼的余韵:空气中流动着苏轼的气息,碑阁里镌刻着苏子的才情,酹江亭见证着苏轼的豁达,赤壁山折射着苏轼的光芒……苏轼把黄州小城搅热了,苏轼又把去黄州游玩的客人“冷却”了。在这里,没有游人在为苏轼鸣不平,每个人都在静心屏气地聆听苏轼,感悟苏轼,解读苏轼。
公元1080年2月,一个“乌台诗案”,将一个大师和一个偏僻的小县连到了一起。四十三岁的苏轼带着被“宽大处理”的流放罪犯的身份,带着满身疲倦和伤痕向黄州走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折和精神的升华。
黄州贬谪期间,苏东坡从“我生无田食破砚”的官禄之人变成了靠躬耕田亩养活家人的农夫:垦荒,种地,建房。那些日月,他住草房,点油灯,穿草鞋,披蓑衣,白天睡觉,晚上外出溜达。赤壁山是苏轼当年躬耕之地,如今已是山环水绕,林木茂密,哪有当年诗人“黄泥满地”的情状?倘若苏轼重游故地,多少有些不适应的,他还是喜欢那条种地的坡地和在坡地上亲自筑堂而居的雪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