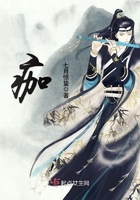经过两天的修仙式休养,乌雅终于在我耐心耗尽前醒了过来。她挣扎着起身,微微眯着眼睛,努力适应窗外透进来的阳光。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了?”我推门而入,将汤药交给熙晴,扶她坐起身来。
师父出手还没有解不了的毒,这一点我是丝毫没有怀疑的。床头的香已经燃尽,香灰碎撒在桌上,余烟袅袅。
乌雅的血适应的还算可以,再加上燃香的溶解,也好了七七八八了。
“我以为我已经死掉了。”她望了我一眼,“不过看到你,我就不怀疑了,又是你救了我,对吧?”
我摇摇头,将汤药递给她:“别太高估我,我没那么厉害。”
乌雅端起汤药放在鼻尖,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我怎么,怎么闻不到了,我,我也闻不到你的味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她拼命的嗅着,试图寻找到一点点熟悉的味道,汤药,香囊,花草。她像是疯了一般,抓到什么闻什么,可是却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先冷静一下,别激动,你现在的身体承受不住巨大的情绪波动。”熙晴立即上前,同我一起拉住她的手臂,不让她再做出伤害自己的动作来。
“啊,我的眼睛好疼啊……”乌雅突然捂住眼睛,在床边打滚。
我忍不住吼她:“乌雅,乌雅,你别再动了,不然你都对不起这双眼睛!”
被我这么一凶,乌雅果真停下了,她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只受伤的小鹿,害怕地捂住眼睛。
房间里碎了一地的瓷器,汤药全部洒在了地上,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子苦味。我挥挥手,示意熙晴再去盛一碗汤药来,熙晴会意,立即退出了房间。
我走到乌雅的身边,蹲下身来握住她冰冷的手。她的手在颤抖,我从未见过她这般模样,哪怕是在战场上,面对着生死,她也潇洒的像个女英雄。
“不要害怕,告诉我还有哪里不舒服?”
我慢慢地拿下她的手,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泪水倔强地在眼眶里打转,怎么也不肯流下来。
她的手颤抖地捂住胸口:“这里疼。”
“我突然好害怕,好难过,这里就像是缺了一块似的,空空的。”
突然间,我的鼻子就酸了。
大概互相喜欢的人是有心灵感应的,因为他们都是将彼此放在心尖上的。
“乌雅,这件事我想我有必要告诉你,虽然我答应了他,但你有权利知道,有个人在默默地守护着你。”
在我的的引领下,乌雅乖乖地回到床上坐好,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本正经地听我说话。
从季风闯入熙府来求我,直到她醒过来,这中间所经历的一切事,我都原原本本的跟她描述了一遍。
“萤蛊虽只是寻常的虫蛊,不像幽灵草那般稀有,却也是剧毒无比。虫蛊本就是靠血液而生的,再加上萤蛊里的蛊虫培养时就注入了毒素,所以一旦进入人体,就只有等死了。”
“不过你很幸运,毒素侵入五脏六腑,本已是无救了,你的命是用你的嗅觉和眼睛换来的,也算值了。”
乌雅总是忍不住打断我:“可是我的眼睛不是好好的?”
被我一个白眼扫过去,乌雅才悻悻地闭了嘴。“季风送你来的时候,毒素已经损害了你的视觉神经,总的来说,是他把自己的眼睛给了你。”
回想起季风当时决绝的样子,我似乎能理解,雁丘词中,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意境了。
“你,说什么?”乌雅不可置信地望向我,“他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乌雅,他已经……”有的时候欲言又止要比说清楚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不仅是乌雅,连我都锥心的疼。
我从袖中拿出一缕红色流苏坠塞在乌雅的手里:“他中毒的时候,手里一直握着这个东西,我想你会知道它的用意。”
季风还说,等他死了以后,让我替他把流苏坠还给乌雅,也算全了他的心。
但是我没有告诉她,事到如今,说还给她不是更让她难过嘛。
乌雅现在,需要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这是,我们初见时我穿的那件罗裙的挂坠,在被俘虏的时候不小心掉了,没想到是他捡到了,还一直留到现在。”她握在手心,小心翼翼的,仿若至宝。
“那就算物归原主了。”我顿了顿,有句话憋在心里,不问出来总觉得难受,“他临死前,问了我一句话,我至今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季风躺在床上,毒素已经完全侵入他的身体,回天乏力了,就连师父都放弃了治疗。
他强撑着一口气,惨白的脸对着我笑,呼吸得很吃力,他甚至连表情都做不了。
“你别告诉她,我不想让她难过。”
我不解:“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与其让我看着她离开,我宁愿离开的人是我。”季风紧握流苏坠,“你说,这算不算是感动呢?她会感动的,对吧。”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问自己。
“你疯了,你简直无药可救了。”
这一次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尽全力偏头去看躺在他身边的乌雅。他看不见,但那个身影已经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忘记。
渐渐地,他的呼吸也微弱了许多,我恍惚听见他在低声呢喃:“如果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如此爱她,我一定会在初见时,给她一个温暖的怀抱。”
下一次,我让让你,让你欺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