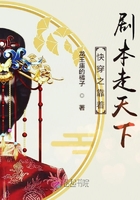七人行至武阳城时,已经日落西山了。今天正好是七月一十五日,中原节。
到客栈住下,已经入了夜。街上行人纷纷攘攘,大都是去河边放河灯的。有招昌意牵起有招休徽的手,在河边,望着静静河面上的那些小小的荷花灯。有招昌意总是能猜中妻子的心,“我瞧见这些荷花灯都好看得很,卿可有意乎?”“善。”有招休徽笑起来总是羞羞的,垂眸,用袖子遮住自己的小嘴。有招昌意喜欢她笑起来的羞涩模样,妻的眼里是星星般的河灯,夫的眼中是妻眼里的星星……
李靖戴着一个红红的狐狸面具拉着月婵的手儿在人群中穿梭,又跳又跑的。这是一条闹巷,街道旁是大大小小的酒楼,茶社,大大小小的灯笼高高挂起,明亮得就像白日一样。月婵在遇见七人之前,从未过过中元节。她一个人过节有些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吗?但是今日不同了,有李靖陪她一起过节,她也能去到人群中上蹿下跳而不孤独了。
街上的小摊上的商品琳琅满目,看得月婵画了眼。“李靖,你等等,我要买一串糖人!”
李靖停了下来,转过身对着月婵摘下面具,灿烂一笑,“你等等我。”“好!”月婵也笑得灿烂。
月婵站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想着李靖给她买的糖葫芦。
“月婵!”李靖高,月婵老远就看见他举着一串糖人对她招手了。月婵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身影,笑得像河中的花灯,双脸绯红,踮起脚尖举起自己的手挥着。
“咬一口吧!”李靖跑得太快,有点喘。月婵看着他一上一下的胸膛,心中升起一个小小的太阳,从来没有人能在她一开口说想要什么东西时,就立马帮她去找,立马去帮她寻,她有点想哭,但是又觉得今天这么高兴,更加应该笑才是呢!月婵小心翼翼地接过,吧唧咬了一口,“真好吃!这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糖人了!”
“你笑起来就像这糖人一样甜。”
“哇!那边有人放花灯!”小姑娘高兴得跳起来了,“李靖我们去那边!”小姑娘牵起少年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向河边了,也不知道听没听见少年的那句话……
街的另一侧有河流过,河畔种着洁白如玉的栀子花被河面上的点点荷花灯投上淡淡的粉色。风来了,吹落的栀子花瓣就像天上的星星,散落凡间。街上的宝马拉着雕着各色纹样,缀着各色珠宝的车,车中焚的香从那用金丝线绣着牡丹的帷幔中散出来,一路便都是弥漫的香味。街上的人儿哪个不是笑语盈盈?
李飞今夜并未打坐,一个人悄然闯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上了城北的一处高楼。今夜月圆,武阳城明如白昼,只有一轮月亮高高挂在西边,天上看不见星星。李飞提了一壶酒,独自望着北方。那是他故园宋国的方向啊,路迢迢,路曼曼,又如何望得见啊?
“自我蒙尘南下已两载有余,不知燕寇可有来犯,不知百姓是否安居,不知君上可得能人将士辅佐,不知君上又是否听信了佞臣小人的谗言啊?”
叹息复叹息,“北方有异。”李飞举起酒壶,对月而饮。“而我李飞却苟且在此,不能为故园献一丝微薄之力!”李飞目光深而重,鬓角几丝白发在风中轻摇。
“若是不能为君上解忧分愁,为我大宋报效!留我这把报国长枪有何用啊?”李飞又饮了一大口,酒顺着李飞的花白的胡子滴落在高楼的围栏之上。高楼之上,一老者负手与月同消愁。高楼之下,灯火阑珊……
城南的客栈中,月光皎皎,从窗外氤氲进来。扶子安在月光下跪得端正。今日是上元节,他要悼念程夫人。他跪了将近一个时辰了,只是望着月亮。程夫人一人在幽都,(幽都是人死后化成的鬼,灵死后化成的魔,妖死后化成的怪所居住的地方,永夜无白昼。)不知她过得可还好。在幽都可还有小鬼听她弹琵琶?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贤弟在否?”南流景敲了敲门。南流景是一个爱喝酒的人儿,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今日是中元,祖君已经走了好久了。他去买了两坛秋露白,本来打算自己一个人喝的,瞥见扶子安的房中还点着灯,便知道了他没有出去。南流景是一个爱说话的人,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正好扶子安在房中,也有人听他说话了。
扶子安回过神来,缓缓起身“在的,流景兄,这便来了。”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再将自己的衣裳从上至下理平了。走过去开了门“流景兄里面请。”
南流景却不进去,晃了晃手中的秋露白,“今晚月色甚好,咱们出去喝酒吧。”
扶子安轻笑道:“多谢流景兄好意,不过还是流景兄独饮的好,我实在是不胜酒力。”
南流景一把将他从房中拽了出来,“我不管,今晚你就要陪我喝酒。”
扶子安摇了摇头,“年方少,还是不益饮酒。”
南流景问道:“您贵庚啊?戴冠了吧?还年少呢,又不要你喝多了。配兄长我小酌几杯便是了。”
扶子安知道自己是拒绝不了了,还是勉勉强强答应了。
南流景一个翻身跳上了房梁,“这里高,好赏月,一起上来吧!”
扶子安心里是觉得上梁的确是不雅的,若换做是其他人,想必自己是一定会拒绝的,但是此时的自己却不知道是怎么了不想管那些礼节,也一跃上了房顶。
南流景扔给他一坛酒,一屁股坐在瓦片上,支起一条腿,“接好了!”扶子安一下接过,“没想到,一壶酒的分量有这么足。”扶子安轻笑,银白的月光在他白皙的脸上铺开,眼中映着寒星,他头上白底的皎月逐云发带闪着微微的光,梨木簪显得光滑而圆润,鬓角一丝华发似乎要度到他面颊的另一面去,趁着晚风在风中轻扬。
南流景见他那模样,的确是好看,“别说你真是长得人模狗样的,还真像一个如玉公子。你这模样出去,别说还真会有小姑娘喜欢。”扶子安没怎么听清,便盘腿坐了下了,端正地挺直了背“什么,流景兄可否再说一次,我方才未听清。”
南流景心中想到,这傻小子这么呆笨,想来也是不会逗小姑娘的,谁会喜欢他啊,我也是傻了才会问他这个问题。南流景一摆手,“没什么。”
南流景目光滑过天空,锁在了天上玉盘般圆润而又白又亮的月亮上,举起酒坛豪饮了一口,“你说,幽都的月亮也像这般圆吗?”
扶子安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他问得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南流景的语气很正经,全然没了之前那番嬉皮笑脸的模样:“你看的书这么多吗,也不知道吗?”
扶子安心中有着像他一样的愁绪,眼中的星黯淡了,“是啊,才识粗鄙,要是知道就好了。程夫人可还安好?”
“可有人听她弹琵琶?”扶子安眼中的月亮很沉。
南流景接了话,道:“祖君生前最喜欢喝酒了,每日早晨晨练前一定要来一碗秋露白。祖君的寝居后那棵梧桐下埋着他自己酿的秋露白。他总是躲着我喝,他以为我不知道他私藏着,其实我都偷喝过好几坛了。”南流景说起这话时,嘴角勾了起来,藏不住的笑意。
“老头儿啊,酒量也的确是好啊!我喝得烂醉如泥时,老头儿还能在梧桐树下舞剑。”笑意更浓了,露出两个虎牙。
南流景又举起酒坛饮了一大口,浊酒辣喉,南流景眉头皱了皱,“老头儿最后一次与我喝酒那月亮也同今日一样大。”笑容就像一团火被浇熄了,僵在了脸上。
扶子安问:“流景兄,可有想回过桐山?”扶子安说的很慢,他不知道这话当不当问。
南流景一声轻哼,“以前想过,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一个地方就是那里的人和事让人怀念,祖君都不在了,我偶尔会想起以前同昌意兄一起去后山抓鱼,比射箭,比骑马……现在昌意兄都与我一起了,想那个地方做什么?”南流景淡然道,别说还得感谢这个呆瓜,不是路上救了他,自己也不会来到这里,不会再遇见昌意兄。
“更何况现在的桐山,有招昌平那个卑鄙小儿……”南流景又饮了一大口,袖子用力扫过嘴角。“说他让人恶心,我要是回去了,首先要他的项上人头!”
“说其他的吧。”南流景话锋一转,又笑了起来。
“我同你说,那时我还小得很,大概两百多岁吧。每日都被关在桐山读那些没用的东西,想下山都没一点办法。祖君请一个白胡子的老木头教我《尔雅》,我对那些什么辞意真的是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一个个字摆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觉得头晕,那老木头讲得也着实是枯燥乏味,我日日听着都觉得昏昏欲睡学,一年下来什么都没有学到,那个老木头就罚我,拿戒尺打我,他也真下得了手,把我手都给打肿了,小爷我这么俊一个,打残了怎么办?为了不让那老木头打我手板,我就把他戒尺给偷了,后来那老木头居然跑到祖君那告状,祖君就罚我七天之内抄《尔雅》二十遍,谁受得了啊,这么厚一册,抄下来手还不得断了。”
“你猜怎么着,我可想了个好办法,你猜是什么办法!”
扶子安笑着:“我如此愚钝,又怎么猜得到?”
南流景喝了一大口,又露出了两个小虎牙,“就知道你猜不到!我告诉你吧我托鸿雁下山去买了一副《尔雅》的文印章,一张一张印上去,不到一天我就‘抄’完了,怎么样小爷我是不是好聪明,真是机智过人!”
南流景脸上尽是得意,抬起手啪得一下拍在扶子安肩上,“你就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吧!”南流景又想了想,说到“你这么呆讲不定还真的就抄它个二十遍。你……不会连人都没骂过吧?”
扶子安很郑重,“有过。”
南流景突然来了兴趣,他实在不会想扶子安这样的方正人会说那些粗俗话,追问道:“真是想不到,说来听听。”
扶子安提起酒坛,也学着南流景举起来喝,他这么大都没喝过酒,一下就被酒呛得直咳嗽。南流景笑他,“真是,还真不会喝酒。”拿出自己的纳川囊,那里面有杯子,是之前在永安城黄金台下住宿时偷拿出来的,他还没找到好人家卖呢。“呐,给你个杯子。”
扶子安接过来,“谢过流景兄。”扶子安倒了一小杯,小酌了一口,抿了抿嘴,皱起了眉。
扶子安道:“那是幼学之年。母亲女子身,不便上街市。我替母亲去买面粉,常去的那家店铺掌柜不在,掌柜的儿子守店。我去买面粉,他不愿卖与我。他道‘不卖与抛头露面之人的儿子’。”
南流景望见扶子安坐得端正,但是放在双膝上的手早已紧紧握成拳。
“他道我是娼妓之子。”扶子安面上无怒色。
“我气不过,便回他‘畜生’。我至今任觉得他连畜生都不如。毫无修养!”扶子安字字慷锵,显然是在强忍着火气。
“我若是你,便要将他舌头扯出来打个结,让他知道话是不可乱说的,以后定教他不敢再犯。”南流景道,“这太便宜他了!”
扶子安苦笑,“母亲道那是污秽之言,我说完只觉得解恨,却未曾想到自己已经给母亲抹黑了。”
南流景又拍了一下扶子安肩头,“我就觉得你做得对!没有抹黑的这一说,你想那么多作甚!”南流景拿过扶子安手中的酒,“这酒想必你也不会喝了,还是给我吧。”
扶子安突然笑了,“南流景一名太阳。”
“你说什么?”南流景问。
“南流景别名太阳。”扶子安答道。
南流景也笑道:“你从哪里看来的?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己都不知道。”
“古人有诗云‘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
南流景不喜欢听这些金句,跳了起来“酒都喝完了,睡觉吧,明早还需要赶路呢!”他同扶子安说了些话,心上罩着的那一层阴云消得差不多了。
二人下了房顶,休息去了。夜已深,明月依旧白净如玉,不知可有人对月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