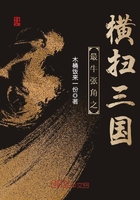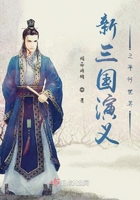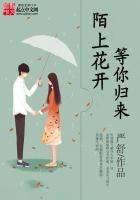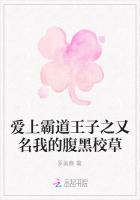丞相范承渊见文武大臣交头接耳,转身出来对着身后的所有文臣武将说道:“不要吵了,我大良朝地大物博,国力雄厚,他北邪国只不过蛮夷之族而已,有何惧哉?你们切勿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申安皇帝连连点头,赞道:“知我者莫如范相!尔等休要再言。”
“那…陛下,”此时又站出一个一个文官,众人一看,是刑部尚书应善桂,“这猲狙尸体该如何处置?”
申安皇帝走下台阶,再次围绕着猲狙的尸体做了一番打量,但也迟迟没有想到好的处理办法。
“你们说,这猲狙该如何处理才好?”申安皇帝环视文武众臣,问道。
大家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一个人应答。
申安皇帝等得焦急,于是主动发问:“范相,你是众臣之首,你来说说有何想法。”
范承渊为相几十年,一直跟随在申安皇帝左右,深知申安皇帝脾性和喜好。他知道,申安皇帝最喜欢的就是这些稀奇之物了。
于是,范承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陛下,依微臣之见,这猲狙世间罕有,恐怕其他许多国家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然大物,如果能够在世纪庆典上让其他诸国都见识见识,岂不更耀我大良国威?”
“哦?”申安皇帝觉得这个想法甚是奇妙,“那你的意思是?”
“将其制成标本,待世纪庆典到来,让诸国共同观瞻!”
此话一出,申安皇帝顿觉欣喜,“好!不愧是我大良丞相,深知我心,没白跟我这么多年。就依范相的想法,将此兽制成标本!”
说完,申安皇帝就将这件事交代给了礼部尚书崔平,要求他在世纪庆典到来前务必将此事办好。
但是,崔平却很是犹豫,他欲言又止。
作为礼部尚书,崔平主管大良朝的礼仪、祭祀、宴餐、教育和外事活动等内容,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长,深知这猲狙为北邪国国王所养爱兽,死了就算了,如果还将其制成标本让他国欣赏,必将让北邪国国王哈胡能怒火中烧。那时,恐怕两国关系就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申安皇帝见崔平一副为难的表情,问道:“崔平,你是有什么意见吗!”
“微臣不敢。”崔平连忙否认,说道,“只是,微臣认为,这猲狙伤人性命已经伏法。刚才那北邪使者也说了,猲狙乃北邪国国王哈胡能所养爱兽。现在,哈胡能痛失爱兽,如果还将这猲狙制成标本让其他国家前来观瞻,恐怕会激怒哈胡能。”
又是北邪国,申安皇帝不明白,这帮大臣怎么就那么怕北邪国。他心中很是不耐烦,沉着气问道:“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微臣认为,可让北邪国使者团将猲狙尸体运回北邪,并让我朝使者携带一封帛书,说明猲狙一事来龙去脉。如此,我朝与北邪之间定能友谊长存。”
毕竟还是礼部尚书,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
其实,崔平所说的这个做法对于眼下的大良国来说,算是最好的选择了。大殿上的文武群臣虽然明面上不说,但其实内心都知道,大良朝虽然表面看着一副兴旺之相,但其实已经像是烂了心的苹果一样,危机四伏了。
而导致大良朝外强中干的原因,归结起来,无非就是申安皇帝“不务正业”,只专注于自己的喜爱之事而少理政务。并且,申安皇帝在许多地方还挥霍无度。
不过,一个这样的皇帝,如果能够有贤臣良将辅佐,那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在申安皇帝旁执掌大权的丞相范承渊,并不是那样的人。如果说得骨感一点,也就一个奸相而已。
对比起来,北邪国虽然在文化、教育、礼仪等方面不及大良朝,但唯独有一点,却是让周边所有国家都惴惴不安的,那就是军事。
如果要打个比方,这北邪国就像秦汉时期的匈奴一样,它在大良朝的眼中也只不过蛮夷之族而已,但其军事实力却不可小觑。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大良朝要跟秦汉比,还是差了些。秦朝时期,秦始皇虽残暴,但作为带领中国历史走进新篇章的第一位皇帝,确实又可以说得上是雄才大略的。
到了汉朝,虽然在汉武帝之前,汉帝国也是匈奴羞辱践踏的对象,还发生了让刘邦一辈子都感到耻辱的白登之围,以及让吕雉也只能忍气吞声的来自冒顿单于欲娶之为妻的戏谑,但汉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却无一不是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申安皇帝听了崔平之言,内心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但是,对于猲狙这种稀奇之物的喜爱,却让他有些拿不定主意。
如此异兽,好不容易捕获到手,申安皇帝还想着要按照范承渊所说制成标本展示给相邻各国观瞻,现在这崔平却建议将其送回北邪。一想到这里,申安皇帝就心有不甘。
他扫视了一下群臣,问道:“你们,都是这样想的?”
群臣却都低头缄默不语。
范承渊见大家不敢说话,如果皇帝照着崔平的建议做了,那自己岂不是没了权威。于是,趁申安皇帝不注意,范承渊就给了刑部尚书应善桂一个眼色。
应善桂瞬间明白了范承渊的意思,出来说道:
“启禀陛下,微臣认为,北邪虽然不可小觑,但其综合实力远远差于我朝。况且猲狙一事本就是北邪有错在先,他们还敢大闹朝堂。如果我们不坚定立场,给他们瞧瞧我们的态度,他们定会觉得我们怕了他北邪国。到时候,北邪国只会更加不把我大良朝放在眼里。所以,微臣认为,应该如范相所说,将猲狙制成标本展示给诸国,既能向北邪表明我们的态度,又扬了我大良的国威。”
话刚说完,范承渊就接着出来说道:“没错,区区北邪蛮夷,岂能就被他们吓破了胆?”
申安皇帝思索片刻,而朝中众臣也开始讨论,他们意见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