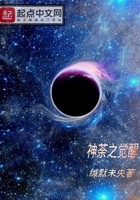金兵撤退,兜兜转转,这赵构总算到了他牵挂的杭州。
杭州鱼米之乡,富庶安逸,江河湖泊众多,交通方便,对饱受流离之苦的赵构,就是个进退自如的天堂。
他累了,不想走了,做了皇帝四年多,还没品到它的好滋味,愧对上天啊!
为堵住悠悠之口,骂他忘了国仇家恨,蝼蚁贪生,乐以忘忧,赵构将杭州改为了临安。
临安——临时的地方而已,我没忘我的家,没忘我的恨,我要北伐救我的父兄,我还要回去的,只是卧薪尝胆而已。
明珠抱着手,远远站着。
这是好大的院子,几进几出?夜幕中连它的阴影都伟岸至极,“秦府”二字,夜色下依旧熠熠生辉。
近乡却情怯,明珠百感交集,她终于找到了家!
自记事以来,她就跟随着漂亮师父漂泊流离于江湖,身似浮萍,就算很小的时候,心蕊也能将她独自的丢弃在陌生的环境之中,多少次梦里惊醒,抱着手颤抖着偷偷的哭泣,就像无根的野草,最怕风雨雷鸣时,无依无靠、命若悬丝。
尽管她在人前努力的笑,也只是人前虚伪掩饰的最后倔强,被强行吞下肚子里的泪水,只有她自己知道是什么滋味!
所以完颜亨曾经拥着她低语的“有我”两个字,被她怎样的视如珍宝,可当完颜亨给了她这两字承诺时,她对这梦寐以求的东西就这么唾手可得时,却胆怯得退却了,亲手推开它,不敢要。
家,只有天才知道它在她心中是个多么渴望的位置?
泪儿在她眼里打转:爹娘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可还挂念着自己,还记得这个流浪的宝宝吗?
明珠弹拨着自己的鼻子尖尖半天了:明天,明天得给爹娘准备点什么非凡的礼物才好,什么礼物呢?
世间最好的东西是不是在皇宫里?
她想到用青鸾宝剑比着赵构的脖子,逼他交出他最宝贝的宝贝,一个目指气使天下的皇帝,会是种什么表情?
想着想着,心中的欢喜就不言而喻,手痒得难以自己。
那偷爹娘的呢?将他们藏得最深的宝贝偷出来,再突然送给他们,他们又会是种什么表情?
西里古怪的,那鸭子一样的大笑就要冲体而出,乐得明珠浑身打颤,像正在枝头摇曳的梨花,带的都是使坏后兴奋的露水。
这个主意是金子提的,干坏事又怎么少得了他?唉,这个臭坏蛋!
明珠以为自己花了眼,久走了夜路今天居然撞了鬼,什么小贼竟然敢偷到了她这个贼祖宗亲爹娘的头上?自己都还只是在盘算,还没有动手,小贼的胆子太大,居然先下手偷到了贼祖宗的家里!
他从那个挂着“秦府”的院子,院子一个不起眼的墙头,跳出来的。
不经意地环顾四周,抖了抖他的衣,一摇一摇的,走了。
还是那不紧不慢的举止,那个混蛋金子!
只是一眼,明珠头那么一晕,心莫名的就乱了,那股翻腾着她不认可的醋意又来了。
不见就不见,许久不见,他们再没相见,为何又要见?老天爷无聊得很,就会戏弄他脚底下的凡夫俗子,你求而不得,不求他却偏要硬塞给你。
那日气起离开,他也并没有再找寻她,没有一个解释,却能厚着脸皮的跑到轻云姐姐那里假惺惺的卖好,装出一副痴情儿男的惨象。果然不过是个说惯了疯话的放荡公子,习惯了身边流水的女人,而她,就是他一时兴起,想要挑逗和征服的女人中的一个。
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居然好像某一天还为他动了心,以为自己会是他的例外……哎,蠢材!
她以为这个不值当的臭东西,自己已经忘了——就像极小心的藏起了她曾经心爱的小宝贝,比如说素淡色的小花花、比如说漂亮师父给过她赞许的一个笑、比如说曾经她极想要拥有的像仙女才可以穿着的霓裳羽衣,还有很多她曾经想——却得不到的东西、些。
偶尔一个瞬间心会抖,不过就在那么一个瞬间而已,不碍事的,她会乖巧的把它忘记,真的不碍事的。
既已忘记,为什么还要来打扰自己,他又怎么胆敢来偷自己家的东西!
明珠不由自主地跟着完颜亨。她宽慰自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她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后悔到绝望。
夜深人静的时候,完颜亨走得不急,这里的大局已定,他已无再留下来的必要,他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看来是等不到了。
消息早已经放出去,这小傻瓜怎么还没到?
醉红轩一别,完颜亨知道这个让他爱“恨”的小妮子生气了,待得他处理好完颜宗弼追赶去的时候,明珠早就失了踪影。
她行侠仗义的胆子向来与她拥有的真功夫不匹配,幸喜后来习了霓裳神功,可小傻妮子的胆子就越发的大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她劫了一个官史的财物,殊不知这官史是个硬货,请有几个武林的高手,这可让这些高手丢了颜面,誓死要抓到她。
可这小妮子偏生又是个爱财的主,心心念念的只想给她的岳爹爹找军饷,背着那老多的财宝都不舍得丢,才跑十来日就让人给堵了,幸喜她拼死拼活的已经跑到了岳家军附近,小脑瓜又灵活,易了容堪堪蒙混过去。几人看是军队不敢妄动,一直就在营外等着她。等完颜亨追到时,岳飞和岳云都不知所以然,只知道明珠扔下一包钱物已经闪人,而后,完颜亨就再得不到她的消息。
他气这傻妮子为了给岳飞劫这点钱财连命都不要了,这糊涂脑子,还自诩着自己聪明。
回香暖阁依旧没寻到她的踪影,完颜亨无奈只好丢下消息,来到临安,着手秦桧的事。
现在连临安的事都了了,这小妮子还是渺无音信,难道她又闯了什么祸出了什么意外?还是上次真的伤得她太深,小妮子决绝地再不要见自己?
完颜亨后悔了,这颗心总为她放不下,更着急了。
“大郎。”
金铃儿总是一团不停息跳跃着的烈火,完颜亨一进门她就飞过来,环着吊在他的脖子上嗲声问到:“明天我们真的走吗?这次你一定要随我回家,孩儿们可都念着他们的阿爹呢!”
“好。”
完颜亨笑着应道,轻轻在她额头上印了一口:“你先回去照看着,功夫我倒不担心他们,一群好武的狼崽子。切不要让他们荒废了文化,特别是我留给他们的书。
我随后就回,懈怠松懈的,别怪我到时候的手重。”
他嘴里说着手重,却难掩父严子孝的温柔,烛火晃动的是他满脸盛不下的父爱,再不是那般不屑万物的轻薄。而这女人,隔看窗都能感到她的热辣,但绝不是那一种。
明珠晃了晃,这才是他的家,他的妻。他嘴上从没有、心底也绝不会有的虚情假意的真正牵挂。
“谁!”
就这么一点点稍微浮躁了的气息,就这么被完颜亨警觉了。他抓起桌上的茶杯随手打了出去,一个翻身追出了窗门:好大的胆子,自己竟没有查觉,怎会这般大意?
夜幕中,明珠还是回过了身子,脸上襟前湿了一大块,好重的手。
就那么一失神,他的茶杯就打了过来,痛的是哪里:身子,还是心?
她气自己:要走就走,何苦还回头?还想要个怎样的结果?
“宝宝!”完颜亨惊了。
明珠面如木雕,一丝冷笑。
日日夜夜萦绕在心尖的人,就这么站在了面前,突然得没有一点准备。完颜亨算透了一切,却没算透明珠会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么突然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她看到了什么,她知道了什么,她在想什么?
条件反射的,他慌乱的穿戴着被金铃儿解散了的衣带,心完全乱了!
“你可还好?疼不疼?怎么也不会躲,就这么......”
完颜亨跳上前就想要看她的伤,他恨自己出手怎么这么重,一心只想要截住这个“贼子”,用了八成功力,非死则伤,怎知会是她,最想见又怕见的人儿。
明珠冷冷躲开完颜亨伸出的手,它沾了多少胭脂,多少朱红,多少泪水和女子的肌肤?
“宝宝,你别走!”完颜亨求着她回旋了的身子。
这声音,因害怕而微微发抖,似在哽咽,似在哀涕,在记忆的深井里,它就是那么一遍又一遍的呼唤她,涌出来,慢慢侵吞的她。这动情的声音,真的还是假的、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