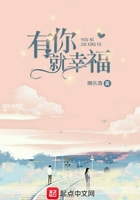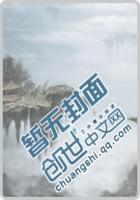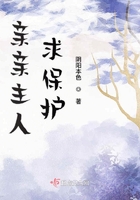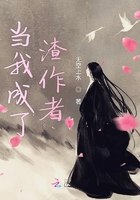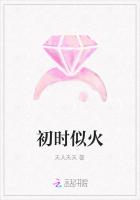小时候,我们看露天电影常去的有三个地方:研究所、自来水公司和我们厂区街坊。
研究所离我们最近,就在我家房后,过条马路就到了;自来水公司也不远,在马路斜对面;我们厂区街坊距离稍远一些,在新医院的对面。
有好电影时,小伙伴们就开心地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兴奋,天还没黑就急着出门。
看电影要提前“占地方”,好位置一般在电影幕布的正面正中间,不靠前也不靠后,太靠前了要使劲仰着头才行;太靠后了,如果前面有大高个挡着也不行。
我们都不愿意在“反面”看电影,这样电影上的人全部是用左手写字,让我们很不习惯。
看电影“占地方”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地上用粉笔画个框框,框内写上“此处有人占”,去晚了占不到好位置的人就很生气,把“人”字改成“儿”字,“此处有人占”就变成了“此处有儿占”。
第二种方式是:在地上铺张破凉席,或者把靠背椅放倒,尽可能地占用更大面积。
第三种方式是:家里先派人去占地方,其他孩子赶紧回家搬板凳。占地方的孩子一般都两条腿叉开,像圆规一样,有人来放凳子了就会着急地说:这里有人占了!像捍卫自己家的领土一样,谁先来谁先占领。
但是,也有不遵守“规则”的大男孩,他们从来不占地方,在放映正片前的《新闻简报》快要结束时,就搬着一个高板凳穿过人群往“最佳位置”处挤,也不管自己的身影投在影幕上,边挤边大声叫喊:我脚上有粑粑,让开!快让开!这时,人群就自动闪出一条通道,大家唯恐避之不及。
看电影前,女孩会精心洗十几个软硬适中的西红柿,用花手绢兜着,看电影时和兄弟姐妹边吃边看,非常享受。
夏天,有上夜班的父母偷偷从厂里溜出来,用绿色烧水壶给一个楼门的孩子送汽水喝。
工厂里有两种汽水:一种是冰水,又凉又甜,小朋友们都爱喝这种;一种就是带汽的,有点儿辣嗓子还有点呛,喝多了会打饱嗝。
听爸爸妈妈说,汽水是只有在高温作业的工人才有权享用的,家长更需要认识把大门的人才能把汽水带出工厂。所以,能给孩子在看电影时送汽水的家长博得了小朋友的一致爱戴。
男孩们都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我不是太爱看,有的又反反复复演了好多遍了,台词大家都能背下来了,可是不看又没有选择,总比没得看强。
尤其是《南征北战》,我一次也没有坚持从头看到尾过,每次演到那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游击队长领着老百姓大撤退的时候,我大脑就开始缺氧,进入混沌状态,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
也不是女孩子才会睡着,男孩也会,有一次电影都散场了,毛毛还没有回家,毛毛妈问一起去看电影的小伙伴,小伙伴说他睡着了叫不醒。
毛毛妈到了放电影的地方,诺大的场地只有毛毛一个人躺在凉席上酣睡,连放电影的都回家了。
看完精彩的电影,回家的路上大家会兴高采烈地讨论一路情节,毫无困意;如果是不吸引人的情节,大家就困得东倒西歪,走路都属于机械运动,本能地朝前迈腿。有一次去研究所看电影,回家的路上,其他门栋的孩子还掉在路旁的排水沟里。
我特别喜欢看“抓特务”的电影,尤其喜欢看女特务出场,当身着漂亮旗袍,烫着时髦卷发,叼着香烟、包里放把小手枪的女特务款款出场时,我眼睛都不带眨的,觉得她们比梳着齐耳短发,拿着杆长枪,灰头土脸、满地打滚的女游击队长好看多了。
《英雄虎胆》中那个女特务阿兰跳舞的场景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就因为这个,我内心痛苦纠结了好长时间,一直觉得自己思想有问题,不像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好孩子。
我第一次经历抓“特务”是和同学小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觉得前面一贼头贼脑的男人像极了电影上的特务,他腰间鼓鼓囊囊的像别了把手枪,我们觉得不能让他跑掉,就在后面尾随着跟踪他到了汽车站。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特务”也发现了我俩,我们商量:真打起来我们也打不过他、没准还会被他灭口,所以,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乘车逃跑了。
我对电影上的接头暗号耳熟能详,经常和小伙伴们学着电影上的样子对接头暗号:什么“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名字?——《阿里拉》”;什么“捉贼——捉脏;捉奸——捉双”。
虽然我对《钢铁战士》中那个画着细细眉毛的女特务对张排长施的“美人计”一窍不通,可这丝毫也没有削减我对电影的由衷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