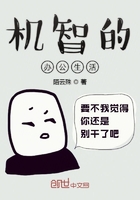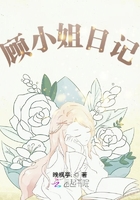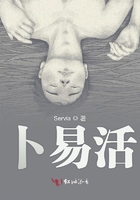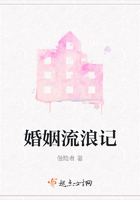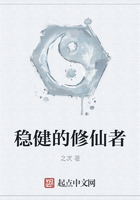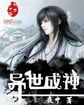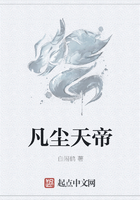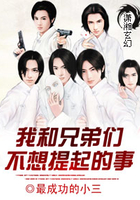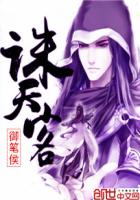徐林离家出走还没有回来。
我把每天晚上在家写作业的习惯挪到了阳台上,高方凳当桌子,坐在吃饭用的小矮方凳子上。能磨蹭到多晚就多晚。
徐林妈妈白阿姨经过时还夸我:安雪到底上中学了,学习越来越用功了!她当然不知道其实我是在等徐林。
小学我和安雨写作业一般都是趴在床上写,几乎每家的学生都是如此,有专用写字台的家庭很少,虽然老师一再强调说床的高矮软硬不适合在上面写作业。
有次钢笔不下水,床单上还有我甩钢笔时甩出的一串钢笔水滴。
中学留的作业多了,安安睡觉早,再说暑假时我经常在阳台上写作业,妈妈觉得挺好:省电。
所以,这个举动也没有引起爸爸妈妈的怀疑。
徐林在家的时候,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把徐伯伯和白阿姨的两辆自行车扛到四楼,我很少看到徐喆和徐炎干这活儿。
我觉得徐林除了学习不好外哪都好:厚道、随和、不斤斤计较还热心肠。
那几天,听到楼梯有动静我就赶紧趴在四楼扶手上往下看,看到是三楼的邻居回来了就万分失望。有时我会瞎想:徐林会不会已经饿死了?
终于,徐林在离家的第七天晚上回来了,我一看到他脏兮兮地穿着那件几乎成黑色的“港衫”,眼泪一下就涌出来眼眶。
我急切地问他:你去哪了这几天?
他把食指放在嘴上,做了个“嘘”的动作,小声说:回头告诉你。就进了家门。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落魄与灰溜溜,徐林家一切都像没发生似的该干什么干什么。
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大人们上班,孩子们上学,该吵架的吵架,该打孩子的打孩子。楼上的邻居们更是如此,除了我,也许有人根本还不知道徐林“消失”了七天。
我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总是感到莫名的失望,无论是对父母对老师还是对同学,他们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应该有的样子,包括对我自己,也失望透顶。
我不喜欢和人说话,喜欢自己待着,要么听广播,要么看书,只要是没看过的汉字,都能激起我浓厚的阅读欲望。
妈妈经常说爸爸是“哪不痒往哪挠”,花钱大手大脚,不像是穷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永远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其实内心非常感谢爸爸,他顶着吵架的压力,愿意花钱给我们订了那么多不同种类的报刊杂志,这些书使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那么乏味,也使我变得越来越爱遐想。
每个季度妈妈都会如期和爸爸大吵一架,因为没有经过她的同意,爸爸又在单位直接订阅书籍了。
我虽然很讨厌他们吵架,但这些书足以抵御妈妈无休止地抱怨与牢骚,这些书也是我抵抗他们下次争吵的盔甲,我觉得很值得。
每当看到爸爸下班故意把手背在身后,我就知道:新杂志来了!我和安雨总是争着去抢,想先睹为快,连饭都顾不上吃。
爸爸订阅的有《向阳花》《连环画报》《故事会》《奔流》《大众电影》《辽宁青年》《小说月报》《中国青年》等等,这些书使我爱上了阅读,这个使我终生受益的习惯。
每到放寒暑假,放假的第一周我就把所有的假期作业全部完成了,剩下的大把时间就全部用来阅读小说,想想都觉得兴奋不己。
爸爸会把单位同事不用的图书证都借回来给我,好让我去图书馆一次就可以借回一大摞儿的小说。
借到喜欢的书,读完之后,我常常舍不得还,放几天,再放几天;有时读到精彩的篇章,看到有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其中的几页纸撕掉的现象,我的懊恼之情无以言喻,然后,我就“续编”中断的情节……
我多么希望自己有能力把喜欢的书全部买回家来阅读,想想今后长大了了,我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再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拥有一柜子一柜子的书,这是我当时做过最奢侈的梦!
我是如饥似渴地热爱这些文字,它们就是我打开这个世界的唯一窗口啊!
冀鲁豫,晋陕甘……我国东邻朝鲜,南接越南、老挝、缅甸,西南和西部与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
我默默地看着这些由不同笔画构成的地名和国家,抚摸着这些代表不同含义的汉字,尽情想象,想象有一天等我长大了,我终究会亲临“现场”,将它们一一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