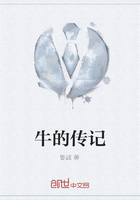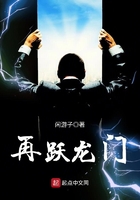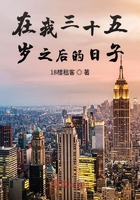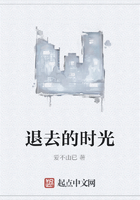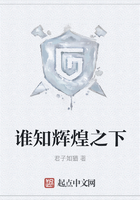王洋说他母亲早就托人买好了木头,木板是一块一块仔细挑选的,连上面的木纹都是专挑好看的、对称的。
他说:“在医院工作就是什么行业的人都能接触到,医治好病人的疾病,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他们往往铭记于心并等待机会报答,所以,有什么事还不等开口,他们就会主动提出帮忙……”
王洋的话很触动我,我们厂有很多两代人都在这个工厂的家庭,有的甚至还在一个分厂,父亲和儿子是一个工种,母亲和女儿是一个工种,说到儿子时往往牵扯出爹,议论母亲时也不免捎带上女儿。如果父母能为儿女长脸的还好,有的不但不能长脸,而且还给他们抹黑。
有的工人在一个班组一待就是一辈子,身边就那么三五个人,勾心斗角、斤斤计较,为多长半级工资往往撕破脸皮,就像井底的青蛙,误以为整个世界就井口那么大。一个小小的组长、小小的段长手中仿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得罪了他们照样吃不了兜着走。更别提出了工厂的大门了,哪怕只是芝麻大的小事,提着礼品都找不到门。大多数普通工人的一生就这样窝在一个小组悄然度过……
王洋和我说,打什么款式的家具赶紧定下来,师傅这两天就可以开工了,他父亲连打家具的场地都找好了,在王洋亲戚家一个闲置的平房里面。我找了几本有关家具的杂志,把喜欢的组合家具款式都折叠起来,准备下班去王洋家商量商量。
打家具的木工师傅有当地的,也有江浙一带的人,有的喜欢找当地的师傅打,觉得便于沟通;有的喜欢让江浙的师傅打,认为他们做活更细一筹。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我们家楼支起打家具的棚子,这样我和小朋友们便可以借着里面的灯光,在楼下多玩一会儿也不会感到害怕;我还喜欢站在干活的师傅旁边看他们刨木头,看着刨花一卷一卷的从刨子上方翻卷出来。
见到王洋我问:“怎么不在你们家楼下搭个棚子打家具呀?交代师傅什么事的也方便。我们厂区街坊里面都是这样的。”
王洋笑着说:“我们医院家属院好像还真的没有过……”又说:“我爸找的平房也不远的,原来有人住,后来亲戚搬走了,里面一直空着,如果合适咱们结婚也可以住在那里,连房租都不用给的。”
我说:“真的?要不咱现在就过去看看?”
从内心讲,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平房,因为它总是让我想起老舍的《龙须沟》场景,觉得那里都是文化层次不高、生活在最底层的小老百姓居住的地方。但是,王洋说的免费居住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毕竟每月五十元的租金对我们也是不小的开支。
从王洋家出来,我们便往他亲戚家的平房骑去,房子在百货大楼的后面,平时去逛街我根本没有留意到还有几排平房坐落在这里。
除了高中时去周美芝家,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平房区域。这里的房子比我多年前去周美芝家那里改进后的“单身宿舍”好了许多,两排房子的间距可以让三轮车轻松通过,几个拿着树枝玩耍的小男孩兴奋地跑来跑去,看到我们热情问:“你们找谁?”
王洋逗他们道:“就是来找你们玩的啊!”
其中一个小男孩说:“我们根本不认识你!”说完就跑了。
因为是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飘出饭菜的味道,和斥责孩子的怒骂声,同时还伴着播放新闻联播的广播员抑扬顿挫的声音,很是具有烟火气息。
进到屋里,里面有股潮湿的味道,我赶紧打开窗户通风,好让霉味散一散。这个平房有里外两间房,外面的是厨房,里间是卧室,屋里有一个婴儿车和一张单人床还没有来得及拿走,床上零星散落着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子。
房屋靠墙处码放着高高的木板,门口堆放了一些木工常用工具。
我问王洋:“师傅已经来过这里了?”
王洋说:“是的。他们在这里住、做饭都挺方便的,天慢慢凉了,总比住在帆布棚子里面好……”
我点点头说:“是的。”
王洋又问:“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我摇摇头说:“不好,太破了!再说……我不喜欢平房。”
他问:“为什么?”
我说:“像旧社会……”
王洋“呵呵”笑道:“真能联想。好多老人就喜欢住平房,觉得接地气!”
我说:“我不是老人,等老了再说吧!不过,我觉得我老了也不一定能喜欢平房……苍蝇蚊子的‘嗡嗡’叫,太不卫生了!”
王洋说:“不喜欢就不住这里,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说着他走过来揽住了我的腰。
我警惕地拨开他的手,瞪着他问:“你想干吗?”
王洋无奈地苦笑着说:“你能不能不要像防敌人一样防着我……我们都是要结婚的人了,你能不能不这样了……”
我故意神态轻松地气他:“要结婚不假,可是还没有登记呢!我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王洋紧追着问:“登记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说:“哪也不一定,到时看情况再说!”
他走过来,把我的双手放在后背说:“你哪里是什么‘三好学生’?‘六好’都不足以形容你!你简直太听老师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