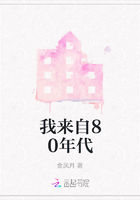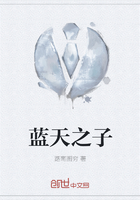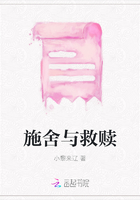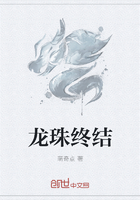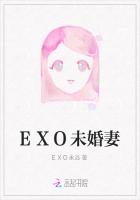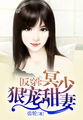我劝安雨复读一年,她虽然嘴上说“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但对走向社会还是有些恐慌的,她内心一直认为参加工作是大人们的事情,而她自己不过还是个孩子。
父母和我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虽然他们没有那么明确地表态。现在爷爷奶奶早已去世,叔叔姑姑也都成家,父亲老家这边基本没有什么经济负担要承担了,再说我也参加了工作,家里的生活水平比原来好了很多。
安雨心里也是想复读的,可又担心母亲的冷言冷语,她知道“复读”本身就是让父母在经济上对她额外的付出,深感“理”不直“气”不壮。如果复读,接下来这一年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我对安雨说:“我们四人的意见比较统一,一致支持你复读一年。”
安雨疑惑地问:“四人?”
我说:“对呀!除了爸妈和我,还有王洋。”
安雨问:“王洋哥哥也支持我复读吗?”
我说:“当然,他是第一个支持你复读的人。”
安雨低下头说:“其实老师也希望我复读一年再考的……”
我说:“是呀,老师一定认为你有这个实力才鼓励你继续应战的!”
安雨担心地问:“如果明年再考不上怎么办?妈妈还不得吃了我!”
我说:“还没开始呢,就给自己下定论了,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安雨道:“我现在已经能接受自己高考落榜的现实了,虽然原因有很多方面,毕竟自己不够刻苦才是起决定性的,所以我谁都不抱怨,我这是自食其果……可是,我实在忍受不了妈妈的态度,虽然表面上她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可她难看的脸色比打我、骂我更让我难过!打完了,骂完了,一会儿就过去了,可她天天摆出那样一副表情我真的受不了!想到明年如果落榜,我还要再经历一次这样的‘非人待遇’,我宁愿放弃复读……”
我安慰她,无论什么脾气秉性的父母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一点上一定是相通的,母亲给她脸色,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动机也是对她高考落榜失望情绪的一种特殊表达吧,虽然其方式令人难以接受。可是,母亲如果想让她早点参加工作,一定会明确拒绝她继续复读的,但是,母亲并没有这样做。
安雨在大家的各种鼓励之下终于同意复读一年。既然决定了复读,接下来就是找学校。我们厂矿学校的老师当然希望安雨回到本校复读,毕竟安雨的高考成绩离分数线只差了十几分。然而,安雨碍于面子,说什么不愿再回到母校复读。她说:“只要不回到原来的学校,去哪里复读都可以,农村也行……”
父亲老家一个县高中,最近几年的高考升学率居高不下,甚至有一年还超过了市重点中学,现在知名度非常高,有好多城市家长都慕名托人把自己孩子送到那里借读。
听说那个学校管理非常严格,学生几乎已外界隔绝,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跑操,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熄灯睡觉,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为了确保道听途说的真实性,父亲居然还联系到他在农村上学时的一位姓肖的高中同学,现在就在这个学校当系主任。肖主任说,他们学校每年都招复读生,安雨的高考成绩也过了他们学校的分数线,去他们学校复读问题不大,关键是担心城市孩子吃不了这个苦,曾经有几个城市孩子就因为适应不了,没待几天就回家了。所以,肖主任希望我父母和安雨都考虑清楚,不然,来了又走,不仅影响其他学生情绪上的稳定,对学校的声誉也不好,请我们三思后再做决定。
我想到了我上高一时,有个叫周美芝的农村女同学因为老家的英语教学水平不行,才来到我们班借读的。这才不过几年的功夫,城市的学生居然要到农村的学校借读了,可见,这些年农村教育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校虽好,可我有些担心安雨的适应能力,我小时候起码还在乡下的奶奶家待过个把暑假,对农村还有个初步认识,我对他们肮脏的苍蝇“嗡嗡”乱飞、无从下脚的“旱厕”,和无论洗衣还是做饭都要出去挑水用的印象尤其深刻。记得那时每次上完厕所,我不仅要洗手,而且连脚也要拿着瓢舀缸里的水冲洗一下。
那时农村到处都是土路,我光脚穿着凉鞋,鞋里稍微进一点土我就要舀缸里的水冲洗脚丫。姑姑看我用水这么浪费,不高兴地说:“这一缸的水你自己一天就能用完……”那个在我看来巨大无比的放在院子里的缸是爷爷用水泥砌成的,叔叔姑姑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挑满它。
我那时太小不懂事,就向奶奶告状说:“姑姑说我,她不让我用缸里面的水……”
于是,奶奶就严厉地斥责姑姑,说她:“挺大的人了,还和个七八岁的孩子一般见识。”其实,那时姑姑也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
但是,安雨是个从小到大在城市长大的姑娘,这种生活上的差异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适应的了的。周美芝当年说她在加盐的开水里泡发霉的馒头当饭吃的话,还在我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