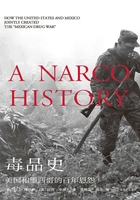这是一座二层楼木结构的法国式普通住宅,卵石嵌墙,呈深灰色。有人领蒋介石进入了会客室。趁孙先生尚未出见的间隙,蒋介石打量起这里的一切。客厅约二十四五平方米,进门的两侧陈放着红木茶几和老式靠背椅,左右壁上挂着四幅名人书法,正中有小圆桌和一套沙发,陈设简朴。透过门窗,但见庭院里绿草如茵,四周种植冬青、玉兰等树木,构成一道绿色的围墙,使这座院宅更显得朴素幽静。
正当蒋介石四下观望之际,中山先生穿着当时流行的蓝色学生装,从楼上下来,笑容可掬地迎向蒋介石。蒋介石鞠躬致敬,问候再三,然后喝茶,逐渐交谈起来,开始互相谈论自己的情况。
蒋介石愤愤然:“军中将领,界限甚深,互相排挤,凡是先生的追随者,必欲去之而后快,哪有容我之地!”当时蒋介石所在的福州之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军部,那些旧军官骄横得很,他们常聚在一起赌钱抽鸦片,只有孙中山莅临时起身恭迎,不敢造次。连总指挥许崇智都不放眼里,往往见许,抬抬屁股点点头,照旧卧在床上抽鸦片;蒋介石来,他们连眼皮也不抬,故意冷落他。而许崇智打了败仗,也迁怒于他。
“你还是回福建住所,此时更须坚忍耐烦,劳怨不避。”孙中山劝勉着。
“我根本无法执行参谋长职责,回去何用?”蒋介石变得固执起来,“离闽回沪,面请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唯有这件事,望老师准我不再回闽……”
听到蒋介石的这些话,孙中山默不作声地皱了皱眉,瞪圆了酷似列宁那样深邃的眼睛,仿佛要谈到什么十分隐秘的东西。
“你去吧,我们的事业已得到苏俄的援助和青年共产党的支持,去吧,唯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
是的,一场历史性的交往正在孙中山的寓所里秘密进行。1922年8月下旬,共产党人李大钊自北京来到这里,与孙中山多次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
孙中山已从陈炯明的广州叛变中,觉悟到单纯利用旧军人、旧军阀去打倒另一军阀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依靠工农大众,必须联合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走新的道路。同月,孙中山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国民党主要人员会议上阐述发动群众运动和改组国民党的意见。会见时,李大钊、林伯渠、宋庆龄等在座。孙中山吩咐侍从官无论何人来访,都不予通报和登楼,严格保守秘密。孙中山的这所寓所成为国共合作的发源地。
孙中山谈到这些情绪有些激动:“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治它,就需要新血液。我在不久还要派出代表团去苏俄考察,以便建立一支新军……”
蒋介石走出先生寓所,继续想他的心事。他如此不愿回闽工作,固然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和军费拮据的困难,然而更主要的还是蒋介石不满意他在军队中的地位。
孙中山倚重他,却一直没有授以实际军权,连小他八岁的邓演达也不如!也许孙中山觉得蒋介石在军中还缺乏人望,“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龊难合”,做高级参谋较为合适。蒋介石为此而愤愤不平,既然他有那种喜好冒险的天性,有一种侠客的激情,又喜欢显示复仇的本能,他决不愿甘居人下当一个没有实权的高级幕僚,他有更大的欲望,他总要在寻找扩大个人权势的道路上不惜代价,再冒一次险……1923年4月20日,蒋介石到达广州,以大元帅参谋长的名义进入帅府办公。
经常陪同孙中山视察,制订军事计划,慰劳各部队,但他手中仍无一兵一卒。不但滇桂这些客军不听指挥,连许崇智也不接受他攻打陈炯明老巢的计划。到任还不到三个月,他又一次辞职,离开苦战中的孙中山,回避到香港。
时间已经是7月中旬了。尽管蒋介石仍在闷闷不乐,但他又回到了无拘无束的世界,属于他的世界。但他对它多少有些不同了,也许是由于受了深深的伤害,他已无心欣赏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俄罗斯。先生说过的决定派出代表团去苏俄考察的事,一直牵着他的心。到达香港的第二天,他便按捺不住急迫,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表达他对孙中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在信的末尾,他对自己的处境又渲染了几笔:“倾轧之祸,甚于壅蔽,娼嫉之患,烈于党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他永远忘不了新旧军阀们卧在烟榻上,在许崇智面前竭力贬低他的身份和伤害他的自尊心时所发出的那种笑声。
这些是绝不会忘记的。他要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总有一天,他也会在他们面前发笑的。
蒋介石寄走信便返回宁波去了。等待又使他烦躁不安起来。他那强烈的怨恨刺破了长空,他的声音变得像锯木头一样刺耳。正在他失望和渺茫而痛苦不堪时,8月5日孙中山回信,答应由他和王登云、沈定一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军事,并有意让蒋介石回来办校治军。
蒋介石终于笑逐颜开。
蒋氏游俄如游太虚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行乘“神田丸”轮船自上海出发,由大连往东北地区,然后乘西伯利亚铁路列车前往莫斯科。从上海出发时,蒋经国、蒋纬国前来送行,惹得蒋介石思母情切,作《所感》一篇,哀叹:“从此道途日远,何时复得回乡扫墓,顾前思后,悲戚无异于二十年前初就外傅之日……”
8月,南方正是暑热天气,而西伯利亚的夜晚却寒气袭人。与白昼相比,黑夜更显得无边无际。大地上的一切,山丘、树林和迤逦起伏的田野,统统被抹去了,只剩下坦荡、黝黑的一片。而黑乎乎的树林上边,却展现着富有生气的夜的世界:
横亘在中天的银河,动荡不宁;朵朵瑰丽的云彩,浮动在整个夜空,有的像着了火的车辆或船只,有的像通明透亮的骏马;满天灿烂的繁星,恰如秋后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散乱的麦茬。
“怪不得苏武牧羊流放到这个地方。”蒋介石倚着车窗记完日记,使劲缩着脖子,交替搓着两只手,说话时牙齿有点打架,“夏天夜里都这样冷,冬天将如何过?”
精通英语的王登云从铺上揭了一条毯子盖在蒋介石身上。精通俄语的张太雷却在过道上做下蹲运动,小伙子的腰部和大腿显得格外有劲,躯干细细的,矫健而虎势,恰如一张弓。昏暗的车灯从顶棚照下来,沈定一已沉睡在铺位上。
9月2日下午1时,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有苏联外交官员来迎。当他们前往宾馆途中,碰到了成千上万的挥舞着红旗和标语的示威游行队伍。过去蒋介石只是听说和从书本上读到有关莫斯科的情况,那里有一幢幢古老的、石砌的、竖着一根根圆柱的私宅,有无数个蓝色、绿色的带金圆顶和金十字架的教堂,那里有一条条使车马颠簸不堪的鹅卵石马路,有先前从未见到过的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所有这一切都是新鲜而有趣的,因此,一路上,他如饥似渴地听接待者讲述有关莫斯科和红军的故事。
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正在放暑假,听说孙中山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蒋名什么,熊雄一拍大腿:“孙文手下姓蒋的人,莫非是蒋尊簋,那就好,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于是他们就天天盼着代表团来。终于来了,欢迎会场就设在学生寝室。一张长桌子旁边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就坐在床上。熊雄一个个辨认,见沈定一生有胡子,很威严,《新青年》
上曾读到他的文章;张太雷,魁伟而漂亮,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之一;王登云是个秘书一流人物,没有什么特别的;主任代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熊雄大失所望,他不是蒋尊簋,其他人也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熊雄本是国民党军官,他很纳闷:蒋介石——这个名字不见经传。开了会以后,学生们议论纷纷:
孙文为什么派一个无名的人当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定一,这个姓蒋的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10月10日,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吃饭。代表团公馆是旧时某贵族的邸宅,虽小却很华丽。熊雄他们又快活起来。虽然来的不是蒋尊簋,却在大厅吃了丰盛的大菜。饭后余兴,沈定一扶须舞剑,不料舞时剑脱手落地,他拾起再舞,旁观者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学生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他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他们加入国民党。他站着说话,一手扶着椅背,样子敦厚而懦弱。学生们私下议论,孙文为什么派这样无用的人?!
蒋介石却自我感觉良好。
临行时,孙中山嘱咐再三,一定要会晤列宁。早在1918年夏,孙中山就在上海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成功,这之后,他屡与列宁函电往返,只是从未谋面。他要蒋介石带去对列宁的敬意和问候。可是列宁在这一年的3月9日第三度脑溢血症发作,因而病倒,在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静养,虽然病体恢复到勉强可以扶杖行动的程度,却难以会客。于是,与蒋介石谈论最多的便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言论直率得令蒋介石吃惊:“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给蒋介石的赠言是:
“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