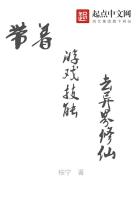青砖小径通向黑灰色的高大木门,踏过枯了的落叶,碾过青绿色的小浆果,她被人带到了这座私人博物馆门前。一千零一夜里念了咒语就可畅通无阻的藏宝山洞,流传到现世同样不必费吹灰之力即可心愿得偿。
她甚至都不需要真的取悦那个大魔王,他就心甘情愿倾力编排所有剧码,只为让她看到自己日月可昭的忠心。
除了诸如普拉多或是罗浮宫之类的第一梯队确实难以攻破之外,不论是家族收藏还是市面上不允许流通的硬货,他都有办法让她没有干扰地观赏。
不想出名的艺术家,不算是荣少爷的好妻子。
荣立诚认为他是连松雨的伯乐,他火眼金睛,从她制造出来的一众垃圾里翻出可以入眼的漏网之鱼,在那个慈善拍卖会上耗费重金拿下它,再千里迢迢地运去了佛罗伦萨,置在他位于阿尔诺河畔的宅子里。
荣立诚很想带她去看看那件作品,告诉她,唐嘉辉和连修然没能看上的东西,他看上了。
可是,在他告诉连松雨这几乎可以感动天地的美谈后,她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刚刚听到风声拂过,平淡地了无痕迹。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既然已经运到了异国他乡,我也没必要再重温旧梦了。”
“有你这样的艺术家吗,你竟然没兴趣了解自己孩子的现状?!”
“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我的孩子,你想多了。我们这种不缺钱的三流艺术家最大的本事就是闭门造车,至于能不能卖出去,全看缘分。反正家里有的是地方,假如实在摆不下,还能找唐嘉辉想办法爆破了。”
她轻描淡写地一弹指,就让他的希望在眼角的泪光里灰飞烟灭。
但荣立诚是从不轻言放弃的男人,他的精神病在减药后变得越发难以控制,人家越是冷淡,他越是两头燃烧。
可惜,如此情深义重地在背后张罗,意想不到的麻烦事也是会发生的。
当荣立诚给雷诺萨家的长男打电话告知实情后,对方连遐想的时间都没给,便直接回了一句“对不起,这个我办不到。”
狂妄不羁的少东家整个楞在当场,张口结舌。他果然天生和四眼小崽子犯冲,不分国籍,不分年龄。
“荣先生,您知道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可能是意识到回敬的语气太过生硬,安德烈又加了补充说明。
“你一个人不行,加上你弟弟那一票不就行了?”
“实在抱歉,下次请让我替您办些力所能及的事吧!这一次只能让您失望了。”
说哪门子大话,还下此次呢。美人当前,有什么事是两兄弟不能商量着办的?荣立诚咂咂嘴,觉得这些年轻孩子就是爱矫情。酷酷的安德烈搞不掂的事,小玛缇亚斯就好说话多了嘛!
前院里,严肃的管理人一边审视连松雨的模样,一边将铁环上的钥匙串晃得叮铃当啷直作响。每个人都有表示不满的发泄方式,显然,老头觉得这刺耳的金属声比月亮更能代表他的心。
黑灰色大门在锁头转动的瞬间发出沉重的声响。雷诺萨家的大公子安德烈心安理得地站在一旁,看着比他年长数十岁的工作人员给入口解了封印。
遥遥望去,安德烈正是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年纪,尚未发育完全,却已经长相体面,身姿修长。
穿衬衫和夹克时是预备科学家的料子,穿正装时是气质高傲冷淡的继承人。亦正亦邪,简洁繁复皆相宜。
倘若非要找点瑕疵出来,恐怕就数那副尺寸略显夸张的胶框眼镜了,它已经很旧,旧得古怪蹊跷,像是从时空胶囊里翻出来的物件,透着一股子念旧痴情的味道,不配他这个人的作风。
安德烈回头看貌合神离的荣氏夫妇,对他们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进去吧,玛缇亚斯应该快到楼梯口了。”
他优雅地一欠身,嘴角翘起。那是从小打下的基础,有装不出来的贵气,还有挥之不去的假惺惺。
然而安德烈表面上的客气亦是有针对性的,面对荣立诚时他闪到一旁毕恭毕敬,面对从天而降的荣太太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跟在荣立诚身后向里走,连松雨发现想要顺利通过正门,她必须侧着身蹭过安德烈的詾口。凭着她的平板身材,通关难度并不大,唯一需要探讨的课题在于到底该正面蹭还是背面蹭。
这表情僵硬的贵族男孩像个门神一样挡住小半扇门,等待她自投罗网。
诚然,连松雨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为何会对自己怀有这么大的敌意。
如果说昨天他只是有些小小的不愉快,那么今天就成了恶从胆边生,那充满刀光剑影的眼神,像是想要把她的灵魂挤出来鞭挞,冷得教人不寒而栗。他和她不过见了一面,无冤无仇,理论上不应该存在八字不合的可能。
“安德烈,谢谢你的安排。”
连松雨经过他身边时,低声对他道谢。她打定主意要对他说些什么,即便他用这种如临大敌的目光注视她。
不过,安德烈很快就告诉她这一切的横眉冷对,只是因为大哥在护着小弟的缘故。护弟狂魔放在哪国都一样,一旦觉察到了潜在的威胁,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他突然伸出手臂撑住门,将她的去路堵死。
“荣太太,有些话我得提前知会你,免得到时候大家因为一些误会闹得不愉快。”
安德烈咬字准确的英语说得极好,他留意到荣立诚在里面和管理人员聊天,趁机把连松雨拉到身前。他深绿色的眼瞳在暗夜里发出幽光,比土狼还凶狠。
“我想让你了解,今晚这个安排我原本是不同意的。”
“我了解。这不情之请想必很难办到,是我们唐突了。”
连松雨没打算反驳什么,依旧保持原来的语速,她只是惊异他突如其来的举动,非但不合时宜,还带着攻击性。她得罪他了吗?
安德烈摇头,他轻笑着,似乎在讽刺她的无知。
“的确很难办到,但我别无选择。其实你真不需要谢我,因为最后拍板的人是我弟弟玛缇亚斯。”
他紧盯着她比黑曜石还幽沉的双瞳,很满意她渐渐品出了这侮辱人的言下之意,高挑的东方美人多聪明呢,一点就透,都不用他费劲解释。
安德烈眼里满溢的鄙夷,快要藏不住了。即便这女人今日的面色比昨日更苍白,他依然看得出她天生的好底子。老天爷显然待她不薄,待他们兄弟却没有那么仁慈。
他那一头浅榛色短发的小绵羊弟弟,哪能和这种来自古国的无敌祸水过招呢。
好险,真的好险,如果没有在今晚及时发出那条短信让对方死心,自己护了那么久的弟弟就快跌到陷阱里去了。
安德烈故意狠捏了一把连松雨的手臂。他讨厌女人,他最讨厌这种女人。
“我弟弟身体弱,年纪小又不懂事。请荣太太千万手下留情,不要给他错误的信号才好。”
连松雨蹙眉,她抿着嘴唇回望安德烈,用内力压着火。
这指控委实太欠揍,可是和尊贵的雷诺萨先生在博物馆门口起了争执,能有什么好处吗?大约是没有的。忍字心头一把刀,她一个年长五岁的女青年没必要和这小屁孩一般见识了。
安然挥别了凶神恶煞的哥哥,在镶有螺旋形雕花扶手的楼梯口,连松雨见到了和善可亲的玛缇亚斯。
他的笑容和昨天没有分别,还是暖暖的浅浅的,在车上对视时那一低头的羞涩,再次出现在他干净青春的脸上。
同款正装上了玛缇亚斯的身,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反而越显乖巧了。
他探过身来和连松雨打招呼,礼貌有加,不掺杂任何暧昧和纠缠不清的神色。
“你们是刚参加聚会回来吗?”
“不。是去陪妈妈吃晚饭了,我身体不太好,平时不喜欢去太热闹的地方。”
为了照顾荣太太的感受,玛缇亚斯只挑了重点说。
大家还不相熟,总不能直言不讳地把所有实情一股脑地倒给她。那也太不公平了,不是应有的待客之道。
假如告诉她,今天是他的生日,并且,每年的这一天他都会和哥哥衣帽整齐地去疗养院,陪毫无生机和反应的母亲吃一餐晚饭,拍一张纪念照呢?那样会不会太沉重了点......
玛缇亚斯笑眯眯地看向门口站着的背光阴影,那是他保护欲强烈的哥哥,用手默默地指了指脑袋,意思是要他记得自己之前十万火急发过来的警告短信,该醒的脑和该守的规矩,都不能浑忘了。
他得承认,在看到那条言简意赅的短信时,确实有股难掩的失望。
原来她并非是那位暴君的朋友,而是人家的妻子呀。依着大哥的意思,他这种乖乖牌压根就不能和她扯上关系。
嗯,反正他在哥哥眼里,永远是一只咩咩的小绵羊,干不成大事的。
和管理人聊完天的荣立诚留意到玛缇亚斯古怪的神情,他忽而有些豁然开朗了。
当着男孩的面,他抓起连松雨的手,握得很紧。他是在昭示自己的所有权。唉,漂亮妻子真是个很不方便的东西,走到哪里都有人觊觎,他庆幸当年没有和她喜结良缘,否则,他还能平安活到今日吗?
玛缇亚斯转身踏上大理石阶梯,步子走得不疾不徐,似乎完全没有被刚才的插曲影响到。他还记得昨夜回家后和哥哥的谈话,对方熟悉的一言堂,让天真无邪的小少爷可伤心了。
“那位小姐,不知会在马德里待多久呢?”
“你怎么还没绕出来?我们不会再跟她见面了!”
“为什么不能见面?既然是荣先生的朋友,我们可以请他们来家里做客呀。”
安德烈嗅到弟弟不寻常的急切,这孩子从来都不懂提要求,除了物理别无爱好,是个相当乏味的家伙。
而他成长至今统共交往过的三个女朋友,全是冲着雷诺萨的姓氏来的,即便如此,这货也一如既往地回回都把人家当真爱,分手时哭得毫无尊严,做净了丢人现眼的蠢事。
“你难道对那个女人有好感吗?”
“我没有。我只是想,她一个人飞到西班牙,荣先生又这么忙,不会有空陪她到处转的。”
“玛缇亚斯,我劝你下次不要再试图当着我的面撒谎。你在想什么东西,我看的一清二楚。”
“我没有撒谎,我没有!”
嗯,他说他没有。这柔柔软软如糖糕的男孩子,空长了一幅瘦高修长的形貌,天生体弱多病,高声多说几句话就喘的不行。可他如此脆弱,却并不总是听话的。
玛缇亚斯听到后方传来的脚步声,荣太太和荣先生手牵着手,板着脸一言不发,他们难道是在赌气吗?
连松雨的手被荣立诚狠狠一拽,险些一个踉跄扑倒在台阶上。但暴戾成性的他不以为意,他继续拖着她向前走,面容冷峻,拖个人更像是拖一袋土豆。
在这诡冷的旋转阶梯里持续上行,没有任何人声做背景音。唯有两侧高墙上林立悬挂的油画从暮暮沉睡中苏醒,目送他们遁入一排冗长的窗格暗影中。
玛缇亚斯用钥匙转开走廊尽头那间房的门锁,双臂张开向两侧猛地一推。房间里光影分明,大面积的昏暗里,唯独射灯还亮着。
巫婆,婴儿,橡树花环。一轮晕开的勾月悬在左上角,咒语和黑色蝙蝠飞过贫瘠干涸的大地,恐惧伴着不祥的梦呓,涌出画布,冲到她面前。
那是荣立诚向她邀功的至美之物,他不给她看森林喷泉里的女神沐浴,却给她看暗夜里灰扑扑的人类骸骨。他站在连松雨身后,紧紧地环住了她。
“喜欢吗?”
荣立诚低头,在她耳畔低语。难听的声音和这群魔乱舞的黑色绘画般配的很。
他以嘴角蹭着她的耳廓,薄荷味的沉重呼吸让她浑身长满了倒刺,一阵强过一阵的战栗从尾椎直通脑干。她真希望那幅画上正在进行的巫术可以显灵,把他从她的世界里彻底抹去。
玛缇亚斯对他们不自然的动作毫无反应,他面容娴静地站在一旁,出神地盯着油画正中巨大的黑羊。他已经看过它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最细微的笔触。
它让他平静,让他获得片刻出世的安宁,只要有它在,他就不会在意这间房里正在上演的恶作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