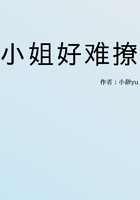我们像两个世界的人,互相沉寂在自己的生活里,对之前的那场纷争和对方视若无睹。
冬天虽然悄然而至,但并不像夏入秋那样声势浩大,我和汀汀穿着一起新买的棉衣挤在教室前面的玻璃前自拍。
帽子被人大力拽着,整个人都向后仰去,转过身不留情面的狠狠的拍了他一下,那一下似乎领悟到了张琰的精髓,他捂着胳膊疼的龇牙咧嘴的说“小展,你是跟林琛学刮痧了吗,手那么重”
“他学的是西医,临床你懂不懂”我不屑的说。
汀汀帮我理了理帽子,笑着说“你应该跟林琛学开颅,把他的脑子打开看一下装的都是些什么废料”
他双手抱胸,一脸莫名的无可奈何“你说说你们俩女孩子怎么就那么重口味呢,这样下去小心会单身哦”
汀汀深吸了一口气,强忍住想要揍他的冲动“貌似在场单身的只有你吧”
“我看小展也快了嘛”
“蒋睿恒你最近很闲是不是”汀汀不耐烦的打断他的话。
他有些小心翼翼的看着我,又小心翼翼的开口“小展,是不是触到你的伤心事了”
钢筋混凝土的硬度估计都比他低了两个度,用他糊城墙肯定好使,我神色暗淡,低落的开口对他说“何止啊,你简直就是在给我捅刀子”
他的神态让我看到了他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愧疚,看到他心里不安我就放心了。
他眼睛一亮,笑着说“那我跟你说点开心的事吧,我要参加b市电视台的正式选拔了,这样明年实习完就能直接进电视台了”
他的双眸又有些暗淡了下来“不过,我要跟程繁竞争这个名额,她那么优秀,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过他”
那根神经在经历了千垂百炼之后继而飞过来一把尖锐的刀子,它不再像从前那样脆弱不堪一击,有些习以为常的轻轻把刀子拔下来。
汀汀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加油,没有赢过她就自己把脸埋地里去吧”
他傻笑着,眼睛弯的像一轮新月“小展,你最近跟杨蕴星怎么了,自从小溪姐婚礼后你俩就再也没见过面,你们吵架了”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现在的状况,吵架也吵过了,冷战的话时间也过于长了,长到足以瓦解一段感情,眼前的这个人跟二百五一样,心烦的不想跟他解释太多,有些敷衍的点头说道“对,我们吵架了”
“你少来,我又不傻,吵架能吵那么久”他眼神放光,想要表示他很精明。
我惊奇的问他“哇,原来你不傻啊”
“快说,你俩到底怎么了”
他烦人的那股劲让我想找个地方把他隔离,一个眼神汀汀心领神会的对他说“你去问杨蕴星啊,你俩不是一个宿舍吗”
“他最近都在忙去英国交换的事情,每次我要找他问他就跑出去了”
抬起眼眸死死的盯着他,尽可能的掩饰自己的震惊,实际上连自己的瞳孔都在颤抖“去英国交换,他自己?”
他诧异的说“你不知道啊,要去一年的,这么大的事他没跟你说吗”
胸口传来一阵沉闷的感觉,努力的平缓呼吸,对他莞尔一笑,轻飘飘的丢了一句“挺好的,正好用这个理由把他甩了”
轻的好像我们就是两看相厌即将分道扬镳桥归桥,路归路的情侣。
“蒋睿恒,你就当今天没告诉这些,回头等我成功把他踹了请你吃饭”
在他愕然的眼神中拉着汀汀走了,脚步很快,似乎只要走的够快,那种要命的汹涌决堤的难过就能被我轻易的甩在后面,最终还是败给了它,忍不住蹲在了操场的梧桐下溃不成军。
绝望像一个强有力的黑洞,手脚并用拼了命往外爬还是被它吸了进去,你只能认命的在那个无望的深渊里摊开乏力的四肢,不做任何挣扎的随波逐流,然后渐渐地被空气里弥漫的空洞搅碎,连疼痛的感觉都快要麻木。
一双手轻轻的抚摸着我的后背,我抽泣哽咽的跟她说“原来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打算的,我每天还在傻兮兮的等待契机,我今天才发现,在他的生命里,我是一颗弃子,那个让我满盘皆输都不会丢掉的人却让我输的一败涂地,我的一往情深和一厢情愿让自己自己都觉得是个笑话”
死死的捂住嘴巴,想要抑制住那些悲伤的,汀汀揽住我的肩膀,飘零的伤感找到了宣泄的支柱,靠倒在她的怀里哭的撕心裂肺,眼泪沁湿了那件新的棉衣,这个冬天明明还没有下雪,却让我提前感受了冰天雪地,百里冰封的寒凉。
当杨蕴溪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好对着星空煎熬了一晚上的眼泪,所以声音嘶哑到几乎快要听不见。
全世界都知道了他要去英国的这件事,杨蕴星问我“小展,我哥要去英国交换了,你是不是很舍不得啊”
舍不得的资格已经被剥夺了,悲从中来不禁潸然泪下,万分的喊她“蕴溪,他好像很舍得我啊”
电话那头的她一怔,追问我“你怎么了,又感冒失声了吗,怎么嗓子哑成这样了”
我带着哭腔跟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要走了,就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不敢告诉你”她有些小心翼翼的试探着不是最坏的结果。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有些苦笑的说“他是已经不在乎我是否有知道的必要”
关于婚礼后发生的种种,让杨蕴溪不禁连连噤声感慨“他还真是一个钻牛角尖的傻子啊”
“蕴溪,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向我迈出了一步,我向来胆小如鼠,可是我鼓足了毕生的勇气向他伸出了手,隔着一个程繁,那些快乐像是我偷来的,我夹在在痛苦彷徨没有安全感之中,每每如此我都告诉我自己,那个守望了多年人只要牵着我的手,再难,再困惑,我都可以坚持下去,但是我的一腔孤勇偏执的等着最终的就只是怅然若失,到最后他甚至打算悄无声息的放开那只他曾经向我伸出的手,你说我该怎么办”几近绝望的啜泣着对她说出这些话,我该怎么办,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我再也没有多余的勇气去追问缘由究竟,那些横冲直撞的无所畏惧在不知不觉中被磨灭的消失殆尽。
一个人的独角戏上演了许久之后,连最后的奔溃都上演着一个人谢幕,透过纷争斑驳的岁月里往回看,那些最初的样子停在指缝之中,不畏世事的我一直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终究蹉跎了年少痴心一片。
人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泣不成声之后,终会还是要收拾好那些狼狈不堪,将所有碍于在人前透露的伤痛深埋,继而若无其事的行走在路上,告诫自己,人生的大起大落在此刻所经历的事上面,只是小小的冰山一角,宽慰自己,所要去迎接的悲喜,也不能断送在已经荒芜的年岁里。
我一如既往的吃饭睡觉上课,兢兢业业的早起占座,时常在汀汀担忧的眼神中繁忙着,一个人在你生命里存在的痕迹能不能抹去我们不可而知,但因为一个人留下的后遗症好了这个我是感同身受。
李老师拿着手电筒让我张嘴,他拿着一根木棍压着我的舌头往里面照着,我努力的忍住有些泛恶心的感觉,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把早饭吐了出来。
“没发烧,也没有炎症,声带也没有损伤,那你就是真的哑巴了”他飞舞着在病历上书写着反正我看不懂的东西。
见我波澜不惊,他笑道“嘿嘿,你这还真是哑出经验了,知道自己过不了两天就能好是吧”
我重重的点了点头,拿笔在纸上写着,李老师,你真像江湖骗子。
他拿手里的笔重重的敲在我的头上,疼的我呲牙咧嘴的,然后摊开双手在他面前。他一脸懵懂的看着我“你要什么”
“她找你赔医药费”
“哪来的死孩子,给你看病还讹上我了,林琛,你俩组团来碰瓷的吧,你小心期末我让你不及格”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期末考超纲题,比如水电气焊之类的我肯定不行”
李老师捶胸顿足“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他从他面前拿过领药单,微微笑颔首道“放心,目前医疗市场还是很缺人才的,把你调急诊一个顶俩你肯定饿不死”
我坐在医院的大厅的塑料椅子上,前面挂号的地方排着长长的队伍,汀汀经常说,只有在排队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龙的传人,只有在看病找熟人插队的时候才不会抨击这个世道黑暗难行。
林琛拿着刚买的温热的豆浆递给我,我立刻摆摆手,示意我已经吃过了。出门前,为了表示我真的没有其他的生病的征兆,接受了汀汀喂的三个包子以及一杯牛奶。
他故意调侃我“呦,今天跟我这么客气呐,平时不是我请吃饭都能吃半扇猪的吗”
忍不住笑了,抢过他手里的豆浆,吸溜了两口。
“你还会笑我就放心了,见过神经病,还头一次见你这个神经性失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