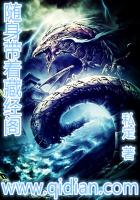“你错了。”秦小白扬起小脸,平静的说道。
他的平静让人觉得诧异,又觉得理所当然,仿佛当他说你错了的时候,那你一定是错了,没有原因。
但也正是这种平静,酒客们纷纷将目光游离到了其他地方,偏移到了酒馆外的大雨上,因为他们不忍直视接下来的场面,那肯定会很难看,也肯定会很可惜。
毕竟这拎着草剑的少年此刻出乎同龄人的平静让酒客们大为赞叹,虽然那柄草剑看起来有些可笑,在经过雨水地冲刷之后就像是一堆杂乱的蓬草。
即管如此,可那依旧是一柄剑。
但并不是所有提剑的少年都会有着鲜衣怒马的光彩,没有实力,没有背景,再如何富有少年气,亦或再如何少年老成,也会在残忍的现实面前被毫不留情地击溃,用无法承受的结果去告诉他们,那所向往的盖世英雄不过是一场被埋汰了的梦。
不过难看两个字,只是酒客们心中的同情与悲悯,因为这几个彪悍的人是薛府的下人,面对一个衣着简朴,看起来也很羸弱的少年,他们不会在乎结果,他们只会享受过程,所以那最后的结局自然会很血腥。
“你是规矩吗?”薛府侍卫突然说道。
酒馆外,风雷隐隐,天空晦暗一片,些许疾雨裹挟着湿气吹进了忽然一片安静的酒馆内。
薛府侍卫盯着秦小白,就像盯着一只羔羊,那双眼里的闪动着的光泽让人心寒,他显然并不打算得到眼前这少年的回答,下一刻,他的拇指指向自己,说道,“不,你不是,我是。”
“所以你说我错了,错之何用?而我说要揍你,今天肯定是揍定了。”侍卫冷笑,他蒲扇般的手抓着酒桌轰然一掀,伴随着阵阵瓷碗摔碎的声音仰面冲秦小白砸了过去。
酒馆外的马槽处,雨水哗啦地流淌,有一书童撑着把油纸伞,遮住了前面的身影,那也是一个少年,白衣,俊眼,顾盼之间,显得意气飞扬,是杜鹃花开的少年。
“真是恶仆难教……”他的眼很亮,穿过了雨雾,望着酒馆内的场面,啧声连连。
“少爷,不去救下那位少年吗?”身后的书童好奇的打量了一眼酒馆,疑惑道。
“这种小场面还需要我出马?”杜开手里拎着一把未撑开的油纸伞,扫在薛府侍卫身上的目光满是不屑。
“可,可那毕竟是一个身骨强劲的成年人……”善良的书童有些担忧。
“我中意的人不会差太多,你看啊,这家伙手中可是拎着一柄草剑……虽然他拎剑的姿势不怎么漂亮,但我敢打赌,那绝对是一柄不错的剑,不错的剑,不错的人,一定会有不错的剑招。”杜开打算为书童找点劝慰的理由,让他安心一点,但在秦小白的身上他只找到了讨厌的文绉气,于是只好将目光转移到了那柄草剑上。
看着自家书童露出怀疑的小脸,杜开挑眉,“放心,还没人能够在你家少爷眼皮底下伤人,当然英雄一般都是最后才会出场的,而且最后出场的英雄一般都能够俘获美人心,虽然这家伙不是美人,但绝对是一个做书童的好料子。”
秦小白自然不知道有位少爷已经自作主张的给他安排好了日后的身份,他看着眼前阔大的酒桌愈发逼近,小脸上有些无奈。
呼啸出的阵阵风声仿佛云层之上咆哮着的怒雷,轻而易举地掠开了他因为雨天而有些凌乱的发鬓。
他捏了捏手中的剑,然后又松了下去,剑上的草有些杂乱,所以他不想动剑,因为那样做很可能将二姐赠给他的剑显露出来,那是一柄色泽乖张的剑,会让他很难为情。
于是秦小白侧了侧身子,就像今日在薛府外一样,很自如地转动脚掌,就将酒桌避了开去。
哐当!酒桌去势未停,稍稍砸落在秦小白的身旁,然后划出数丈的距离,一路崩裂洒落桌腿木屑,直到酒馆门槛处方才停下。
这一幕在酒客们的眼里有点匪夷所思,那么一张阔大酒桌竟然只是擦肩而过,得多好的运气才能被如此微妙的距离所眷顾!
侍卫微怔,他想到了今日在薛府外对这少年喷唾沫钉子的情形,简直和现在一模一样!而且那张小脸也如现在这般平静!
这让他极为恼火,然后暴怒,于是恼羞成怒,对身边几个同僚喝道,“给我上,运气好是吧?我倒要瞧瞧你这运气能逆天到哪里去!”
“不,这帮恶仆已经不是可教否的问题了,这是无法驯化……天啊,我无法相信对付一个少年竟然四五个大汉一起出手,瞧瞧,多么卑鄙下流无耻粗鄙的故事!”马槽木桩旁,杜开唉声叹息,他身后的书童一手撑伞,一手捂住小脸不忍去看。
秦小白心里非常不高兴,因为这几个大汉的行径实在是有些过分,这已经不是礼貌和尊重的问题了,四五个大汉对付一个少年人这种事怎么看都不太道德,所以他决定给这群家伙一些教训。
呼!
秦小白想着自己应该如何出手才不至于伤及这群人的时候,侍卫已经蓄足了气力,他的手掌边缘遍布厚茧,看起来力感十足,就像一把无往不利,摧枯拉朽的砍刀,撕裂着气流,冲秦小白当头竖劈而下。
离得稍近些的酒客立马感受到了这一掌的气势与力度,他们认为这一掌落下,绝对会将这个少年的胳膊骨劈碎。
啪嗒!
就在这时,一把青白相间的油纸伞撑了开来。
伞柄处,是一只温润如玉的手。
五指纤长白净,就像少女的葇荑。
“人多欺负人少,这看起来可不是一件好事。”声音之间带着少年人的张扬,但这张扬之内并无嚣张,有的是一股锐气激荡,以及很自然的意气风发。
杜开手腕微动,油纸伞开始旋动,转出一圈圈气流,弥散开来,便成了如水的涟漪。
“啊!!”忽然,侍卫发出痛苦的叫声。
人们望着他的目光开始只是疑惑,然后有些心惊,最后满目悚然。
那劈向秦小白的手掌俨然被油纸伞挡住,随着木纹伞柄的转动,这侍卫的手掌微扭,手臂也微扭,下一刻,他的衣袖瞬间碎裂成布片纷扬了出去,显露出胳臂上那一道道狰狞的血管。
涟漪威震,青筋暴起,血管狰狞,它们疯了一般迅速扭动,如同虬龙错根盘绕,也仿佛一条条青红斑纹相间的蟒蛇拼命缩卷躯体,想要绞杀猎物一般。
秦小白自小就喜欢冬天,喜欢秋天,喜欢夏天,不过他最喜欢春天,因为春天适合万物生长。
二姐教他修行杀人这么多年,他向来便有抵触心,他想要教训这群侍卫,但并不想看到眼前这残忍的一幕,于是秦小白连忙劝阻这位杜鹃花开的少年,示意不要这般虐待侍卫。
“虐待?不,我只是在驯化,就像驯化我家那匹烈马一样。”杜开说话的时候很认真,认真得有些冷酷,就像真得在驯化马儿一样,所以手里的油纸伞也自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侍卫粗壮的手臂已经殷红一片,那种红,是肌肤表层下渗开了的血。
这种流血方式并不常见,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实现,即便能够实现,出于人道,也很少有人会动用这般手段,因为那对承受者来说简直是可怕的折磨,往往都会带去无法磨灭的心里阴影。
“可我觉得他现在很乖,如果你的马已经被驯服了的话,那他就像那匹马。”秦小白见侍卫的胳臂越来越殷红,越来越粗壮,不禁眉头紧蹙,尝试着按照杜开的思路去劝说。
乖?酒客们听到这个字眼莫名想笑,可却又笑不出声。
用乖这个字去形容薛府的侍卫,在白城,这本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可这两个少年却在一本正经的讨论这件可笑的事情。
突然发生这一幕,侍卫的几个同僚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当他们从呆滞中惊醒过来的时候,却再也不敢动手了。
因为眼前撑着油纸伞的白衣少年他们认识。
因为六月盖雪巷的所有人都必须得认识这个少年。
因为白城的秋主只有这么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