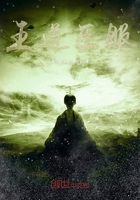亥时,灵枢阁的水车吱呀吱呀缓慢转动,下站一个蓝衣少年,剑眉星目,乌青发带随意飘在脑后,俊朗面容带着难得平易的神色。
卫琨珸拍拍溅到自己袖上的水,离水车远了点,就看到一个穿着夜行衣蒙得严严实实的人向这边小跑过来。
“你也太夸张了点?”卫琨珸抄着手嘲笑。
柳巷终于跑到他面前,拉下面罩,比了个噤声的手势:“万一被别人发现怎么办?”
“你以为就你穿成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
柳巷就把帽兜也摘下,吸了口气:“什么事卫兄?”
卫琨珸顿了顿,道:“我今日叫你来,是问你还有无为百味谪仙报仇之心愿?”
柳巷表情瞬间严肃,郑重道:“这是自然,先师之仇学生必报。可……卫兄为何有此一问?”
“你看看这个。”卫琨珸从怀中掏出那支箭。
柳巷接过,仔仔细细看了看这支箭,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当年汤婕前辈于郦水香消玉殒,听说夺其命的,是一支箭。”卫琨珸打量着柳巷的神情。
“没错。”柳巷的双手开始微微颤抖,“师娘的尸体是我亲手打捞起的……这支箭……此镞,此羽……和当年插在她胸口那支一模一样!”蓦地抬头,“当年那支我已烧毁,卫兄你怎么会有……”
“看来……我们果真拥有同样的敌人。”卫琨珸勾起嘴角,眸中一丝冷意划过。
柳巷望着卫琨珸,了然,卫琨珸定有亲友也死于此箭下,至于是谁,好像并不是该他多问的。
“据我所知,百味谪仙之死八成源自对其妻汤婕惨遭杀害的愤懑。”卫琨珸道,“可汤婕前辈之死蹊跷万分,绝对是有人故意为之从而激怒百味谪仙,令其失去理智显露马脚。所以若要探明百味谪仙死因,找到袭击汤婕前辈的凶手便至关重要。既有此箭为证,你就未考虑过寻找杀你师娘的凶手?”
“当年此箭是由身着诛青门门服的弟子所射,当是诛青门所为!”柳巷道,“这也是我找陆诀决斗的又一缘由。”
“诛青门乃剑道名家,杀人何需用箭?”
“为掩人耳目……”
“既是掩人耳目,又为何身穿诛青门服?”
“……”柳巷眼神空了下,逐渐清明,他握紧拳,“卫兄的意思是……杀我师娘、挑起战乱的,另有其人?”
卫琨珸点了点头,又道:“当年汤婕前辈坠海,箭尖当被海水冲刷了无痕迹,可你看此箭。”
柳巷忙转过箭尖,借着月光定睛看,看到了嵌在螺旋里的紫渍,眉头更深了些:“毒。”
“是。”卫琨珸道,“我的一位故人之父原属毒宗,应就是为此批箭上毒之人,可哪想在交货后被人杀害,我认为八成是杀人灭口,这说明这批箭的用处绝不单纯。”
“故人之父?可知其讳?”柳巷追问。
“陈祺。”卫琨珸道。
“陈……陈伯……”柳巷向后退了两步,似有些无力,“陈伯是毒宗元老,待我如亲侄,可当年他出了谷却再也没回来……原,原来也已故去了……”柳巷手抹了把脸,声音哽咽。
卫琨珸无声叹了口气。
——
卫琨珸踱出山门,谷中夜晚潮寒,旁边古木荫郁,地上露水浓看不太清明,只是一簇簇迷蒙的白从脚边蔓延到视线尾端。
他呼出口气,白悠悠向天空飘去。
他为什么信任柳巷呢?
可能只有一个理由。柳巷当时与他决斗,用的是迷药。
君尧先师君长林对君尧唯一的要求:勿将杀人之毒制法传授后人。君尧做到了,连最亲近的弟子都未曾得知。
既然君尧是如此遵信守诺的好汉,他倾力以养的弟子定不会差。
可他并未说自己的怀疑,只是让柳巷去查箭上之毒究竟是何。
就算再怎么怀疑,只要不是完全确定,绝不可以讹传讹错生忿怨。
可仔细与柳巷说来,这批箭如今是否用完,造箭之人的目的又是什么。他凭空不知哪来的预感。这些……好像不止会牵扯几条人命而已……
卫琨珸再回过神来,眼前见到了通外的洞口,洞中月明珠因无日光折反漆黑一片。
唉……怎么走到这了……
“噌……哗哗……”外面传来鹤梁瀑的巨响。可纵然瀑声再大,以卫琨珸的耳力依然能听出异样。
沿山洞行出去,来到青石柱上,在渺濛的夜色中,卫琨珸看到了在瀑下的少年。
少年裸露上身,水珠在肩脊滚落,勾勒出绝美线条。右手提剑练着剑法,手臂充满力量感,流瀑在剑刃引出一丝银线。卫琨珸稍稍怔忪,随即握紧手心。少年白净的背上有拳头大小的火燎过的黑紫的疤痕,这是多重的伤,受伤的人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太轻易看得出来。
“谁?”剑尖挑着一层水花向卫琨珸刮来,卫琨珸没有躲,在陆诀看清是他的同时被打在胸口落进湖里。
“扑通!”
水很深,很冷,卫琨珸在水中睁眼,只见一片墨绿,深沉的让人窒息。
陆诀,我这点痛可及你受的万一?
“卫…琨…珸!”水上传来的声音,闷进水里,听不清明。
陆诀,我最近变的不太像我。我是很洒脱一个人,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一个人。
陆诀跳进水中,游到他眼前,虽光线昏暗,可陆诀脸上的表情足够让他看的清明。
那是担心,是生怕有一点差错和闪失的疼惜。
陆诀,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以为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腰被揽住,身子被人向上带去,眼前的潋滟放大,直到破出湖面。
“咳咳咳!”卫琨珸还是呛着了。陆诀揽着他:“我不知是你,你可有事?”
“我有事如何,无事又如何?”卫琨珸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陆诀的眼睛。
“你无事就好。你不会水,我先扶你上岸。你穿的单薄,谷中又冷,回去还是打点热水洗……”
“陆诀。”卫琨珸打断陆诀,看向他。
两人离的那么近,近到陆诀额角滴下的水他都能数清有几颗。
一颗滑至唇角。
卫琨珸含了上去。
水滴沿着卫琨珸唇线漫开。
当双唇触碰的那一瞬,卫琨珸所有关节似跳了一下,心口一针针麻痒。
耳边充斥着瀑声,大到所有声音都听不见,但这巨大的轰鸣仿佛就来自他胸口。卫琨珸的手缓缓抬起,抚上陆诀的背。
陆诀的唇很薄,很凉,又柔软,似使一点力都会伤到。
他当时又是如何狠心伤他的?
如此近的距离,其实什么都看不清。陆诀现在会是怎样的表情呢?错愕的、厌恶的?
他闭了眼,顿了一下,离开。
“你懂了吗?陆诀。”没看陆诀的眼睛,卫琨珸出声,声音平静,略带一些嘶哑,“我卫琨珸,现在对你还是这种龌龊的心思。你怕我,避我,都再正确不过,因为我满脑子都想对你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觉得很恶心很荒唐吧?那就请你以后离我远远的,别再因为什么大义什么仁心来救我,与我当什么朋友了……”
瀑声那么大,他肯定陆诀没有听见多少。就这样吧,就当自己给了他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卫琨珸推开陆诀,幸好离岸不远,他伸手够到石柱,撑着准备上岸。
腰忽被拦住,卫琨珸跌退,贴上陆诀胸膛。而陆诀,右臂稍用力,抱紧了他。
“以前的事,我都想起来了。”陆诀的声音就在耳畔,若秋雨,一字一字清晰地浸入卫琨珸耳朵,“卫琨珸对陆诀的感情,我从未觉得荒谬丢人。我护你周全,怎会是为侠义道心。“
“我与你相交,不过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