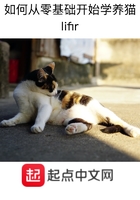当初离开京都赴江南为官是光绪九年(1883),一转眼已经过去了十八年。经过甲午年(1894)的中日战争和庚子年(1900)的义和拳之乱,北京到天津短短四个多小时车程所经之地都已变得面目全非。天津城外那片竹林,曾有过一个充满诗意的地名——紫竹林,现在竹林和林中小庙,都已经“焚毁无遗”,城垣也都“拆堕尽净”,改成了“马路”。甲午之战时,聂士成率军一面抵挡洋兵入侵,一面承受义和拳的背后袭扰,悲壮战死于此。京郊丰台一带现在被洋兵盘踞,那里往昔姹柴紫嫣红的“芍药之盛”,已经“殆不可问”。沿路乡村,到处是败堵颓垣,许多民居已片瓦不存。至京都永定门,见到其右侧城墙,因在战争中被洋兵堕毁数丈,现已辟为车道。
劫火沧桑,触目惊心。
这次来京都过班,毕竟与二十多年前的进京赶考不可同日而语。当年进京,两眼一摸黑,身上仅有的几个叫“赤仄”的四川铜钱都被永定门下的门卒搜刮了去。现在他已是在官之身,在京都的“过班之旅”都由京官好友高树、高楠兄弟和乔树枏具体安排。三位都是同治九年(1870)李超琼在成都锦江书院求学时期换过兰牒的昆季兄弟。当年,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二十多年过去,彼此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总角之交”。
高树、高楠和乔树枏三位好友以及他们的孩子,对李超琼在京都的生活和办事行程都作了细致的安排。李超琼一到,就发现新住处“糊屋扫地”之事都已经一一当当,“行厨用物”也无一不备。只要愿意,他还可以随时去高家、乔家讨扰,“食则食,车则车,毫无主客之迹”。
高氏兄弟和乔树枬都住在宣武门南的菜市口一带,所以安排李超琼先在泸州试馆暂住,而后再搬去乔树枏居住的绳匠胡同。菜市口一带房舍街道相对整洁,租金不贵,距离中央六部衙门比较近,是明清两代外省籍中下级京官扎堆聚居的地方。到了晚清,更是消息流通、新思潮涌动的渊薮。“戊戌六君子”大多住在这一带,刘光第就住在绳匠胡同伏魔寺乔树枏寓所的隔壁。乔树枏和高楠虽都不属于“康党”,但都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
流寓京都期间,李超琼从琉璃厂的地摊上买到过一部小说——《儒林外史》,读之爱不释手,逢人都称此书为“人物镜”。书中用到的一句民间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时就是广泛流传的佳句。在历史早已翻过了清朝这一页的今天,已经是人人都能脱口而出了。但体制不同,语境不同,理解就相去甚远。
时过境迁,后来之人会想当然地推想,三年知府如此,即使是十年普通知县,少说也会有个七万八万。区区几千两,何至于愁!
推想不是历史。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朝历代的制度,其实都是家产制。李超琼所处的清代当然也是如此。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州县官就是“一人政府”,州县财政就是“一人财政”。州县官吏向省和中央政府上缴一定的国税后,自己可以从实际征收来的税收中支付行政经费,并将余额保留给自己。
州县官的个人收入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俸禄”,七品知县岁俸四十五两,李超琼曾获加级,至五品直隶州知州,与知府同级,岁俸八十两;二是“养廉银”,在光绪朝,根据地区差别,知县为每年五百到两千两,知府为八百到四千两,都只是政策额度,只在当年税收有余额时才具有实际意义;三是“火耗”,允许在确保上缴正赋不少的前提下,以火耗名义增收附加税。养廉银、机构运作、官场应酬、幕僚薪酬、杂役工食、灾赈支出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用途,都从中提取。前提是皇粮国税一分都不能少。
收税和安民,是州县官两大职责。那么,两者矛盾怎么办?例如,遭遇严重灾荒,民不聊生,州县官就必须面临选择。他可以狂征暴敛,确保皇粮国税,谋取自己的政绩,甚至顺便中饱私囊;他也可以如实报荒,争取蠲免或者部分蠲免皇粮国税,达到让地方休养生息的目的。
选择的后果,如同加减法一样简单明了。选择后者,或许会有个把“担粪者”出来说声好,但那是要付出牺牲的。远的且不说,直接的牺牲,就是州县官放弃自己本来可以获得的法定收入,同时,地方财政遭受亏空。
李超琼在元和县两度任职,共计八年。光绪十五年(1889)因水灾申报漕粮四万石全免造成的一万五千两亏空、二十一年(1895)因叶怀善撤职留下的一万三千两欠款和二十三年(1897)因虫灾实施的部分漕粮蠲免,再加上平时作的主政官,为上级江苏首县为官员的迎来送往支付的巨额供张,导致元和县财政长期处于亏空状态。
光绪二十五年(1899),李超琼终于在江阴任上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好年景。但是母亲去世,他必须离职丁忧。丁忧官员,按例一律停俸,养廉银、耗羡银的收入也一并取消。新来的江阴县令与李超琼交接完毕,临别时曾慷慨答应,等“上忙”钱粮(上半年的田赋)收上来后,一定会分出一部分补贴李超琼的。但后来此公反悔了,不再提起。
为筹集过班银子,李超琼向宝山知县沈佺和苏松太道台袁树勋[4]两位同僚各借一千五百两。此外,再发动潘由笙等几位弟子三百、五百地四出为他借钱。
十月,吏部的印结局突然发出通知,要额外加收“印结费”。凡报捐道员者,要另交银子五百三十两。加上“部费”五百两,须交付的额外费用已经超过了一千两。李超琼连连叫苦,看来,自己既已报捐,就成了吏部砧板上的肉,只有坐等着挨宰的分。
他从自己存在宝兴隆银号里的仅有的五百两盘缠里,取出了三百两,不足部分请在京的高树、高楠兄弟先垫着。其余的银子如何筹措,他“颇为悒悒”。
为了筹集银子,他想起一位谢姓故友。他与谢是在元和县任职时相识的,那时谢在苏州候补,顺便开馆授徒,补贴家用。谢有母丧,李超琼便借给了他一百两银子。后来,谢从河南写信来,称他适逢“大挑”,好不容易当上了汲县县令,但上任盘缠一时短缺。李超琼又通过邮寄借给了他一百五十两。多少年过去,他再也没有了谢的音讯。情急之下,他想到,既然谢已经当了官,现在自己正在急需用钱的当口,何妨去封信,看能否多少还回来一些。
那天,天气骤冷,北风呼啸。李超琼租住的绳匠胡同里的那间两椽斗室,房顶上的瓦片被刮得哗哗作响。摇曳的油灯下,李超琼展纸砚墨,给谢姓兄弟写信。信上“皆与言窘状,欲其一济涸辙”,诉说自己如何山穷水尽,请对方一伸援手。写着写着,李超琼感觉不对劲,他意识到,自己眼下确实是被银子逼得走投无路了,但谁知道这位谢兄弟的境况如何呢?他为自己一时糊涂产生的卑劣念头而愧汗欲流。
信最终还是没有寄出去,但是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他为自己曾经动过这样的念头,而内疚不已。
又一天,李超琼在菜市口绳匠胡同好友乔树枏的寓所,意外地与曾蜀章[5]相遇。曾蜀章也是他早年在锦江书院的结义兄弟,他一眼就认出了曾。十年前,光绪十五年七月的一天,在胥门瓣莲巷的租屋里,即将去接元和县印的他和曾蜀章、廖平(季平)、陈经畲(纬元),还有张子黼(祥麟)几位好友畅谈至深夜。当时,曾蜀章刚刚点了翰林,廖平和陈经畲即将南下广东,而他,明天就去草桥头的元和县接印。当年的他们,个个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即将各赴前程。大家高声论辩,毫无睡意。那些热烈的场景和感人的话语,仿佛都是昨天的事。
触痛他心境的是,时间过去才十来年,与曾蜀章蓦然相见,对方竟一时不敢相识。直到一切都说了个明白,曾蜀章也还愣了好久,不肯相认。这个细节,让李超琼黯然神伤。自己的确老了。
他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年岁不等人,一切都该抓紧了。曾蜀章虽然始终未得重用,到现在也还只是个翰林院侍御,但他已经在历史上有了自己的重大建树。正是他,在朝野的思想界带头喊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驭夷之道,莫如强兵”。这是戊戌那年,他针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一个影响恶劣的迂腐之见——“驭夷”应当“以诚信结之”提出的。大丈夫当如斯耳!官运好坏、官阶高低都算什么?
与曾蜀章的相遇,给他带来了一次警醒。要抓紧利用有限的生命,多做些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不能再为了“道员”的虚名白白耗下去了。
十一月初二,天上飘起了雪粒。李超琼拿定了主意,把过班的目标“仍改归知县”,再也不求当什么道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他平静而慎重地写信通知了为他过班提供服务的中间人袁保三,也告诉了自己的儿辈们。
放弃过班道员,就意味着他终生的宦途很可能就只停留在帝国行政体制的最低层级——知县。
对此,他是深感遗憾的。老友王芸庄[6]曾因李超琼的官途际遇发过感叹:“作令二十年,非无知遇。而到老仍以一知县终。”光绪三十二年,李超琼在上海知县任上给在日本留学的爱子李侃写信时,特别提到了王芸庄的这番话。他关照侃儿,王的话将来正好可以写到自己的墓志铭上去。
二月初二,李超琼以“卓异俸满”起复知县的身份,排在七八十名起复官员的行列之中。他在吏部官员的引领下,步入内廷乾清宫,晋见当今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太后御座离得远,“隐约不可辨”。光绪皇帝御座在前,天颜咫尺。
起复官员从皇帝面前鱼贯而过时,每人必须开口禀报一句话。这句话,事前是有严格规定的,只限十一个字:“姓名”三字,“何省人”四字,“年龄”四字。
李超琼一向嗓门大,把这十一个字说得特别宏亮,竟使得光绪皇帝微微抬了抬眼皮。在这瞬间,他与天子四目相对。这位“尧臞禹瘠”的年轻皇帝充满忧郁的眼神,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
起复的程序繁纷复杂,都得一步步走过。吏部各司局办事颟顸如故,“堂司各官竟日不至”;“司官都如木偶,任凭胥役摆布”。要钱索费、上下其手的事情都是公开的。整个吏部,都任由“狐鼠鬼蜮盘踞把持”。在吏部各堂司的办公廨舍里坐俟既久,经常“目见奸胥赃入累累”,根本无所顾忌。
在吏部的藤花厅里竟日兀坐,等人办事的时候,李超琼一时兴起,挥笔题联一对,挂在了廨后楹柱上:
老去名心已久交,饥驱今又上燕台。藤花厅外暄阳好,独坐真终献曙来。
他感叹:“辇轂如此,铨司如此,天下事尚可问哉?”皇宫里这样,选官的吏部这样,天下事还用再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