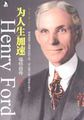于是,李超琼当场手书示条,约以四事:准考取结只准一张、非衣冠不得入场、非应名不准给卷、交卷必须签照。“起教于微眇”,在他看来,这是关乎一县学风的大事,必须力挽。李超琼从自己的养廉银里出资,购买经史书籍,奖励名列前茅的八名生童。又捐出当年俸禄,买下一王姓客民的六十亩土地,以土地的“岁租”作为优秀生童的奖励金。
十五年(1889)七月,李超琼奉调元和知县。当船已经驶离溧阳,进入常州境时,这位已经离任的知县,还在惦记溧阳的教育。他在船上补作一诗,《为溧邑诸童子咏》:
徙舍谁教傍学宫,漫将觽韘诮童蒙。衙斋未厌为村塾,草弁端期养圣功。截发爱钟陶士行,等身书熟贾黄中。家驹自属名门产,莫道颜标错认同。[4]
在溧阳三年多,李超琼遇到过两次大的灾荒,光绪十三年的涝灾和十四年的特大旱灾。作为知县,灾后发放赈济粮款、蠲免赋税的“荒政”由他主持。在李超琼看来,主持荒政,也是教育百姓、凝聚人心的重要机会。
十三年(1887)五月,大雨浃旬,湖河漫溢,据初步的灾情统计,全县被淹的圩田有二十万亩之多。照惯例,官方尽管明知民间报荒多少会有虚冒,但事关舆情,一般都不再复勘核实。在确定蠲免或者缓征数额时,只是凭经验在大致数额上做些讨价还价而已。
雨后,李超琼疟疾稍愈,再次一叶扁舟,出得北双桥,来到全县最为低洼的胥渚古渎村作微服私访。这个村里有座土墩,据说,每遇洪涝,当官的只要登上此墩四下一番眺望,公事遂毕,便算知道了受灾程度,回去就能拍脑袋报数字了。一个土墩竟如此神奇,在老百姓中传为笑柄,干脆就叫它“勘荒墩”。
暑热难当,李超琼看过勘荒墩,便在沿岸一片竹林里,找当地田父聊天。一问,原来勘荒的秘密早已尽人皆知,每次灾荒,灾后的蠲缓数目都是当官的按成色核减得出的。哪些田亩蠲与不蠲、缓与不缓、蠲缓多少,其实都是以当地“区董”的强势或懦弱为准的,衙门里的书役也就有了充分的做手脚的空间,“高下其间”,没了顾忌。所以,即使官府或蠲或减,受灾的农户也“鲜有实惠”。
于是,李超琼一改往常做法,要求各保在报荒清册上将“荒田坐落丘叚、花户姓名”逐一填明。勘荒人携带“鱼鳞册”(地图)前往,“按图以索”。这样,便“虚实立见”。他自己亲自外出勘荒,“所至皆屏去趋从,唯布鞵草笠,与田夫农父躞蹀塍间”,“虚捏者丈量不符,立予惩责”。
这样一来,“乡民无敢肆其欺者”。过去县里来人勘荒,只要列一个“荒废名目”,就可以“荒户”之名,每亩得到赈济数十文,而那些书役、练保,甚至区董等多少有点公权力的人,就“藉以自肥”,连“官中厮仆,亦得染指”。
李超琼宣布,今后每对一个受灾村庄的勘荒和施赈,都一定会用公开的方式向父老乡亲当面说明白,决不会妄费一钱,决不让任何人有从中捞好处的机会。
次年(1888)是罕见的大旱之年。八月底,旱情刚过,收到的报荒清册累积盈尺。九月,李超琼踏勘灾情的足迹遍及境内各地。有首小诗记录了他勘灾所见:
愁说重阳过,曾无风雨来。九秋仍苦热,百里半成灾。节候惊何速,瓯窶剧可哀,疲农尤盼泽,种麦待春回。[5]
最后,他核定确实“被旱无收”,应该报请蠲缓额征的农田,总计二十三万二千二百七十九亩。
十月初二,县衙前张贴出由知县李超琼亲笔书写,并加盖大红官印的“硃谕”,“剀切示之”,对有藉报荒而渔利的保甲长给予申斥和警告。
十一月,李超琼又在各区、图上报的赈灾请求里,发现因为上报情况的“滥”和“无理”,赈灾事务始终“未得要领”。谎冒风气的严重,使他为之愁闷不安,为之愤慨震怒。十二日,他登舟南行,先去西梗镇思古桥一带的农村查视,指出了王姓和杨姓两个村子上报情况的冒滥不实。
李超琼每次下乡勘荒,食宿都在雇来的小船上,从不接受乡民招待。人在船上,写诗自是一乐:
荒江遥夜独横樯,寂寂宵深水气凉。霜重孤篷时滴响,月斜微罅忽飞光。浮沉身世船摇曳,灾欠民情梦短长。两岸蛩声悲咽苦,似闻愁叹在黎氓。[6]
那天一早,戴埠一带来人报灾,要求赈济。吃住在小船上的李超琼有点晕眩,呕吐了几口,勉强吃了些东西,就登岸跟着报灾人走进南山,沿途抽查戴埠的受灾户。
他看到,戴埠的农田因旱严重受灾,固然不假,但各家农户都还有刈草、伐木、烧炭之类的副业,多少还是可以带来一定收入的。所以判断,这里的农户与别处急需赈济的“极贫户”相比,日子要好过些。戴埠的真正问题是,大量闲散劳动力没有全部投入到农业生产上去。
于是,他召集方圆二十里内的保甲长,一方面批评冒滥不实的风气,一方面宣布政策,为每个受灾农户发放大麦种子三担,要求在冬至之前播种。争取明年开春有些收成。
在李超琼看来,勘荒赈灾固然是救民于水火;同时也是,端正民风的机会。
民生为大
李超琼最关心的是民生大计。来溧阳前,强汝询先生曾建议他读读由李景峄、陈鸿寿两位同时也是大学问家的溧阳前任知县先后主持编纂的《(嘉庆)溧阳县志》。李超琼研读后,一方面赞叹《(嘉庆)溧阳县志》体例完备,无愧大家手笔,一方面指出了它的一些缺陷。他认为,记载民生大计的《食货志》部分写得有些粗略。
李超琼任内,适逢溧阳县续修县志,他按例以知县身份主持其事。这部志书成书后就是《(光绪)溧阳县续志》。在今天,它与《(嘉庆)溧阳县志》同为后人研究溧阳历史的名志佳乘。
李超琼在《溧阳县续志》编纂班子中的角色,不是一个挂名主修,而是一些重要篇章的实际撰稿人。续志的《食货志》全部出自他的手笔。“田赋”、“田赋起存”、“漕运”、“税课”、“盐法”、“户口”、“蠲恤”等事关民生的历史细节一一记录在案。田亩数据,“亩”以下精确到“分、厘、毫、丝、忽、微”;银两数据,“两”以下精确到“钱、分、厘”;谷粮数据,“石”以下精确到“斗、升、合、勺”。不仅续记了嘉庆的历史数据,还大量补充了被前志忽略的“康”、“雍”、“乾”,甚至顺治时期的历史数据。其良苦用心,无非是要告诉后人溧阳人曾经的真实生存状态。
光绪十四年(1888)是李超琼在溧阳知县任上的第二年。新年到来之际,他自撰春联,并把它们在官舍大小门前张贴。其中一联称:
此身从田间来,久与穷檐同疾苦;尽诚乃份内事,愧无善政答升平。
上苍仿佛有意考验他,这一年成了溧阳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之年。六月到九月中旬,近百日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连日来,各区各图纷纷告急。四野盼泽,万家愁叹。
客民聚居的南部山区,“连畦接陇,一片枯焦,令人睹之惨目”。
城北面的情况会稍好些吗?他派人前去观察。结果,“仆辈自西北乡归”,汇报察看到的“田禾受伤之状”,令人“闻之惊愕慨叹”。
九月已是麦种季节,但是无雨不能下种。如果没有“甘霖二寸”,下了种也不可能成活。来年春收的希望,眼看又将破灭。一时人心惶惶。
李超琼白天在外奔走,勘察灾情,研究农事,还要随时调解村民的夺水争端;深夜,经常独自于衙署中庭站立祷雨。祈祷中,他越来越怀疑,天久不雨,会不会是因为他这个县老爷的德行不够,于是割开自己手臂,刺血为疏,向上苍表明心迹。
藩司拨发的二百五十石麦种十月下旬到达溧阳。从当地老农嘴里得知,最佳播种期已经错过,此时播种,来年收成将大打折扣。初为官守,李超琼时时想着:“吾生起乡井,疾苦同齐民。隐伤苛政猛,颇羡阳河春。”[1]他一方面自己掏钱,再添购一百石麦种,尽量弥补损失;一方面恼恨自己对民事“未尽心”,有负官守。
他又了解到一件揪心事。县里用于放赈的稻谷,都是今年地产,而今年大旱,稻谷灌浆不足,每石谷碾成米仅得四十五斤。只有把赈荒稻谷提高到对每个灾民“日给一升”的水平,才够勉强糊口。
为了心目中那片美好的阳河春色,他以知县身份向上申请“截漕二万石”。结果,被严厉驳回。藩司认为,溧阳新任知县所请“冒昧”,“特加申饬”。
他四处约请城里的士绅,紧急追募赈济粮,但为时已晚,效果甚微。十月,李超琼以自己捐出养廉银二百串为开局,在士绅中开办赈灾募捐,再加上藩司拨下的三千串,共筹得一万四千串。这笔钱,如以计口给食的方法,向全县确需赈济的二万九千多受灾人口投放,冬春两季勉强可以维持。即使这样,他还是因为自己“事未尽心”,无力顾及大批散居在沟沟壑壑里的极贫人群而内咎。
那年岁末,李超琼痛定思痛,自撰《劝办备荒事宜》一文[2]在全县各处刊布。《劝办备荒事宜》提出四条意见:修治水利;预防蝗孽;严备虫灾;推广积谷。他认为,境内水利亟须大修。即使因为资金短缺,整治三塔荡这样的大工程不可能进行,至少也应该发动绅民采取“数村通力合作”的做法疏浚支河汊港。来年春天,戴埠一带的河工就会展开。“水利修,则旱有所资,潦有所泄”,戴埠这样的临水市镇才会有“汲饮之利”。他深虑“蝗旱相因”,呼吁人们采用各种手段消灭蝗卵及其幼虫,并且严防各种虫害。
这一年,对李超琼刺痛最深的是:全县十六个区,十几年前就有储粮备荒制度,但由于“生齿日繁”,储粮太少,管理不善,导致关键之时无粮可借。今后,他主张“仿陶文毅公(指陶澍)《丰备仓遗法》,略为变通”,“无论一区一图一村均可兴办。”建仓的办法“听民自便,官吏无待吹求”。“每年秋成后,无分自产租田,每亩捐稻二斤,送入仓内”。“以数岁备一岁之荒,蓄积渐增,自不患其不足”,“以一乡济一乡之乏,见闻最确,更不患其不均”。
可惜《劝办备荒事宜》刊布才半年,李超琼就调离溧阳,这四条措施未能由他亲手落实。
离开溧阳前的那一夜,夜雾蒸腾。照农谚的说法,这又是“久晴之象”。李超琼“悬虑无己”:“溧阳山田,盼雨之心,已迫不可待……”
李超琼治溧三年,尤其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大旱中的表现,得到护理江苏巡抚的苏州藩台黄彭年的褒奖。黄彭年把他列为省内极少几个能“尽心民事”地方官之一。
李超琼调职的消息传开,绅耆士民有赠“教善得民”匾的,有送“循良继美”匾的,有送“德威法明”硃牌的,还有送红缎万民伞的。离任时,溧阳街头,寅僚绅耆“走送者甚多”、“商民皆香花夹道”。
绅耆士民的感戴可能只是表象。在非绅非商的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李超琼是怎样的一个官员呢?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十七日上午的一件小事,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城西图西园村老农民彭荣宝,一大早就踏着一路泥泞,赶到溧阳县城。找到县衙,说是要向知县李大人报个喜:他儿子富根的媳妇钱氏一胎生了三个男孩!
西园村靠近城厢,曾是李超琼治赌的重点地区。李超琼巡乡时彭荣宝曾挤在人群里见过,还说上过几句暖心的话。他觉得家里的喜讯理应让这位县太爷分享。他想不到的是,县太爷李超琼正在心急火燎中。入春以来,溧阳县连日阴雨。过多的降水,有害于蚕,又有害于麦,危及民生大计。李超琼只要夜里听到雨声,就会焦虑得辗转难眠。县里“土民”(原住民)和“客民”(外来兵)矛盾越来越大。导致省里藩、臬两司联名来函,询问溧阳“客民隐患”情况。连巡抚大人也亲自打招呼,要求李超琼“佑‘土’而抑‘客’”(护佑本土人,打压外来人)。但是李超琼不同意,坚持认为,“佑”此“抑”彼,事关政策公平,不能任意偏袒,理是理,事是事,一碗水必须端平。小县令要违拗大巡抚,何等的艰难!能不烦吗?
此刻的李超琼与喜孜孜的彭荣宝正相反,心里不但极烦,而且极恼。省里派来的一位施姓赈灾大员,竟是个糊涂官,一来溧阳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李超琼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七千串救灾钱统统拿去在全县十六个区中胡乱发放,才发了五个区就掏空了,其余十一个区的成批的受灾农户嗷嗷待哺,现在全都归于失望。特别是那些人数众多、无钱无势的“客民”,获赈的希望完全破灭。天灾又加人祸,李超琼正又急又恼,日夜愁思。
但是这万千烦恼,哪里抵得过三个新生命同时降临人间的喜讯!李超琼听懂了彭老头用本地土话作的叙述,立刻放下手中案牍,凑近前来,而且越听越有兴味。他记不起这位老农是在自己哪一次下乡巡访中认识的,但这又什么关系呢?
彭老头越说越来劲,竟然得寸进尺,要求李大人在百忙之中为孩子取名。李超琼欣然应允。他仔细问明彭家的家族字派和孩子们的生辰八字,沉吟良久,一口气报出了三个发音响亮、寓意美好的名字:“近智”、“近仁”、“近勇”。
彭老头大喜,连连磕头道谢。
李超琼意犹未尽,转身回到内舍。寻寻觅觅,翻箱倒柜,凑出一套彩礼来:“银牌三面、彩红一段、绿布三匹、白米三升”,另加上老母亲凑上的“洋蚨(西班牙银元)三元”。
最后,彭老头“欢然而去”。
西园村老农彭荣宝走出衙门后,会怎样向路人说起他的县太爷?回到村里,又将怎样向老乡说起他的县太爷?在睡梦中又会怎样想起他的县太爷……
这些都没有记录。但是都不难想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