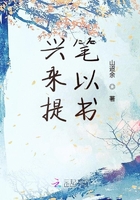杨深秀字漪村,山西闻喜人,生于1849年,时年49岁。历任刑部主事、山东道监察御史等。1898年初,与宋伯鲁、李岳瑞等人发起成立关学会,是维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年近半百的杨深秀在政治上一直比较激进,特别是其言官身份使他养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在1898年政治变革中,杨深秀最早上书朝廷请定国是,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杨深秀认同康有为等人的主张,不仅与康有为及其门人走得近,而且像徐致靖那样,总是将自己的名分借给康有为等人使用。所以在1898年杨深秀的那些奏折中,有不少内容虽然代表了杨深秀的认识,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手笔,而是康有为或其他什么人动手起草的,只是以杨深秀的言官身份上奏朝廷而已。
由于杨深秀与康有为走得近,在政治理念上接受了康有为的许多看法或判断,也就比较倾向于使用类似于“阶级分析”观点去看待朝廷,看待皇上与皇太后的关系,而且有时似乎显得还不那么严肃和谨慎。根据杨深秀同僚文悌的记述,当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时,同为言官的杨深秀、宋伯鲁积极参与,文悌见到后就设法告诉杨深秀,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身为言官,自有表达政治见解的方式,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参与社会上这样的政治组织。文悌的说法引起了杨深秀的重视,杨深秀旋即便服前往文悌处详谈,解释康有为的主张,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积极参与这些政治组织。更重要的是,就在这次谈话中,杨深秀说了一些文悌“万不敢出口”、万不敢转述的敏感话语,而这些话语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其实就是康有为对朝政的分析,就是有关皇太后擅权揽权而皇上无权之类的话题。对于这一点,文悌在那份检举书中说得很明白,杨深秀的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的创见,而是受康有为的煽惑。
杨深秀反对皇太后揽权擅权,当然有康有为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其实已经转化为杨深秀的认识。根据一些同僚的记述,杨深秀似乎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分场合不计后果,常常昌言假如给他3000杆毛瑟枪,他必将扫平颐和园,逼迫皇太后还权于皇上。
根据这样的认识,当皇太后出园三度训政的消息传出后,杨深秀应该很快就知道。他或许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这样严重,或许不知道康有为的阴谋会泄漏,或许相反,他意识到康有为出走已充分暴露了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变革走向末路和失败,所以他发誓要垂死挣扎、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用自己特别的方式诘问皇上为何被废,请求皇太后迅速撤帘归政,并且匆匆前往军事将领董福祥那儿,试图劝说董福祥首举义旗,出兵勤王,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康有为没有达成的目标。
杨深秀是一个坦诚的人,他的这些计划并不隐藏在自己胸中,究竟是哪一个渠道将他的计划泄露给了最高层,我们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坚定的皇权主义者,坚定反对皇太后干政,甚至不惜煽动军队进行勤王,甚至自诩为骆宾王第二,期待满洲八旗军事将领中能够有人深明大义,仿效大唐徐敬业高举义旗,拥戴皇上,废黜皇太后。可惜,杨深秀的这些部署只停留在言论层面,并没有成为事实,当然这也不影响他成为清廷第一批要惩处的对象。
清廷第一批惩处名单中除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三人之外,就是十几天前刚刚出任军机章京的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
杨锐的情况,我们已有很多交代。我们知道他不仅不认同康有为激进的政治变革主张,反而持严厉批判态度,他是张之洞的门生弟子,在思想理念上更倾向于张之洞的渐变思想和主张,所以他在皇上恳切要求出主意化解危机时,很自然建议皇上抛弃康有为。建议皇上重用那些稳健的老臣,不要完全听任那些狂躁的政治新锐的极端建议。然而到了康有为阴谋败露时,康广仁,可能还有后来受审的其他人,都多次提及皇上的密诏。而皇上在被皇太后追问是否知道康有为围园弑后阴谋时,是否有一个什么密诏时,大约皇上也不能不说真话,于是杨锐也就成了1898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阶下囚。杨锐对此当然不会服气,根据张荫桓后来的说法,杨锐被逮后曾公开辩白,说自己当差不过五日,而又没有上过一个折子,反而与他人同罪,这难道公平吗,这至少对他杨锐是冤枉的。
与杨锐的情形相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是林旭,林旭拥有相当的政治背景,且与荣禄等政治大佬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年仅24岁,少年气盛,观点偏激,对康有为那些极端言论拍手叫绝,赞不绝口,是康有为激进政治主义的积极追随者。但是,当杨锐向皇上指出康有为的问题后,林旭大致能够接受杨锐的分析,且配合杨锐劝说康有为离开北京。只是康有为走得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结果就弄巧成拙,惹出了极大的政治麻烦。林旭认为自己所作所为皆为君子之行,因而当他被逮之后,也曾坦然追问审讯者自己何罪之有,遭此大难?这一点与杨锐的情形非常相似。
至于谭嗣同,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谭嗣同是康有为全部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是他从湖南唤来了一批江湖弟兄,也是他当面劝说袁世凯,并承诺会从皇上那里取到一份密诏,诛杀荣禄、围园弑后。谭嗣同太清楚这个事情的性质和可能后果,所以当他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他就准备为这件事情献出生命。而且,仅仅凭借他在江湖上的地位和影响,他当然可以轻易逃出北京,逍遥江湖。但是他知道,他假如真的那样逃出北京,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必将受到极大损害,人虽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所以当康有为离开北京后,特别是当康有为成为朝廷通缉对象后,谭嗣同没有选择逃亡,而是选择了留下,选择死亡。
根据梁启超《谭嗣同传》的说法,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朝廷下令抓捕康有为、搜查南海会馆时,他正在谭嗣同住处商谈一些事情,当他们听到皇太后将出园训政的消息后,谭嗣同从容不迫地叮嘱梁启超,过去几天一直想着救皇上而现在已无所救、无需救,现在想救康有为而亦无所救不能救。他谭嗣同需要做的事情已经不了而了,剩下的只是等待死亡。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他好言劝说梁启超试着进入日本公使馆,尝试着去找伊藤博文,请求伊藤博文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发个电报,想办法救助保护康有为。
按照谭嗣同的叮嘱,梁启超于9月21日匆忙前往日本公使馆拜谒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并在伊藤及林权助的劝说下,当天晚上就留在了那里。而谭嗣同在那一天那儿都没去,静静地呆在家里等待着步军统领衙门的捕役。等了一天一夜,到了9月22日,仍然没有逮捕他的消息,谭嗣同遂前往日本公使馆与梁启超相见,劝说梁启超争取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流亡,并将自己的一些著作手稿及家书等一并交给了梁启超,郑重其事托付后事,表示自己心甘情愿为中国的维新事业献出生命,理由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现在康有为生死未卜,谭嗣同与梁启超相约,由他谭嗣同去死,以死去激励国人,以报圣君;由梁启超坚持活下去,继续维新事业。说到这里,谭嗣同与梁启超一抱而别。
在此后几天,谭嗣同也没有消极地在家里等死,等着捕役来抓他,而是利用自己与江湖上的复杂联系,想方设法谋救皇上。只是由于朝廷已有严密防范,江湖力量远不足以在北京发难。9月24日(八月初九日),谭嗣同被列为第一批抓捕对象,到了第二天(9月25日,八月初十日),谭嗣同从容被捕。被捕前,仍有朋友苦劝谭嗣同东渡日本逃亡,但他死意已决,坚辞不走。他坦然告诉这些朋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这大约就是中国一直无法摆脱危机、重建辉煌的根本原因。我谭嗣同现在选择这条不归路,希望以我的鲜血和生命为我中国换来一个美好的前程。
梁启超的记述当然有演绎的成分,只是大体上说来,这个记述比较合乎谭嗣同的内在心情,他后来之所以在刑场上破口大骂,正是这种心情的真实流露和反应。
9月24日被下令逮捕的最后一人是刘光第。刘光第生于1859年,时年39岁。他长时期任职刑部,只是数天前方才因陈宝箴的保荐,被皇上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务。在政治理念上,刘光第与杨锐一样,对张之洞等人的政治稳健主义比较倾心,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略有反感,在本质上并不是康有为、谭嗣同、林旭一派的人物,只是他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四人同时被任命,在与谭嗣同同班值守时,也曾有过合作。最主要的是,皇上在颁给杨锐的那份密诏中,也曾将刘光第列为杨锐、谭嗣同、康有为一类的同志,这大概是刘光第被逮捕的主要原因。刘光第被列为第一批通缉捕拿对象,显然有点冤枉,有点扩大化。这大约也是在政治危机突发初期难以避免的情形,但愿随后的审讯能够弄清真相,分清是非,分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