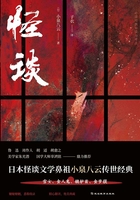有一年老伴过生日,九时刚过,两个女儿、女婿即已登门。小儿子、儿媳头天早已置办好了蔬菜瓜果、生熟肉食。于是,剥葱剥蒜的,剔骨切肉的,烹调煮炒的,一片忙活景象。只是不见大儿子、儿媳过来。不一会儿,大儿子骑着摩托,带了啤酒、饮料等物来了。原来是大儿媳艳琴的爸爸领了本村的两位匠人给大儿子厨房里贴瓷砖。因为我的这位亲家翁在村里是红白喜事上的一把烹调好手,艳琴完全能腾出手早点过来。大儿子说,人家艳琴爸也是今日生日,艳琴今儿不叫她爸动手,做好几个菜就过来。原来亲家翁和老伴是同一天生日,大家都十分惊喜。只是因为亲家两口子比我俩要小十来岁,从来不过生日,所以艳琴一直没有说过此事。
没一会儿,艳琴过来了。小儿媳慧平就笑着逗艳琴:姐姐(她们妯娌俩以姐妹相称),两家老人生日凑得这么巧,往后逢到这一天,我看你是给咱妈过生日呀还是给你爸过生日呀?惹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
不料,大儿媳艳琴说,还有更巧的哩,我娘家大妈和咱爸(指我)也是同一天生日,都是农历七月初四!
在人们的惊讶声中,大女儿月枝笑着向艳琴说,怪不得咱两家结亲哩,咱们两家确实有缘分嘛!说得满屋子人的笑声更高了起来。
2005年4月26日
童年的吃食
如今的儿童食品,名目繁多,花样齐全,真乃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和孙子进了超市,哪种食品好吃,叫什么名堂,孙子比我懂行得多;我却只能像个“食盲”一般,任由孙子挑选……
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那时的乡下,冬夏卖食品的只有很少的几种;虽则如此,回想起来,还是满有兴味的。
我家对门住着一户韩姓人家。韩爷爷卖点针头线脑的小物件,也有点糖蛋之类的小吃食。最早引起我兴趣的,就是那红白相间的糖蛋儿。韩爷爷右眼的半个下眼睑红红的翻在外边,总是湿淋淋、水汪汪的;韩爷爷还有个特点,每次大便总要走到500米开外的关帝庙后他的地里去,所谓“肥水不流他人田”吧。小时候很羡慕韩爷爷的商品摊,以为能卖东西的总是很富有,大点后才知韩爷爷家其实也很贫寒,靠几亩薄田和小买卖勉强糊口。但韩爷爷并不吝啬,也许是邻居的缘故,有时候会给我一两个红白相间的糖蛋儿。每每吃过韩爷爷的糖蛋儿,心里美滋滋的能甜上好多天。
冬天乡下卖吃食的,最常见的就是糖葫芦和芝麻糖了。糖葫芦我们当地叫山楂串,由于有点酸,吃了牙痒,我并不太喜欢;我最爱吃的是芝麻糖。这是一种用小麦粉发酵后制成的棒形空心糖,周身粘一层白生生的芝麻,吃起来酥得掉渣儿,又有点黏牙;但正是这种甜得既酥又黏牙的劲道,才显得特别的有味儿。虽然来村里卖芝麻糖的小贩几乎天天都有,大人半月二十天,才会给我和弟弟每人买上一根,算是解解馋儿。
有一年小学校放了寒假,不知谁家孩子带了头,从城里贩了芝麻糖来卖。于是我和几个小伙伴也都跟着效仿。我家有个三尺长、尺半宽的旧木盘,正好可摆放芝麻糖。因为年纪太小(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我和一个李姓的同龄小伙伴合伙儿,白天两人用四股绳抬了木盘到邻村去卖芝麻糖,晚上大人将木盘放在屋棚上靠窗口的地方,不但安全,而且冷风吹着,芝麻糖又化不了。两家大人叮咛我们,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根糖和掉下的芝麻粒儿,我俩为了这第一次做生意能赚点钱,也很能自律。一次从邻村返回的路上,记得是下一个小土坡,木盘的一头触了地,把整盘的芝麻糖翻在了地上,大部分芝麻糖都碎成了两截儿;大人们哭笑不得,只好两家把碎糖截儿分吃了。虽然没能赚了钱,我们却大大过了一次芝麻糖瘾。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经商活动。
时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年冬季,我总喜欢买几根芝麻糖吃。
夏天,我最爱吃的就数粽子了。农历四月的下旬,乡间就能听到卖粽子小贩的吆喝声,粽子!黏米粽子!但家人是很少给我们买粽子的。偶尔买回两个粽子,我和弟弟一人一个,剥开粽叶,那黄黄的、黏黏的黍米(那时都用黍子,不像现在用江米)中间,三两个红枣隐约其间,一股香甜的气味弥散了开来;我和弟弟总是小口细嚼慢咽,悠悠地品尝,直到把粘在粽叶上的黍米颗儿舔得一粒不剩。母亲看着我俩贪吃的馋相,总是安慰我们:粽子太小,又贵,买着不合算;赶到端午,咱们自个儿包粽子吃!
端午节的前一天下午,母亲就开始包粽子了:先是把头年用过的粽叶用开水泡软了(母亲总是舍不得将用过的粽叶扔了),将两三片粽叶排列好,在适当的地方折了回来,用一块洗净的砖压上,又将黄澄澄的黍米和枣儿泡在一个冷水盆里。母亲是我们家唯一的会包粽子的好手,包出的粽子又好看,又匀称。她在粽叶打折处旋转形成一个角,从水中捞出一撮黍米把底角填充了,再把漂在水面上的枣儿放进两三粒,用黍米填满,像挽花儿一般,一个四角饱满的粽子就显形了。母亲用嘴衔住绑粽子的粽线(用粽叶撕成的细条)的一头,用另一头在粽子的中腰处一缠绕,一个粽子就包成了。母亲说,咱们河北老家包的这种四角粽子,比当地卖的扁平的三角粽子好绑,且结实不易散。往锅里摆放时,母亲总是一手抓两个的点过数目,添上冷水,用一个铁箅凸面朝下,上面压了秤锤,盖上笼盖,在院里蒸馍灶上,点着木柴,烧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夜里,我朦朦胧胧中觉着母亲总是要出去添柴,点水,使锅内一直保持着滚熬状态……
平时早上大人叫不醒的我和弟弟,端午节这天总是早早醒来,顾不上洗脸,便剥开粽叶,狼吞虎咽地吃起粽子来。整个院子都弥漫着粽叶粽子的清香。母亲劝诫着,慢点吃,小心咽着,多着哩!看着全家人喜形于色,尽情地、惬意地享受着自己的劳作成果,母亲从心里往出甜。
随着母亲渐渐走向老迈,为了不使母亲的包粽子技术失传,我有心地学会了这套技术。母亲谢世后,我年年端午节给全家人包粽子;尽管超市里卖有多少种馅儿的粽子,都没有我们家的粽子味正、地道。
作家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卖糖》一文中写道:“小时候吃的东西,味道不必甚佳,过后思量每多佳趣,往往不能忘记。”实在是道出了我们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话。
2007年8月15日
好人范升元
自打我到省文联工作的时候起,老范就已经是单位的炊事员了。他是怎么来省文联的?在省文联工作多长时候了?不知道。我也从没有打听过。——在了,就在了吧。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他,个子不高,瘦瘦的,四十多岁,方脸盘,面貌白净,要不是额头有太多的皱纹,应该还算是漂亮的。许是家境贫寒,他孤身一人。听说年轻时在老家祁县某个“大院”当过用人。风言风语的,说他似乎有什么生理缺陷,但他确实一生未娶,这是人人皆知的。
老范的脾性极好。我在省文联工作的十多年间,从未见过他和谁拌过嘴、红过脸,人也极善良。那时在灶上吃饭的也就是十大几个二十来人,大都是机关的单身、年轻人,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致耐心地奉侍大伙儿。这十几个人有作协的、美协的,还有行政、总务上的,不在一块儿工作,来吃饭的时间前后不一,又免不了有出外办事的,谁们吃过了,谁个还未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总是坐在卖饭窗口里边,等到一个不剩地都吃过了饭,他才会离开窗口,去宿舍休息一会儿。他是把单位真正当作自己家了,他要在这儿干好一辈子,也要在这儿养老,靠机关为他送终。
他身为炊事员,吃饭极为简单,从不贪嘴偏吃。他吃素,不沾荤腥。中午吃面条,面碗里从不浇菜。只在面条里撒点盐,倒点醋,搅拌上多多的红辣椒,整个碗里红洼洼一片,辣得他一边嘘嘘有声,一边呼噜呼噜往嘴里吸面条,额头、鼻梁上也就浸出许多微小的汗珠来。
他又特干净,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厨房里、宿舍里到处收拾得利利索索,睡床旁边红漆大衣柜子总是擦得锃亮。后勤、总务上的几个年轻人,都爱在他宿舍里闲坐,说笑打闹。
老范生活上极简朴。工资虽然不算高,但他开销甚小,众人都知道他有不少结余。他那个红衣柜常年上着锁。老家有个侄儿,每年都来看望他几次,侄儿走时,他总是给侄儿塞点钱,很大方的。老范真是个好人、善人,一个侄儿,他也舍得给钱。人太善良了,就有个把不良之徒打他的主意。有次,大天白日,他离开宿舍没多一会儿,大衣柜上的铜锁被撬开,辛辛苦苦积攒的钱被盗了个净光。显然,偷盗者出不了在他家玩笑打闹的“常客”,是掌握了他家底细的;他也许能猜测个八九分,但他只说,咱又没有捉住人家把柄,不能胡说人家呀!只好把被打掉的牙咽进肚里。
“文革”的第三个年头,山西省级机关的干部、职工奉命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说,他一个炊事员,又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造反”组织,甚至连机关里两派组织的名称也叫不上来,每天只管自己做好饭,这派、那派,他总是一样对待,本不必去学习班的;但是,他却去了。许是当时机关的主事者认为,既然没有一个人吃饭了,去了学习班还省得他自个儿起灶。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消除派性,但他是全机关最没有派性的人,应该说,在学习班里他是最没有精神负担、最为轻松的人了。但是,突然一天夜里,我们都被惊醒,说是老范自杀未遂——他用刮脸的刀片割自己的喉管,被人发现制止了,脖子处流了不少的血,叫校医给缠了绷带。于是,我们都被排了名单,白天黑夜轮流监护,守在身旁;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管谁们追问,老范从没有吐露过一个字。我总觉着这和他在单位丢钱的事有些干系,许是有人威胁他:如果他揭发此事,将要对他如何如何?老范胆小怕事,又对学习班的大局很不了解——这种事情根本不是学习班要解决的事,作贼者心虚,一威吓他,他就走上了这条路。自然,这只是我的揣测。因老范始终一字不吐,也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中央学习班结束后,我就离开了省城。1984年底,省文联与省作协分家后搬到迎泽大街上去了,省作协还在老地方——南华门东四条,老范也原地未动,成了省作协的炊事员。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仍是那样地热心、细心、耐心,尽职尽责地为大伙儿服务。我有时去省作协,见了面,他总是十分亲热地问这问那,还要问讯和我同在省文联工作过的同乡赵士元的情况,托我向士元问好……
后来,我有两次去省作协,都没有见到老范的面。心想,老范可能不在人世了,省作协定会为这位曾在单位干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好好地送终……便试探着向作协的老同事打听。同事告诉我,哪里!老范回祁县老家了!我说,他孤身一人,回的什么老家!同事说,你不记得有个常来看望他的侄儿吗?原来那是老范的养子,因老范长年不在家,养子在他哥哥家长大,就叫成侄儿了。侄儿把他接回老家了。
啊!好人范升元!
他是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善良、诚实。他在省文联、省作协干了多半辈子炊事员,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像春蚕吐丝,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却对单位无任何企求。因为善良,免不了会有个把不良之徒算计他、欺负他;也因善良,受到众人的喜欢和称赞。老范离开了省文联、省作协,和他共过事的人无不怀念他。祝愿老范在老家过得幸福愉快!
2007年10月10日
冥婚
瞎子吴眼死了。
活了50多岁的吴眼,只过了17年有光明、有快乐的日子,其余全是过的暗无天日的苦焦生活。吴眼并不是生来瞎。要不是17岁上一次撞车瞎了双眼,他本来完全能过上普通农家的自在岁月,就因为双眼失明,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许多农活做不了,又无一特长;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是个智障农妇,家里日子过得紧巴,自然连个媳妇也娶不上。邻里看见吴眼恓惶,东家送他一件旧衣裤,西家给他一双旧鞋袜,瞎后几十年来,吴眼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逢年过节也是如此。村人说过大年的也不给娃换件新衣服,他爸说,身上的衣服不破不烂,摸着光就行,他能知道是新是旧?比生来瞎盲人的一点长处是,他因未瞎时对村里的大街、小巷都熟悉,眼瞎后在村里走路从来不用拐杖,一切跟着感觉走,众人逗问他这是走到谁家门口了,他能说得准确无误。他又常常热心帮助人家干点力所能及的出力活,谁家用小平车拉土、送粪,他驾辕里,只要主家有个小孩一旁扶住辕杆引路就行;遇上人家调煤,他就抡起镢头,“你给翻,我给砸”,一干就是一晌,末了,主家叫他吃一顿好饭,临走,还忘不了叫他拿上一两件旧衣物……
吴眼在六七岁上,他妈给他生了个妹妹,倒是不聋不瞎,除了憨吃傻笑,什么活也不会做。吴眼爸一人在生产队干活,要养活两傻一瞎加自个,生活的困顿可想而知。生产队对他这个欠款户破例粮、油照分。这傻女子长到20多岁上忽然失了踪,是自个走失了还是被人拐去做了生娃机器,丢失得不明不白。村里人看见吴眼爸不急也不找,不仅不追究,都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