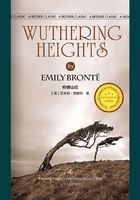潘家兄弟姐妹五人中,潘伊玲排行最小,加上天使般的美貌和出众的聪颖,爷爷自然视之为掌上明珠。就因为这个原因,全家上下,既有洞门钥匙,又有通道钥匙的,除了老太爷,就潘伊玲一个。
只因一年前,原袁世凯的亲宠奉新主子之命到江浙来办差,曾悄然落脚于潘家密室中。潘伊玲并不知情,独闯密室找爷爷,不想撞见了那亲宠,由此种下了祸根。
时下,潘伊玲避过下人耳目,拖携着康凌光,关死洞门,拽上吊桥,来到了小屋内。待铺摊好席子,她便“命令”康凌光脸朝下平躺好并解开裤腰带。康凌光这才悟出她今天神神秘秘举止中的这份别有用心,十二分不情愿地说道:“你这是存心要违反校规,解裤腰带更是多此一举。”
康凌光没有看到潘伊玲苦涩的笑容,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凄美。但分明感觉到对方少了往日巧舌如簧的那分镇定自若。“在家里谈校规,就如围棋盘里下象棋,装什么正经!不解开裤腰带,怎么找你的尾椎?”说着,她跪坐在康凌光的左侧身旁,一手撩起康凌光衬衫的后衣盖,见康凌光仅是松了裤带,便嗔怪起来:“还算是个新时代的男子汉,内里竟是那么封建保守,你的屁股还真懂得知羞!”说完,两手一拉裤腰,康凌光的小半个屁股白生生地露了出来。
素来不苟言笑的康凌光这回也来了劲:“我说潘大小姐,到底是搞人体素描,还是练推拿按摩?”康凌光本想要聊上几句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进了别人设下的套子。他寻思着,这般一入套,无论你来而不往,或是有来有往,都将会置自己于尴尬之地。就不知这反常之举的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他了解她的脾性,轻易是问不出来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潘伊玲似乎更乐了:“就你那屁股蛋,也想当写生模特?”她咯咯咯地笑着,一节一节地按下去找准了腰椎上方的第三椎,就推拿起来。
才过一会儿,潘伊玲就柔声问道:“有热的感觉了吗?”
康凌光回答说:“你一摸,我心头就发热。”
此时此刻,潘伊玲要的正是这种异性效应,但她装作气恼地说:“我摸着你什么啦?不要脸的东西!”说着,抡开两个肉锤子,鸡啄米似的敲击康凌光的光背。
其实,康凌光刚才说的,半是玩笑,半是真话。潘伊玲推拿时,两个臂肘时不时拖泥带水地在康凌光的肌肤上刮过,暖烘烘的鼻息也在背上游动,有血有灵的成熟肌肤,怎能禁得住异性有意无意地撩弄,康凌光早已是热血奔涌。
潘伊玲抡够了,示意康凌光翻过身来后,假怒道:“我不想看见你的死皮赖脸。”便背对着康凌光,蹲坐在一侧,做起腹部按摩来。
才按摩过三圈,觉得蹲着不易使力,回过身来,索性骑坐在康凌光的双腿上,低着头又按摩起来。黑发似瀑布一般披挂下来,恰到好处地遮掩住自己的脸,却又能窥视捕捉到对方表情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
康凌光和潘伊玲虽情同手足,课间也常常是形影不离,但像这般私处一室又有这样的肌肤接触还从来没有过,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感到很不自然。但慢慢地他分明觉得对方的心思也许比自己还慌乱,那指法全没按教程规定的运行,与其说是按摩,倒不如说是在擦拭明代的青花瓷。康凌光正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便开个玩笑想提醒一下:“你的指法全没按教学要求运行,这回我的裤腰带没碍着你的手脚吧?”
不料,立马遭对方猛烈反击:“再油嘴滑舌,扒光你我也敢按摩。”不过,话才出口,潘伊玲自己的脸已烫得比按摩过的还厉害。
心事重重的潘伊玲急于要完成重大的历史使命,已无心于实习操练了。她紧挨着康凌光仰面躺下后说:“该你了,动手的能力我承认不如你,示范给我看看——高才生!”
康凌光不得不坐起来,用商量的口气说:“这实习反正是只练不考的,又何必太认真……”
潘伊玲“哼”过一声,截住康凌光的话头说:“我料定你会来这一手,你要做君子,就该让我难堪?今天你若要耍弄来而不往的把戏,看我怎么收拾你!”
面对“威胁利诱”,康凌光无奈地说:“是你拖带我来的,逼人上了梁山,还要倒打一耙……你的裤腰带还没有解开,怎么示范?”
潘伊玲偷笑一下说:“现在,你是医生,我是你的病孩,一切由你来处置。要真有病孩来求诊,难道你叫婴儿自己解裤带不成!”
康凌光不自然地一笑说:“看来,你倒真像个孩子,一个不会解裤带的婴儿。” 康凌光的手第一回失去了利索,当他笨手笨脚地解开牛皮裤带的铜扣后,又慢慢轻轻地将裤腰拉至肚脐眼。整个过程仿佛特工人员拆除定时炸弹一般小心谨慎。
康凌光才要按摩,只听潘伊玲说:“公平一点嘛,你到底怜我是女孩,还是欺我是女孩?”
康凌光认真起来:“男女有别么,我们已经违反了实习的有关规定——只要好按摩就可以了。”
潘伊玲诡秘一笑后不依不饶道:“亏你还懂男女有别,瞧你那直露露的眼神,料你不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既然如此,还是把裤腰拉上来一点。” 康凌光不知是计,抓着裤腰才要往上拉时,潘伊玲两手紧抓住康凌光的手冷不防迅捷一推,立时袒露出一小片女性油黑黑的盎然春色……
就那么一瞥,康凌光只觉全身的血液刹那间都冲向了脑门……他急着去提拉裤腰,裤腰才拉起,只见潘伊玲轻撩衣襟,让白嫩嫩的胸脯尽显尽露……那突如其来的艳姿艳色,顷刻间冲垮了康凌光仅有的那道脆弱的防线。他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潘伊玲伸手来拉他……两具白皙的肉体才如胶似漆地缠在了一起……
情欲的狂潮渐渐退下去,香汗涔涔气喘吁吁的潘伊玲赤裸着站起身来,康凌光抬头看时,好一派“花带雨露花更艳,缭乱春意惹人眼”的异样春色。
当潘伊玲从毛巾架上抽了两块毛巾返身回来,将一块毛巾抛丢给康凌光时,发现了康凌光眼中异样的神情,便揶揄开了:“我把身子和贞洁都交付给了别人,可那人一边享着快意,一边骂我轻薄放浪。”
康凌光站起身来,忙着辩解道:“我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去想,骂你还不等于骂自己?只是我分明觉着你今天太反常,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你好似有什么隐情瞒着我。”
潘伊玲的神情黯淡了下来,接话说:“凌光,没什么反常不反常的。说我出格我也认了,反正我的身子是迟早要交给你的。不过,确有你所不知的,明天,我就要启程到南洋去了。这一走,虽说是两年的期限,但说不准是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康凌光更是摸不着头脑,瞪大了眼睛说:“你毕业论文还没有交,为什么说走就走,连句商量的话都没有,走得又是如此仓促?”他一把紧紧搂住潘伊玲,仿佛这美丽的胴体立刻就要离他而去。
潘伊玲喃喃地告诉康凌光:“毕业论文对我来说已无足轻重。”
接着,她把袁世凯的一个亲宠要纳她为妾,她对爷爷使了个缓兵之计,言称只有去南洋留学两年才肯答应这门亲事,否则只有一死的事和盘托出。并说:“等我在南洋立足之后,你再设法远走高飞。到那时候,我们自可同结百年之好。”
“一个年轻、容貌又不算太丑的女子,孤身一人在外,凶险更是难以预料。今天这样草率行事,看似荒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自己虽没有贵妃身,貂蝉心,西施志,昭君魂,但自己的肉身意欲一样是纯洁的。凌光,你能理解我吗?”
康凌光手抚着柔滑的胴体,用热吻堵住了潘伊玲伤感的情流。他愤恨于有人要横刀夺爱,更为潘伊玲的计划生忧:“你爷爷老谋深算,那亲宠又是何等人物,他们会让你心想事成吗?”
潘伊玲苦笑一下说:“是呀,我爷爷谋爵位,拿我作买官的本钱。当然,与其让他卖我,还不如由我自己来卖!那亲宠贪色成性,早已做着窃香霸玉的美梦,他们谁也不会放过我。然而,他们又谁也不想失去我。这就给了我一定的周旋余地。只要到得南洋,任那贼人权高位重,也是鞭长莫及,由不得他了。”
“当然,不排除有万一。正是为防不测,我才提早把身子交付与你,你还觉得反常吗?”
潘伊玲语带凄艳悲柔。这次分手,纵然不见得就是有情人的生离死别,却分明是一对痴情鸳鸯要天各一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