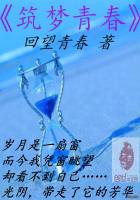拐脚阿婆看了看秀梅白白嫩嫩的小腿肚子,啧啧啧地笑夸起来:“看你这小腿肚子,真像根脆生瓜,又白又嫩,指甲一掐定能掐出水来。十七八岁,真是女人最水灵的时段,可也常常是女人惹眼招风生祸的当口呐!”
秀梅知道自己的小腿肚自要比别的女孩的丰润得多。可也就是个小腿肚,而且,还是女人夸女人,就已经是形状、颜色、质感都出来了。怪不得大旺吻舔自己的脸颊时是那样的贪舌。他要是第一次吻自己的小腿肚,不知又会是怎样的一种贪婪劲。
秀梅正想红了脸,笑了笑说:“阿婆这么夸我,怪不好意思的。”回话的当儿,秀梅盯住了水中的两只蛤蟆,只见一只大肚皮蛤蟆驮着一只瘦瘦的蛤蟆在水中一划一撑地游动着。要是在几年前,她还以为上面那只是个无赖,非一脚把它踢下来不可。现在也知道了,他们也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儿。
不远处的水草里有鱼儿在打唧唧,准是鱼儿太欢了,蹦出水面,搁浅在河滩边的水草上,昂头摆尾地亮闪着身子,全无半点忌人之意。
小时候,秀梅曾不至一次地问过奶奶,奶奶总是说,那是鱼儿打亲亲。秀梅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打亲亲”是什么意思。奶奶笑着说,等你长大了,自会懂得的。
秀梅拉着阿婆的手,趟过峡沟去。心头却想着:这鱼儿怎么也像年轻的男女一般,会打打闹闹着相亲相爱?那得意忘形得蹦出水面的,不知是雌的还是雄的,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她甚至想:要是大旺今晚有意,就让他亲个够抱个够摸个够……这回她想得脸成了张红纸,羞答答避开拐脚阿婆的目光,低下头去。
拐脚阿婆似看透了秀梅的心思,但她只是一笑而过:哪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没有一展芳心的念头……
当一老一少从坟岗地上走下滩坡时,秀梅的小布袋里已是满满当当了。因为多了一份特殊的见面礼,秀梅的心头也新添了份满足感。
返趟过峡沟,两人站在草皮地上洗脚穿鞋。拐脚阿婆说:“早些回家,你奶奶怕是早等急了。回去,代我问你爷爷奶奶好,顺便也代我问声三奶奶好,不要忘了。”
这坟岗河的两滩上几乎是一寸不剩地长满了密密层层的青柴火。浅水滩处的蒲草连着下滩头的芦苇,芦苇又连着滩岸头耐旱的干戈柴。书本上找不到“干戈”这个学名,这是村民们对这种植物的一种形象化的称谓。
干戈柴的叶片通常二三尺长,像一把把狭长的双刃剑。说它是戈,一点也不夸张。那叶面的两边上密布着尖利的锯齿。裸露的肌肤要是被它轻轻一带,就会拉开一道细细的血口子。所以,平日里,人们又习惯称坟岗河叫干戈浜。
干戈浜两滩的青柴火绵延十几里地,只有在坟岗地的滩头留出丈把宽的一段缺口,那是多少年来遭人们踩踏的结果。
或许是多得了点阳光的恩惠,也或许是额外得了人尿水的滋润,这缺口两头的干戈和芦苇长得特别的高密粗壮。这自然也成了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玩吓人游戏时最好的藏身之处,让意中人吓一跳后大叫一声,再哈哈哈地笑一笑,乐一乐,逗乐游戏便在不经意间在全了让对方快乐的心愿。
人世间的真情真爱总是在不知不觉地为成全别人的过程中显得更加可亲可敬可爱!
然而,这人世间也天天上演着邪恶势力野蛮摧残善良、粗暴蹂躏圣洁的悲剧。而这一老一少,又怎么会料到,灾难正一步步向她们逼近。
当秀梅扶着阿婆才近滩岸头,横堵里突然闪出一个精瘦的男人,伸出双臂,挡住两人的去路。他两眼直往秀梅身上瞟,嘴里不干不净地说:“哪家的小娘子,嫩得水都要出来,野出来想勾男人吧。”
秀梅惊呼一声扭头就往滩西口跑。拐脚阿婆一边催秀梅快跑,一边怒斥那个精瘦的男人:“你别长着个人样净说畜生话,小心来世遭报应。”
“看来你今世已经遭了报应,前世你准是个烂货,去你的吧。”精瘦的男人说着,一个扫堂腿将拐脚阿婆扫倒在地上。
秀梅才近西滩口,冷不丁跳出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张臂拦住了去路,嘴巴叽里咕噜着:“花姑娘的别怕,皇军的大大地喜欢……”
秀梅怎会料到此时此地会碰上个东洋鬼子,惊吓得如一盆冰水从头浇下,全身哆嗦起来。只有脑子清醒着,在阿婆催促着快跑时,一扭身向滩口冲去。
那胖鬼子像是见到了羊羔的恶狼,一拱身,跃跳着,跑得飞快。两个男人很快联成合围之势,秀梅只得转身向坟岗地跑去。两个男人四目相对,奸笑着放慢了追赶的脚步。
拐脚阿婆躺在地上,试了两次都未能站起来,只觉得那条好腿也不听使唤了,钻心的疼痛使她直冒冷汗。她直骂自己,怎么不明就里把姑娘领到这里来了……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伸开双臂要拦两个男人的去路:“要害害我老婆子,不能糟蹋那姑娘,你们不能糟蹋那姑娘……”
眼看胖鬼子要绕她而去,拐脚阿婆一把扯开了自己的衣襟,那是一对未曾哺育过孩子的依旧丰耸着的乳房……
胖鬼子定睛间发现姑娘快要爬上坟岗地了,一声:“八格。”撒腿要追。拐脚阿婆一把死死抱住了胖鬼子。胖鬼子使劲扭摔了两次未能脱身,恼恨之极,拔出长柄匕首就朝拐脚阿婆的上胸部刺去。拐脚阿婆惨叫一声,瘦男人趁机将她拉翻在地上。
胖鬼子边跑边叫着:“王兴才的,路口的把好,老婆子的不叫,你的大大的功劳……”
拐脚阿婆仰躺在地上,伤口血流不止;疼得没了一丝力气,一动都动不了;心口像是压上了块大石头一样……想着秀梅,急得大喊起来:“救命啊,快来人啊……”
随着喊话声,一股鲜血跟着从伤口冒出来。她只喊出一声,嘴就被堵上了,然后,眼睛被蒙住了,手也被攥住了。渐渐地,她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秀梅边跑边扭头找阿婆,就像那只受伤的小兔子越发不愿意离开兔妈妈一样。
胖鬼子边追边叽里呱啦着脱去了上衣,裸露着冬瓜一样的胸背。胖鬼子越追越近,秀梅不敢再扭头。
秀梅她越惊怕越气急起来,脚步越来越沉重……胖鬼子连着飞跨了几步追上她,一个背后抱,紧紧将秀梅抱离了地面。
秀梅惊叫一声后,大声急喊着“阿婆,阿婆”,就是听不到阿婆的回应。离了地的两只脚不住地踢蹬着,两手使劲掰着、抓着、抠着,怎奈何得了胖鬼子铁箍一样的臂围。
胖鬼子“嗨哟”一声,一个闪身,将秀梅摔了个仰面朝天,跟着一脚踩住秀梅的肩头,腾下手去解裤带扣。
秀梅拼尽全力,翻身起来,还未站稳,胖鬼子抬脚扫向秀梅的膝弯。秀梅膝弯一软,人失去重心,跌坐在地上。胖鬼子狞笑着,按住秀梅的肩头,一用力,将秀梅扳倒在地上。
不知是顾不上还是不愿意或是忘了,秀梅腰间的小布袋还紧紧地系着。胖鬼子一脚踩住小布袋,不让秀梅翻动身子,另一只脚不住地踢姑娘的屁股,叽里咕噜着又去解裤带扣。
兽行刺激着姑娘,她拼力扭动着身子,布袋带终于断裂了,她两手一撑地,起身就跑。
胖鬼子顾不上解裤带,猛跨三步,一个饿虎扑食,跃蹿四五尺远,倒地伸手死死攥住了秀梅的一个脚腕子,一个恶拉,将秀梅拉倒在地上。
胖鬼子狞笑着,咕噜着,提着秀梅的两脚向坟岗地的草密处走去。人的两脚离了地,就算是青壮年男人,力气再大也难以使上劲,更别说是一个女孩子了。
秀梅无助地挣扭着,绝望地哭喊着:放开我——放开我——阿婆啊,快来啊……
胖鬼子在草密处停住了,微微弯下腰,两手臂用力一绞,将秀梅扭摔成脸朝天,紧跟着一个蛤蟆跳,骑坐在姑娘的两腿上,两手死死地揿压在青春的胸脯上。
秀梅只觉得气喘不过来,身子动弹不得。她深知自己已经成了被恶狼咬住了喉咙的小鹿子、小羊羔子,求死不成,紧闭着双眼,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地呜呜着:妈妈呀,快来救女儿啊,女儿没了妈妈,活得好苦啊……
胖鬼子看着身下的猎物,父亲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如果把杏子娶回来,那你的艳福定会不浅。可现在早已是时移地易人变,那本属于自己的艳福早被人强占去了。尽管自己已睡过许多个中国女人,但只有眼前这个中国女人才配与杏子相比。便淫笑着说:“花姑娘的,哭叫的不要,你的,我的,快乐的大大的有……”
这胖鬼子正是西川纯一郎,如今他已经吃喝成了个大冬瓜。
姑娘顿觉无数条毛毛虫才爬上了脸颊,又向颈窝口爬去,她羞辱难当,悲愤难鸣,心如刀绞,所有避耻寻死的手段都被剥夺了,只有呜呜着,扭动着,踢蹬着……
邪恶控制的时空里,美丽、圣洁和善良永远是丑陋、野蛮和残暴的牺牲品!
就在魔爪行将实施进一步的凌辱时,终于激醒了姑娘那强烈的自护自卫意识,她猛抬头一口死命咬住恶贼毛茸茸的小手臂,借势一手撑身,一手抡拳狠狠砸向恶贼耳门。恶贼才痛叫出声,遭重击的脑袋跟着“轰”一声响,上身随之失去重心,不得不用一手去撑地。姑娘就势抽出一条腿,抬脚狠命向恶贼肩头蹬去,趁机翻身爬起来就跑。才跑出十来步,眼看着恶贼再次逼身,姑娘一头撞向大柳树……
就在这时,只见王兴才慌慌张张着跑过来,边比画着边说:“太君的,不好了,有人的,过来了……”狼狈为奸的一对不敢久留,将昏迷不醒的姑娘抬到快艇上后,很快就不知去向了。
当秀梅的爷爷奶奶和大旺漫无目标地寻找到坟岗滩口时,都一眼看到了那摊刺眼的血污。顺着滴滴血迹望去,只见有个人一动不动地俯卧在坟岗地的滩脚上。
走近看时,见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一只脚踩在浅水里,一个膝盖蜷曲着,两手向上伸举着,十个手指都抠进了泥地,似要奋力爬上去一般。
大旺轻轻将女人的脸侧过一点,秀梅爷爷一眼认定这个横遭不测的女人是拐脚阿婆,忙凑上脸去,试了试说:“怕是没气了。”
那情形分明在提示三个人:坟岗地上另有隐情。三个人都已脱掉了鞋,大旺拉着爷爷奶奶一起上了坟岗地。坟岗地本不大,三人走到岗地中央,举目四望,没见半个人影。大旺和爷爷奶奶一声又一声呼喊着,也没半点回音。
坟岗上像样的树没几棵,视线几乎没什么遮拦。地上倒是一寸不漏地密长着野草。只见草挨草,草挤草,密密丛丛层层叠叠地密生着,好似铺上了层绿茸茸的绒毯子。
其中最多见长得又旺相的要数苈板草。苈板草的叶子长长窄窄的,通常都斜伸着,只是叶梢稍稍下弯。远远望去,那叶子就像是一片片细细窄窄的小木板条似的。这也许是苈板草得名的由来。
苈板草的叶片极富韧性,就是青叶,轻易也踩不烂、压不弯。一到秋后,农人们喜将苈板草割回去晒成草干以备用。冬天闲来无事时,就用它来搓绳、打草鞋。搓成的绳打成的鞋自比稻草的光洁,而且耐用。每年秋后,大旺和秀梅爷爷都要上岗子来打上几小捆的。
忧心如焚的大旺见一片苈板草绵伏着,料是被人碾压而成。忙跑过去细看,在一丛枸杞子树旁,看到了那只熟悉的小布袋。
小布袋鼓鼓的,一边的带子断了。秀梅奶奶过来一认,便“秀梅呀秀梅呀”的一声声痛哭起来。
这意味着什么,虽不见秀梅人,已不难推知大致的情景,只不知何方恶人所为。大旺心痛似割,情急如焚。他想,心细的秀梅或许有意将小物件丢弃在草丛里,便仔细搜寻着可疑的印迹。寻到大柳树下,大旺一眼看见树干上沾附着新鲜的血迹,更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这血迹说不定就是秀梅以死抗争时留下的,大旺立时似利剑穿心般痛彻难已——秀梅遭恶人强暴无疑——不追杀恶人,誓不为人。就在此时此地,大旺定下了追杀恶人的决心——不管秀梅是死是活,定要替秀梅报仇雪恨。
大旺一遍又一遍回想着秀梅那银铃般的笑声,桃花般的笑容,蜜糖般的话语,金子般的心灵……出门时,他还在思谋着,今晚上,定要秀梅兑现亲口许下的“十记屁股”,哪怕是隔着衣衫的也要。怎能想到,至美至爱会惨遭……不觉悲愤填膺,胸中似翻江倒海一般。
为了不让爷爷奶奶见到血迹而更加伤心,大旺随即返回到老人身边,从奶奶手里接过小布袋,边劝慰边搀着老人一步一步走下坟岗地。
过了浅滩沟,大旺安顿老人坐下,把小布袋交给老人,然后去捋摘了一大把芦叶,让老人擦去脚上的淤泥,以便穿上鞋子。
秀梅爷爷正要叫大旺去把拐脚阿婆背过来时,大旺早已返身跑了过去。他伸手细细试着阿婆的鼻息,一试,急忙说:“爷爷奶奶,阿婆还有一口气。”
老人一听,都顾不上穿鞋子,忙起身过来做接应。大旺两手平托着阿婆过了浅滩沟,两老一个托头,一个抬脚,将她轻轻放躺在地势平坦一点的滩地上。
只见拐脚阿婆脸色蜡黄,昏迷不醒。上衣散着,满胸膛满衣襟满裤腰都是污血。滩脚坡上的泥地更是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创口在两乳间偏右,伤及右乳廓,右乳房像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
为什么一个从不害人的善良的残疾人竟会遭此惨绝人寰的横祸!三个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恨在心头:只有畜生才会这样做。要逮住了恶人,就是千刀万剐也还难解心头之恨。大旺想着救人要紧,便对爷爷奶奶说:“你们照看一下,我去叫人来。”说着,赤着脚一溜烟急奔而去。
秀梅奶奶看着这肉露露的惨烈惊心的创口,一边替拐脚阿婆理衣襟,一边想着孙女,惨痛重上心头,又号哭起来:“是哪个天杀的啊,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我的孙女儿啊,还我孙女儿啊……”
秀梅奶奶泪水淋淋地想去擦一擦拐脚阿婆伤口上的泥浆水,见创口还在隐隐出血,忙说:“老头子,小布袋里有红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