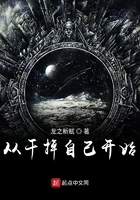松本不紧不慢说着话的时候,绫子紧锁的眉头渐渐松开来,犹如在迷雾中透过来一缕阳光,又似在迷途中发现了一条羊肠小道。
就算暖意有限,小路艰险,在活命都困难的情况下,有人肯搭救你一把,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好死不如歹活。那人就算是趁机要捞你一把好处,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比起那些见死不肯出手相救的富人来,已是恩德有加了。
因而绫子忙说:“三叔,你别这么说。你在我哥陷于危难之际出手相救而不收任何一点财物之利,又在我家几次面临山穷水尽之难处时不惜全力相助,更别说是当不当过不过了。
“我大话说不上半句,但侄女我还是个知情知义之人。在此,先让我代父母兄妹先谢过三叔的深情厚爱,日后有机会我们再报三叔的大恩大德。”
松本看着妩媚姣美的绫子,想象着多年不见的丽子的模样,谦和地说:“侄女言重了。救纯一郎不过是举手之劳,扶贫帮困,人之本分,更何况是自家人,何谈大恩大德。只怕是丽子的肩头还嫩,要受苦受累了,你回去要多多开导开导。”
绫子心知肚明,松本三叔看中的是丽子更嫩的“肩头”。她思忖着,松本三叔虽卑下,劫嫩色心切,但要是换了四叔五伯六爷,也绝不会有一个例外的。
男人们天生好色。也许是农村的灾荒让城里的有钱男人尝多了欲乐之欢而变得愈加贪得无厌起来。那恶少就巴不得年年闹灾荒,早在前几年,就常把“狮子望天塌,男人望天灾”的话常挂在嘴唇边。
家里的困境是到了丽子不出来找活已无法排解的地步,而松本三叔家是她唯一合适的去处。绫子顺着松本三叔的话意说:“难为三叔对我们兄妹的一片慈爱心怀,丽子也是个知礼尽义的女孩子。我所担心的是她能否胜任三叔将要安排给她的活计。”
松本面露难色,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家里的那些佣工都是有缘有故而来的,刚才的谋划只是一时的情分之定。至于辞退哪个佣工,具体还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好让丽子来了既能胜任又能舒心,确实还需一番思考。
“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摆平,这本就不好办,而今天谋人与明天谋事结合起来考虑就更难了。好比是下棋,只动一两个子而要使全盘活起来,是很费心思的。不过,绫子你尽可放心,我会慎重考虑的。”
松本从裤袋里摸出几张纸币塞到绫子手里继续说:“你们姐妹俩就要与父母城里乡下两地分开了,纯一郎也是出发在即,照应父母的担子全在你们姐妹肩上。而你怕是两三个月难有一次回家的机会,好在丽子在我身边,我自会叫她多多回家的。这五十元钱,拿回去让兄嫂用上十天半个月再说。”
绫子忽然隐隐觉得,这一切好似松本三叔预先布设好的一盘棋,他一步步走来,下得是如此从容自如。就如高手,有时一子下去,看似闲棋,却能操纵棋局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自己和哥哥下黑白棋时,就曾一次又一次输在哥哥的谋算里。
当然,松本三叔是另一类高手,他会让你求之不得又后悔不已,后悔不已时又求之不得;当你输得很惨时适时给你一点意想不到的安慰和实惠,你也就不再觉得太过难堪,而且他会让你感到自己所经历的那种惨和痛是值得的,甚至是一种幸运。
不过,绫子很快就想通了,自己所看到的那些能呼风唤雨般的人物,又有哪个不是靠权势地位实力说话的。穷人原本常在别人的算计中,只要各有所得,也就不值得去多想了,更何况,松本三叔再次给了西川家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她再三谢过后就告别了松本君代,搭上了另一辆马车,松本为她提早付清了车马费。
从马车下来走回家,足有一支烟的工夫。绫子离城时买足了能带得动的米、面,还有一小块猪肉,两条小黄鱼,一小扎青菜,还不忘捎带了一瓶土烧酒。
绫子的父兄都喜好喝酒。平日里,要是有机会让他们在酒和肉中只许选一样,父子俩都会选择酒而不要肉。两人喝酒也很少用菜,都说这才是真正的喝酒。可这几年来,父子俩都滴酒未沾。
时运既常是让一部分人趋利获益的主要原因,又常是另一部分人失势得祸的最重要的外因。同时,在这祸福交替的过程中,会促使有些人不得不放弃某些旧俗陈习,而让另一些人沾染上新的恶习。
绫子曾想着带一块饼和几粒糖给妈和妹妹,可她对着饼和糖果呆看了好一会儿还是走开了。她想,不知三叔下回什么时候给钱,给多少钱。
回家的路上,肩头的沉重还没有心头的思虑沉重,她反复地思考着怎样去说服丽子。
踏进门口,绫子只见妈妈、哥哥和妹妹都围在父亲的床边,等着听自己的消息。她忙将米、面、鱼、肉、菜放在长条桌上,全不顾自己汗流浃背,就来到父亲床边,把酒瓶子塞到父亲手里后,将自己拜见三叔后所做出的安排简要向父母兄妹陈说了一遍。
尽管近些年来笑贫不笑娼已渐成风气,大部分农户家也早已是非娼即妓了,但对西川家来说才起个头儿。纯一郎和丽子听了一言不发,倒是父亲和母亲连连点头,明确表示没有异议。
绫子父亲闻了闻酒瓶口,撇了撇厚嘴唇一笑说:“这些年还真多亏了你们三叔。”儿女们好久不见父亲的笑容了,这一笑,满脸皱纹堆成了一条条深深的沟。妈妈、纯一郎、丽子也各自浅浅一乐,只是绫子另有辛酸在心头。
父亲的话倒也不算是太过的溢美之词。当年绫子能进丝纺厂,也全靠了松本荐头的情面。那阵子,某厂要招工的消息一传开,农村的年轻男女们便潮水似的涌过去,厂门口比戏场子还拥挤。但十有八九的人高兴而去败兴而归。
那几年绫子要是进不了厂,家里不仅要少一笔稳定的收入,外加还要多一张吃饭的嘴,一出一进两相比,这济荒度灾的日子不知要艰难多少倍。
晚饭是有鱼有肉有菜,饭是香喷喷的白米饭,还有一瓶酒。这在丰收的年景里,逢年过节也不过如此。不过,宴饮之欢大多乐的是心境,今番这顿团圆饭气氛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闷。没有人开口说句话,一顿晚餐倒像成了一幕哑剧。
纯一郎自顾自喝闷酒,绫子丽子只顾着扒饭。儿女们个个都自有难言的缕缕哀伤愁绪在心头。在远离父母膝下之前,都想把这难得的一点美味多留一份给父母。
父母拉扯大了自己,却在父母需要自己的时候远离他们。而且,明日兄妹分道姐妹分手以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在父母身边再聚首。
做父母的更是难舍骨肉。这回儿女们离家远去,“生离死别”之义当是包含在里边的,要不是国法、家境如此,又岂肯让乳虎远去,乳燕双飞。
儿女们明天将各奔前程,是福是祸,做父母不能不考虑,却是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下回骨肉团聚将在何年何月何日,也许只能在遥遥无期的守望中。这才是父母心头的最痛。
晚饭后,一收拾停当,绫子将丽子拉到屋后的僻静处悄声问道:“你眼里有恨意?”
丽子冷笑一声说:“是的,我恨老天爷为什么不长眼,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绝路偏偏是天造成的!我也恨当官的,有什么打不完的仗,要是哥哥在,自可多一条谋生的出路。”
绫子又问:“还恨我吧?”
丽子先是摇头,后又点点头:“有一点。”
绫子跟着问:“哪一点?”
丽子自是有气在心头:“为什么事先不说一声,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如今男人都色,有钱有势的男人更色。你让我去松本三叔家,不就等于要我进狼窝?你自己愿去那种地方,我不管,为什么还要拖人下水?”
绫子理解丽子心头的气:“你气不打一头来,只差没说我逼妹为娼了。你说你将要去的地方是狼窝,这也许不假,就依你所说,你替姐想一想,我去的地方是狼窝还是虎窝?
“我要是去了那狼窝虎窝就有钱能拿回来,那宁肯我受苦受难也绝不让你离家一步。可我什么都试过了,无法做到。如果你能为姐想一想,更为父母想一想,气也许早就消了大半了。
“你再想一想,要是有能耐,不想进狼窝,那就进羊窝兔窝去呀!不是姐逼你急,实在是姐一人难以支撑。那是人家算计好了的,容不得你算算想想,更不会容你挑挑拣拣。
“丽子,姐知你心志高,但你有所不知,如今这世道真是变了,就是进‘狼窝’、‘虎窝’自毁身子,也要看人家的脸色才行。姐明天就要坐床去了,都说姐妹最知心,要是姐有时间,事先会不与你相商吗?”
绫子的陈说没半句假话,也没半点虚情。
看着丽子带着歉意的眼神又欲说还休的样子,绫子接着又说:“像你一样,我也曾怨天尤人地恨过,恨老天不公,恨世道不平,恨人心叵测,恨男人色重……
“可恨到最后,只恨我自己,恨自己生在穷人家,恨自己生不逢时,恨自己是女儿身,甚至恨自己有几分姿色。你不知,我有时恨得痛不欲生还必须得先笑出声来,否则,连恨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恨过之后,毕竟可以得点甜得点乐。”
这大概是天底下所有生活在残酷境况中的女孩子们共有的一种悲哀。
停了停,绫子说:“你说有权有势的男人贪色成性,我何尝不知道。但他们既然是‘虎’、‘狼’,又何愁逮不到‘羊’。你再想想:我们不求他求谁去?求别人,如果没有钱物铺路,能有结果吗?不用钱物,还有什么可行的手段?
“我是听出了三叔乘人之危的弦外之音。这世上,就有些男人以霸占亲友的女色为能事,特别是送上门去的,他们觉得那是最稳妥的。图了别人的色,借机滴几点猫哭老鼠的眼泪,再给你一点小恩小惠,让你痛着的时候还无端地存着一丝感恩之心。不过,那点小恩小惠,确实也救过我们的一时之急,你也并非一点不知道。我也听说,捕鱼人大冬天下河捕鱼之前,常要吃些许砒霜以活血暖身子。我想,人要真是失去了所有的生存手段,还有什么‘砒霜’不敢吃不能吃?
“丽子,其实人都是被命运牵着走的,只是不如人牵着牛马那般看得真切。我认为,一个人既然逃不出命运的安排,那只有认命才有可能去获取一些实际的好处。
我常想,自古以来,人们为什么都称‘命运’为‘神’,就因为‘命运’确是神通广大,一般人是绝对逃不出它的摆布的。
“丽子,我早想透了,对于我们来说,与其空守那份毫无实际意义的自尊——说穿了,这份自尊在命都难保的情况下不过是一种用以自慰的自欺——还不如去转守那种能使生命得以延续的沉沦。因为,受人奴役的活法总比空想的自慰多几分实在的意义,否则,也绝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子心甘情愿地自赴妓途。
“更重要的是,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父母将我们养大成人,又怎么可以逃离现实,推卸反哺责任。我们自己可以为了自尊而饿死病死,但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爸爸妈妈饿死病死。
“要知道,我们并不是自甘堕落,而是出于生计所迫。你去三叔那里,不仅关系着爸爸妈妈眼前的衣食和病痛,更牵挂着哥哥和你我将来的希望。”
丽子的心近乎死了:“我们还能有什么希望?”
绫子肯定地说:“有。你我的沉沦是暂时的,哥哥纯一郎的升迁荣归之日就是我们的出头之时。丽子啊,你要明白,哥哥能否升迁,松本三叔关系重大,而他那里,你的作用至关重要。
“也许是三年前你裸露的胸背诱发了他对你的强烈的占有欲望,这反过来又为我们利用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你在他那里,必须多长个心眼,切不可任性,因小而失大。
为着救父母脱离贫病交加的危难境地,也为日后纯一郎早日得升迁,把乐子给三叔远比交给其他男人更有盼头,丽子你自可不必太在意。”
丽子没想到,仅年长自己两岁、一样胸无点墨的绫子竟思考得如此周密深远,她已无话可辩,全服了,于是点头表示没了异义。
西川纯一郎在暗处听到了绫子与丽子的全部对话,不觉愧疚不安起来。作为哥哥,作为男子汉,利用应征之机只一心想着自己能出人头地,很少顾念家人,甚至错认绫子只为自己而轻狂逐水流。
谁知她承担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后依然不失对未来的希望。自此以后,尤其是穿上军装以后,他的一切行动,都以活命升官为出发点。
“要是自己战死了呢?”纯一郎心头不觉一惊……一想到死,他急着要去找渡边杏子作最后的道别。
纯一郎害怕碰见杏子的弟弟渡边俊一,尤其受不了渡边俊一那鄙视的眼神。渡边俊一曾当着纯一郎的面讥刺他看上姐姐杏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纯一郎当然有些自卑。他怨自己长相像妈妈,又矮又瘦,个头还不及丽子高。
要是在两年前,渡边俊一的鄙视还不至于对纯一郎构成太大的威压。近两年来,渡边俊一像吃了发酵粉似的,个头一个劲往上冒,两人站在一起,纯一郎只及渡边俊一肩头高,那种仰脸看人的滋味太难受了。
纯一郎来到杏子家门口,见门虚掩着,没上闩,猜想是杏子留给自己的方便。纯一郎才轻手轻脚推门进去,就听到渡边俊一激动的话语,“我就不让你走,我就是不放手。”
杏子妈在矿井上班,难得回一次家。纯一郎估计是姐弟俩在争吵,只不知为何而斗嘴。越是怕鬼就越躲不掉鬼。也是相争无好言,纯一郎不愿贸然介入进去而自寻尴尬,想等听出个眉目后再说。于是纯一郎顺手将门轻掩上,伫立静听起来。
杏子说:“姐的决定自有姐的道理,你不要再难为姐了。”
渡边俊一回道:“明明是你在难为我,想走就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这难道就是你做姐的道理?”
杏子又说:“俊一,有些事理你还不太懂。你想,咱们村还有哪户人家对国家的征召令毫无实际行动?我们要是再像乌龟那样缩在自己的壳子里无动于衷,村里的人还不看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