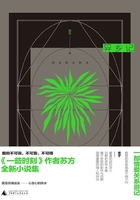宝根说:“鸡蛋如果没有缝,苍蝇想叮也叮不上。想那程家添了个劳力,饭菜的油水多了,程女一天天丰润起来。女人婚久不孕,在家自要讨丈夫欢心,出去自然想要摆足女人味,这样的女人就越发妩媚动人。女人漂亮没有错,但她总不该红杏出墙去。‘红杏出墙’和‘采野花’还不是一路货!”
引弟一面想着宝根是否在暗示警告自己,一面不动声色地说:“也许程女不过想要个孩子,怀不上孩子,不该总是女人的过错。打个比方说,母鸡孵蛋,有的蛋孵出了小鸡,有的蛋孵不出小鸡,那孵不出小鸡的蛋,是母鸡的错,还是公鸡的过?”
宝根语塞,过一会儿才说:“开头,程女也许只为借鸡生个蛋,不过,这种事一旦做了就没法收。到后来,程女也太放纵了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拣个僻静的河段,假装摸蚌摸螺蛳,竟就在水中做那事。”
引弟有些疑惑:“你怎么知道得这般细?”
宝根说:“我外婆家就在程家宅,那水中的‘戏’也正好被外婆撞见,只是没有点破。”
引弟叹息说:“那回外婆要是点破了,他们或许会收敛一点,不至于闹出人命来。”
宝根说:“我娘说起过,外婆也曾有过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痛苦经历,直到现在还常唠叨着女人一辈子最大的悲哀就在于错失了心上人。
“所以,外婆认为,年轻人就该有年轻人的性子,年轻人要使性子是防不胜防的。实际上,对程女,外婆心里怕是同情多于责备。”
引弟问道:“常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外婆这般唠叨,外公没给点颜色弹压弹压吗?”
宝根答道:“受弹压的常常是外公自己。当外公骂程女不贞不洁时,外婆反驳说,女人的贞洁只有给了心上人,才算真正完成了贞洁的使命。若是让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占了身子,女人的贞洁其实早已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空盒子,还管什么男人的看轻看重。要不是看在孩子的分上,就是死了也不觉得有多大的可惜。女人要是由别人指定着安排着与一个自己不相识又不爱的男人成亲,与母牛母羊被人牵着去交配有什么两样?这样的女人与母羊母猪母牛还有多少区别?
“外婆的这番话直让外公愣了半晌,过后才心有不甘地说,女人总不肯认命,死了值得吗?外婆则说,那是你们男人的算盘。女人自有女人的心思:女人就如一朵花,好花当自谢。就算是过早凋谢了,那份纯真的香和美自会永远留在人世间。不是这个理,祝英台的戏能唱到今天吗?外公被呛得哑口无言。”
外婆的话触发了引弟深深的共鸣,她的心震颤了,并且渐渐地明朗起来:说到底,男人心中所谓的贞洁与女人心中自认的贞洁,其实并不是同一块“玉”,绝对是不等价的。
女人自要守身如“玉”,那男人就该担当起护“玉”的责任。然而,就是那些整天鼓噪着三从四德的伪君子,却专干着毁“玉”损“玉”的勾当。就说那个江西客,不说他毁“玉”,至少也损了程女心中的美玉。
平心而论,程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思和行动究竟有几分是可以指责的?反过来想,程女要怀上了孩子,没出什么轨,没出什么格,就算是守身如玉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女人心中的“玉”岂不都成了可供定价买卖的货物一样了吗?还有什么贞洁可说呢!
引弟的心里愈加亮堂起来:女人的贞洁应该是肉体与心灵完美的统一,男女间的性事也只能是如此。女人之所以敢“离经叛道”,十有八九是因为失去了这分完美的统一。自古到今,祝英台、外婆和程女,她们其实都在勇敢地为自己的贞洁而抗争,所不同的只是斗争的方式和结果不同罢了。
引弟的心潮难以平静:女人固然应该重贞洁,可男人三房四妾了,还去逛窑子,连个鸳鸯喜鹊都不如,他们自己的贞洁呢?公道又在哪里?
一想到公道,引弟自然又想起了临嫁之前顺子哥说的笑话。
说有一个嫖客对妓女说,你真贱啊!
妓女回答说,是啊,从你爬上我身体的那刻起,我的皮肉的圣洁就全被你糟蹋完了,但我是被逼的。她又指着嫖客的鼻子说,但你还没有爬上我的身体,你的心和骨头早就贱了!你家里不也有女人吗,你要不贱,找我干什么?要论贱,我至少贱在你后面。
一说起公道,宝根自然偏向外公:“外婆说她自己没有做出越轨的事,但二十多年来,她心里一直念着心上人。问题是外公也始终没有去染指别的女人,你要是外公,会认为是公平的吗?”
引弟说:“不知什么缘故,在这一点上,穷男人和富男人好似合穿了一条裤子,常唱同一个调子。外公没有责罚外婆吗?
“说穿了,外公同样有一本难念的经。也许是同床异梦之后同病相怜的苦水和共同耕种的汗水冲掉了横在两人心头的障碍,一直相守相安无事。那程女就没有这种化解的可能。”
引弟愤懑起来:“就算程女不该做偷欢的事,那也没腥着旁人,应该让当事人自己去了账,别人为什么要横着加害于她呢?”
宝根自有他的说法:“说有人害程女也好,说程女自作自受也好,说天理不公也好,说人世不平也好,总之一句,美丽对于女人来说,少许是福运,大多是灾难。就如地上的花,越香越艳的就越有人去采摘。
“说书人不提诸葛丞相相则罢,一说起孔明,总要顺便说说他的丑陋的婆娘。诸葛亮常年带兵打仗在外,要是娶个美貌的女人做妻子,这花瓶怕就要被别人搂得多了,这才叫处处有先见之明。
“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尚且会有此担心,平民小百姓的,自管勒紧裤带的还难保其身,更不要说自己松了裤带败了风俗的,还谈什么谁害谁。”
引弟自然替程女不平:“听三婶说,程女不是管不住自己裤腰带的女人。她与旧相好私通,实则被逼无奈,只为怀个孩子。因为心切,才那般任性。她认为,怀上了孩子,就是事情露馅了,也好证明怀不上孩子不是女人的罪过。她竟敢冒这样的风险,她那时心里有多痛苦!
“据说,被捉双时,她坦陈了自己的想法,可没有人信她的。当问到要单游还是双游时,程女说是自己找上门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那帮兴风作浪的人便放了那男的。”
宝根补话说:“倒不是我有意责难程女。那程家宅东半场富,西半场穷,富家子弟没有一个安好心眼的,看见漂亮的女人,就像嗜腥的猫一样。程女偏又生就了俊俏的身段子,打她主意的富家子弟自然不会少。
“当初,尽管江西客常留出大段的空当,也许程女原本并没有水性杨花心,人又十分机灵,恶少们始终沾不上她的身便怀恨在心。也是她后来自己不争气,被头里的事有几回是不透风的,行得多了,败露是迟早的事,这是一错。”
“那第二错呢?”引弟急着想听下去。
“这第二错错在程女选择了单游。选择单游就等于选择了重罚。”
“一个人出面承担责任,为什么反而要处以重罚呢?”
其实,不论什么地方,对奸行的处罚历来很严酷,只是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选用的处罚手段有所不同罢了。在娘家的十多年间里,引弟不止一次听说过这类事,只是从没去过现场,便不解地问。
宝根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两个人的罪一个人顶,重罚是顺理成章的事。奸情败露时,一般总是男的溜得快,操办处罚事项的又尽是些男人,加重处罚女人当然是男人最乐意的。再说,女人,比如说寡妇,肚子搞大了,不重罚,一般也就不肯招出男的来。祖辈定下的规矩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引弟问:“双游怎么处罚,单游又如何重罚?”
宝根说:“双游时,一般让男女只穿条裤衩,赤着膊,并排游走示众。如果女的有点背景,或者家人出点钱买通了操办人以后,女人的胸脯前可以挂块小布片,甚至穿件小褂子。
“单游,按抛铜板的结果来定。图符朝上,全身被剥得不剩一根纱丝。如果字符朝上,可以穿条裤衩,但裤衩必须要剪破。剪在哪里,是否剪成条条缕缕,全由操办的人决定。
“说是按规矩办事,具体操办时,大多要走样的。就是捉奸捉了双,对男的看守松,男的逃了,操办者自然不会尽力去抓回来,甚至故意让男的跑脱,就好来单游。
“从小到大,我看到的几次都是单游。程女还算有点小幸,裤衩总共才剪了三四剪刀。不过一圈兜下来,全身上下沾满了烂泥巴、牛粪、狗屎和吐沫。”
引弟的悲怜不禁从胸中升起:“难道就没有人肯站出来辩几句,阻拦阻拦,护卫护卫?”
宝根说:“你倒说得轻巧,这可是伤风败俗的罪名。善良怕事的不敢走出门来;生性固执地不肯走出门来。在那个阵势中,十有八九是心存歹念假装正经幸灾乐祸要看戏的,还有一大群不大不小不识世事的孩子。是有几个长者出面求过情,可话一出口就淹没在铜锣声和喧闹声中了。”
引弟满含着不平:“我敢肯定,准是那些貌似正经其实满肚子坏水的人把程女逼上了不归路。”
宝根叹了一口气说:“事后,好心人也都这么推测过。那天游斗回来天已擦黑,围观的人早没了兴致都散尽了。那帮子人要挟程女去了祠堂,说是向祖宗牌位谢过罪后才能回家,后走的几个围观者当时听到了从祠堂里传出来的程女凄惨的哭叫声。程女本性刚烈,选择单游并无惧色,游斗临结束了却哭叫起来,而且哭声凄惨,大家料想程女遭了恶少们的凌辱,可惜早已死无对证了。”
引弟更是愤愤不平起来:“要是我,就是寻死也要等讨了个说法再去死。还有两个男的,竟保不了一个女的?”
宝根说:“程女回家后,一声声哭喊着心上人的名字,可始终不见其影子。那江西客还未到场角早知了一切情形,想必他认为女人丢尽了自己的脸面还尽呼着野男人的姓名,自是死活不肯再进程家门,但他没有走远。
“半夜时分,江西客救了程女一回,他以为没事了,也就一头不回地走出了程家门。不过善心使他又折了回来,当他再次将程女从河里拖上来时,程女已经气绝身亡。
“大家都认为,只要有一个男人守在程女身旁,程女也许还有救。依外婆说,程女是心死了才去寻死的。”
引弟为程女的惨痛命运痛心不已,默默无言时才对“要是来明的,多少还算条汉子”的话悟出了点含义: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必须明明白白地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肯来明的一手的汉子是靠不住的。
而程女那个“心上人”,在程女最需要他的时候,竟忘情负义逃了游斗,让程女一个人顶着耻辱和痛苦,到最后更是见死不来相救。这般负心,程女要是活着也会悔恨不已的。
引弟总觉得,宝根似乎还在提醒或者警告自己什么,她朝宝根靠了靠又问:“一笔写不出两个程字,同是程家宅的人,那些人为什么要对程女下如此的恶手段?”
宝根说:“人姓什么不重要,要紧的是要懂得男女之别和穷富之分。”
引弟说:“论男女有别我知道,这穷富之分怎么讲,与程女的惨痛命运又有什么关联呢?”
宝根用一种不屑一提的口吻说:“还问怎么讲!这世上,穷人的痛苦几乎都是富人和当官的造成的。都说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为什么,因为衙门是有财有势的人掌管的。就算程女手中捏着全部的理,你叫她到哪里去申冤申诉?
“古话说得好,为富者不仁,程女即使不遭难于私通,怕是迟早要落入富人设计好的某个圈套中,都因她太美又太穷。为什么有‘穷不跟富斗’的说法,因为穷是斗不过富的,你好好想想这个理。”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宝根果然是绕个弯子说自己。“怎么你越讲我越听不懂了?”引弟装作没听懂,轻轻拍了拍宝根的肩头说。
宝根捉住引弟的手,觉得手背似胖了许多,又放了胖手说:“自古以来,凡是富人,都打骨子里生就一副坏心肠,以为天下美色全该由他们来享用。皇帝是天下第一大贵大富,他就有资格到全国各地去收罗美女。你想,哪个朝代的三宫六院里没养着成千上万的宫女妃子。
“自皇帝以下,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官员和富人,又有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掠美成性的?掠美不成就想着毁美,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这是达官富人们共有的肮脏心思。”
引弟问:“富人为什么都有这种可恶可恨的心思呢?”
宝根说:“说起来很简单,那句‘温饱思淫欲’的老话早把根源给说透说穿了。而富人自不止于温饱,他们面上追求吃和穿,可骨子里看重的是淫乐。
“富人们大吃大嚼着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吃得心宽体胖,脑满肠肥,享口福的同时烧旺了淫欲心。他们穿绸着缎,拥毛围皮,显尽风流倜傥的富贵气时又助长了他们鄙视征服贫穷的邪气。
“俗话说,万恶淫为首,其实这话不过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万淫富为根。那些富人还常兼得权势,至少也是容易靠上权势。因而,他们自以为有恃无恐而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引弟觉得,宝根的这几句说得最为透彻,不知学了何人的舌头,她很想听下去:“那‘穷’字又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