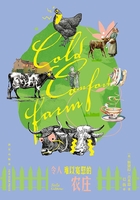第二卷 六、瓦罐被摔碎了 (2)
他的眩晕于他被押着赶来阴森广场的这刻烟消云散。一会儿他清醒了。这儿对他也已熟悉。开始,他的脑中或是在恍惚中,一道烟雾升起,抑或是水汽,弥漫于他和身边的事物之中,他只能模糊瞧见这些东西,似乎是隔着飘飘忽忽的梦中的迷雾,又如陷入梦中的黑漆。一切东西的轮廓都是晃动的,一切东西的形状都是变形的,各种物体重叠一起,庞大异常,人与物无限膨胀,和怪兽幽灵无异。幻觉过去,月光安定下来,一样回复原形,真实的世界显现眼前,他的双眼双脚受到了撞击,这撞击又使他方才自认为身在其中的阴森的诗意的境界构件挨个破灭了。原来他趟着烂泥糊,而不是涉足冥河;是盗贼而不是魔鬼在推搡着他;是他的生命而非灵魂在受到威胁;因为他没有钱,这玩艺可是在正人君子和强盗之间充当调解人的有效的宝贝。当他靠得更近,对这狂欢场面更加冷静分析时,最终脱离了群魔夜聚,一下子摔进了下等酒店。
这个下等酒店即奇迹大院,只是小偷云集之地,葡萄酒的红色和鲜血的红色相映成趣。
他那支衣衫褴褛的卫队最终把他在目的地扔下了。环境对他重归诗境并不利,和地狱的诗境也有差异。真乃粗俗不堪,下流十足。如果不是发生在十五世纪,若说格兰古瓦从米开朗基罗一跤摔进卡罗也不为过。
熊熊烈焰于一块庞大的圆形石板上燃烧着,一口此时没盛食物的铁鼎坐在火上,被火焰烧得通红。九张破桌子乱七八糟地搁在火堆四周,又被连“几何学”都没听过的仆役们搞得方正整齐,最起码各条边的相交角度让人感觉很舒服。桌上闪亮发光的是几个满盛葡萄酒与大麦酒的瓦罐,许多醉汉围坐桌边,或许借着火光,或许酒劲所致,每人都红光满面。中间一个大肚子的嬉皮笑脸地抱住一个肥嘟嘟的妓女接吻。一个“伪伤兵”吹着口哨把他那伪伤口的绷带解开,把他从早上就裹满绷带的强健有力的膝关节活动活动。对面一个生病的把白屈菜汁和猪血调和起来,想第二天涂在自己的“义腿”上。
两张桌子后面,是身着全套朝圣衣服的一个伪香客、真强盗有板有眼地唱着圣后哀史,有鼻音,还端出唱圣诗的腔调。那边,一个老家伙正教一个年青无赖装癫痫的方法,即要想口吐白沫便要咬嚼肥皂。还有一个忙着给自己消肿的装鼓胀病的人,搞得和他同桌的四五个女瘸子赶紧捂住鼻子,她们正为如何分配当夜偷来的一个小孩而发愁。这些情景,就像200年后索瓦尔说的,“皇室觉得很逗,可供王上消遣,并且在小波旁宫侍俸御前的皇家四幕芭蕾舞剧《黑夜》的初始部分。”另外一个1653年该剧的演出者又说:“这使奇迹大院的各种光怪陆离得到完美体现。为这个邦斯拉德特意写下了华章。”
粗俗的笑声、淫秽的歌声此起彼伏,个个都只是一味笑着、骂着、议论着,不管他人。相互撞击的酒罐子引起了争吵,本已破了的衣服被缺口的罐子撕碎了。
火堆旁一条大狗蜷着盯望。几个小孩也来掺和,那被偷来的小孩的哭叫伴奏着这场疯狂的宴会。高板凳上坐着一个肥嘟嘟的男孩,悬着两脚,把下巴够在桌边,不说一句话。还有一个表情庄重地摊着桌面上淌下的烛油。泥浆里蹲着另一个小孩,似乎要把全身钻进大锅中,他拿瓦片刮着墙,发出连斯特拉迪乌斯都受不了的噪音。
一个乞丐坐在大边的酒桶上,即乞丐王临政。
格兰古瓦被那三个揪住他不放的乞丐带到桶前,嘈杂的人们马上静了下来,只有那刮铁锅的小孩依然干自己的事情。
格兰古瓦吓得大气不敢出,低头不语。
“把帽子摘掉吧,老兄。”三个乞丐中的一个叫着。没等他回过神来帽子已被摘掉。这尖顶帽尽管破了,挡雨遮阳倒还凑合。格兰古瓦无奈地叹气。
这时,国王坐在酒桶上对他说:“这狗东西是何许人也?”这声音让格兰古瓦一哆嗦,这个既威严又有力的声音让他想到一个人。上午这个人在群众中“可怜可怜吧”的哼唧声让他的圣迹剧颇受重创,果不其然,抬头一看是克洛班?特鲁叶福。
那家伙的王者标记佩戴在身,但仍然一身破烂。已不见了胳膊上的伪疮,现在他拿着一根白皮鞭,即衙役拿来开路,被称为“布莱伊”的那种东西。头戴上头合拢有一圈帽檐的帽子,虽说是王冠但和童帽相差无几。格兰古瓦认出他即是那个在司法宫大厅中和他捣乱的要饭的,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丝冀望。
他咕哝着:“先生……老爷……陛下……怎样称呼您好呢?”称号一步步上升,已无可复加,上升或下降他拿不定主意。
“随便,老爷、陛下、伙伴无所谓。有何辩护词,赶紧说。”
“为我自己辩护?”格兰古瓦琢磨,“怎么这么说呢?我今天上午才……”他咕咕哝哝。
“魔鬼的指甲!”克洛班插嘴:“少放屁,混蛋,速速报上姓名。你听着,三位尊贵的君王在你面前:我乃克洛班?特鲁叶福,为丢纳王,继承了丐帮帮主之位,也是黑话王国显赫的君王;那边那个头上围着擦桌布的黄脸老人是玛提亚斯?亨加第?斯皮卡利,为埃及和波希米亚公爵;那个不听我们讲话,正和骚娘们调情的胖子是伽利略帝国的皇帝吉尧姆?卢梭。我们仨为你的审判官。你非本王国子民却擅闯进来,使我们城邦的特权受侵,惩罚在所难免。要是你是‘卡崩’。‘法兰米图’或‘里福来’倒也算了,用你们正经人的黑话说即小偷、装病或烧伤的,你是这种人吗?你可以给自己辩护。把身份报上来。”
“啊!”格兰古瓦说,“不胜荣幸,我是作家……”
“算了,”特鲁叶福又打断了他,“正派的市民先生们,把你吊死可谓易如反掌,我们将用你们对付我们的方法来对付你们。我们使用你们拿来应付无赖流氓的法律,我们嫌它太过严格不负责任。让大伙常看见正人君子套着麻绳项圈扮丑脸十分必要,可使项圈更加气派。过来,朋友,把你身上的破烂高高兴兴地脱下来分给小姐女士们,让流氓无赖开怀的方法是吊死你。快把你的钱分给大伙去买酒。还有什么花样吗?那边石臼中有一尊石头天主像,我们从牛头圣彼得堂偷来的。把你的灵魂扔给他吧,给你四分钟做祈祷。”
此番演讲真是骇人听闻。
“太好了,上帝保佑!教皇老人家也比不上克洛班?特鲁叶福英明。”伽利略皇帝喝彩道,这时为了放稳桌子又摔碎了一个酒罐子。
“各位君主皇上,”格兰古瓦不知为何恢复了冷静和坚定,“别这么想,我是彼埃尔?格兰古瓦,是诗人,我写了今天上午在司法宫大厅演出的寓意剧。”
“噢,原来是你老兄!”克洛班说,“我也在那儿,上帝作证,伙计,纵然如此,难道就凭那场让我们着实厌烦的戏是你写的就让我们留下你的命吗?”
格兰古瓦想恐怕我命将休了。但他并不放弃:“我不懂,诗人为何不算流氓无赖?伊索普斯是流浪汉,荷马罗斯要过饭,墨立利马斯是窃贼……”
克洛班接茬:“你故意用糊涂话迷惑我们。别废话等死吧。”
“丢纳国王陛下,原谅我吧,”寸土必争的格兰古瓦立即反唇相讥,“听听我的废话……过一会……听我讲……不由分说赐刑不合理!”
叫嚣声把他那可怜的申辩淹没了。那小孩更卖力地刮铁锅。更有甚者,一个老妪正将摊肥油的一口煎锅坐在烧得通红的三脚架上,受热后肥油毕毕剥剥地响,象一堆小孩叫着追赶狂人节戴伪面具的人似的。
这时,特鲁叶福正与埃及公爵与伽利略皇帝密谈什么。伽利略皇帝已大醉,接着他恼怒地叫着:“安静!”但铁锅与煎锅不理不睬,奏响依旧,他气得从酒桶上跳下来,把铁锅一脚推翻,锅连同孩子滚到远处。另一只脚把煎锅踢倒,火上立刻浇上满锅肥油。接着他威严地回到宝座上,那小孩哼哼唧唧在哭,老婆子骂骂咧咧的,因为她的晚饭化成火苗,吃不了了。这些皇帝可顾不上这些。
随着特鲁叶福的一个手势,走来公爵皇帝和丐帮大小长老形成一个马蹄状。格兰古瓦在马蹄状的中心,被人揪住,半圈人都衣衫褴褛,廉价的金属亮片,斧子、叉子、喝醉踉跄的腿,赤裸的肥胳膊,脏兮兮、傻乎乎、憔悴的脸。克洛班?特鲁叶福在丐帮圆桌会议正中坐下,实足一个元老院的议长,贵族团的首领和枢机主教会议的教皇。第一,因为他坐在高高的酒桶上,第二,由于他神情高傲阴森,让人发毛,凶光毕射。如果说一般的小混混都是畜类,那么他有种除尽粗鄙的剽悍劲头,即是众多猪脸之中的野猪头。
“喂”,他对格兰古瓦说,一边拿茧子遍布的手摸着变形的下巴。“为何不可吊死你,我弄不明白。你的确不喜欢这种事情,然而很容易,只是你们这些人没习惯而已,杞人忧天。总之,我们不敌视你,现在就可让你暂时脱离险境。你同意入伙吗?”
眼瞧命丧黄泉的格兰古瓦只得听天由命,可见这建议的作用之大。他象抓住救命稻草似地说:“十分愿意,我答应。”
“你愿意入伙扒手党?”克洛班又问。
“小偷,太好了。”格兰古瓦说。
“你愿做不纳税市民?”丢纳王接着说。
“愿做不纳税市民的一员。”
“想入住黑话王国。”
“想成为黑话王国的臣民。”
“成为乞丐?”
“乞丐。”
“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你得知道,国王讲过,纵然如此,你也得被吊死。”
“天哪!”诗人讲。
克洛班冷静地说:“只是在以后再办一个比较隆重的仪式。钱由咱们好心的巴黎城来出,由几个正派人拿美丽的石头绞刑架吊死你,起码安慰你一下。”
“要是这样也好。”格兰古瓦回答。
“另有优点。你成为不同于一般巴黎市民的不纳税市民,可免交清洁、济贫、街灯等各项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