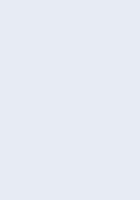奥里维又不出门了,不久克利斯朵夫也回来了。真的,他俩不可能献身社会革 命,奥里维不能同他们联盟,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这样。奥里维是作为被压迫的弱者而逃避,克利斯朵夫则因为是个独立不羁的强者而躲避。可是尽管他俩一个蹲在船头,一个蹲在船尾,他们总归于劳工队伍。自以为洒脱而坚强的克利斯朵夫,心存关切地看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他喜欢到骚动的平民堆里与他们混在一起,放松一下精神,事后就会更有劲儿更清醒。他继续同高加来往,偶尔也还上奥兰丽的铺子去吃饭,在那儿自由自在没有顾忌,无论多怪异的论调他都不会感到惊讶。他还故意做怪,煽动人家说更激烈的话。
在场的人也不明白克利斯朵夫是否态度严肃。因为他自己也越来越激动,终于忘了他本来是在闹着玩儿。有一次他有了灵感,即兴创作了一支革 命歌曲,立刻被人背熟了,第二天就在工人团体中传遍了。也因为这事儿,他犯了嫌疑,吸引了警察当局的注意。正巧玛奴斯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叫做爱克撒维?斐那,在警察局做事,很崇拜克利斯朵夫的,他告诉玛奴斯:“你们的克拉夫脱在干什么?他想逞英雄,我们都了解。可是上级愿意在这种革 命阴谋中抓个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样就能指控革 命党私通外国。如果这傻瓜再不当心,我们就得抓他了。那不是很麻烦吗?你去告诉他一声。”
玛奴斯通知了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要他小心一些。克利斯朵夫却颇不以为然。
“得了罢!”他说,“我当然不是个危险人物,可我想玩一玩,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工作,也有信仰。老实说,我们信仰不同,我们不是一种人……好罢,打架就打架,我才不怕……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能像你这样躲起来。那样,我几乎无法呼吸。”
奥里维可以呼吸。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和两个气闲神定的女朋友舒舒服服地待着。那时亚诺太太忙着慈善事业,赛西尔一心照看孩子,嘴里只谈孩子,也只和孩子说话,说些咿咿呀呀的话,把孩子那没有调子的歌曲慢慢地变成了人话。
奥里维同工人们混在一起,最终得了两个熟人,像他一样很自由。一个是地毯匠葛冷,他的工作完全是看他高兴与否,他十分任性,可是手艺很好。他爱把工作做得完美,对艺术品有鉴赏力,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一些修养。奥里维请他修过一件古式家具,难度挺大,他居然干得很好,但花了不少心思,收费却很公道。奥里维对他很感兴趣,询问他的身世和他对劳工运动的看法。葛冷没什么看法,他完全不关心。他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就是他。在工人中的小布尔乔亚中间,这等人很多,那是法兰西最聪明的种族之一:他们肉体的劳动和精神活动是平衡的。
另外一个就更古怪了。他叫做乌德罗,是名邮差,长相很体面:高大的个子,闪亮的眼睛,留着淡黄的胡须,表情开朗,是个没什么烦恼的人。有一天他去奥里维的屋子送一封挂号信。奥里维签字的时候,他在书房里看了看,把书目扫了一眼。
“嘿!嘿!你的古书挺多……”接着又道,“我也有一部分蒲高尼的文献。”
“你是蒲高尼人吗?”
邮差笑着,哼起蒲高尼的民谣,答道:“是的,我是阿凡龙一带的人,我的家庭可追溯到一二○○年,另外还……”
奥里维很惊奇,很想再了解一些。乌德罗也渴望有人听,他的确是蒲高尼的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他的祖先曾参加过腓列伯?奥古斯都的十字军;还有一个是亨利二世的国务大臣。从十七世纪起,家道败落,大革 命时期更是受了冲击。幸亏邮差乌德罗颇有魄力,安分守己地做着事,并且忠诚于家族,这一家子才又恢复了一点儿元气。他喜欢搜集一些谱系的史料,都是关于他的家族和乡土的。放假的时候,他就到档案保存所去抄录旧文件,遇到不清楚的,就去向考古学院学生或巴黎大学文科的学生请教。他倒并不因显赫的家世而过分得意。他一边笑一边讲,一点儿也没有怨恨命运的意思。他那种健康淡泊、快活的心情,让人见了十分舒服。
五一节近了。
巴黎有些可怕的谣言在流传,劳工总会那些吹牛大王又开始鼓吹。他们的报纸声称要大审了,号召工人纠察队行动起来,喊出“饿死他们”的口号,这让布尔乔亚深感恐惧。他们拿总罢工做威吓。胆小怕事的巴黎人有的躲到乡下去;有的怕乱起来,忙着屯积粮食。有一天克利斯朵夫遇到加奈,他驾着汽车,车里装着两只火腿和一袋番薯。他吓坏了,连自己属于哪一党都弄不清楚了;一会儿是老共和党,一会儿是保王党,一会儿又是革 命党。他对暴力的渴望好像一支疯掉的表针,方向不定地乱跳。在众人面前,他照旧和朋友们一样大叫大嚷,心里却巴不得随便来个力量打倒赤色的幽灵。
克利斯朵夫讥讽这种胆怯,认为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奥里维却很担心。他出身于布尔乔亚,想到以前的大革 命和面前的形势,布尔乔亚老是不免要心惊肉跳的。
“得了罢!”克利斯朵夫说,“放心睡觉罢,你的这个革 命不会那么快!你们怕革 命,怕挨打……所有人都这样:布尔乔亚、平民、整个民族、西方所有的民族。大家都珍惜自己的血,生怕流出来一滴,四十年来都在虚张声势。想想德莱弗斯案子罢!‘杀呀!杀呀!’难道没个够吗?好一群吹牛大王!费了多少的墨汁和唾沫!可是又流过几滴血呢?”
“别这么确信,”奥里维答道,“你知道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流了第一滴血,恐怕就会控制不住了,就会撕掉文明人的面具,露出野兽的利爪;那时谁还能制服它呢?每个人都在犹豫,但一朝爆发可就没法收拾了……”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这就是吹牛大王西拉诺和冒充英雄的尚德莱流行的原因吧。
奥里维摇摇头,他知道,这种吹嘘是行动的前奏曲。但说到五一节么,他也不太相信真会有革 命:事情已张扬开来,政府已做好准备,指挥暴动的领袖们肯定会把时间往后推。
四月的下旬,奥里维感冒了,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要病一场,而且还会诱发支气管炎。克利斯朵夫在他家住着照顾他。这次倒不严重,很快就好了,但是,奥里维照例还得休息一阵,十分虚弱。他经日卧床,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克利斯朵夫工作。
克利斯朵夫在伏案创作,写得累了,便去弹一会儿琴,并不弹他刚写下的曲子,而是随心所欲地弹。很奇怪的是:他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他以前的风格,但弹出来的倒像是别人的作品,粗暴、狂乱、骚动不安,完全失去了严谨的逻辑。这些即兴发挥,似乎是无意识的,直接从肉体迸发,像野兽在嗥叫,似乎在酝酿一场风暴。克利斯朵夫自己不觉得,但奥里维却感到有些不安。在身体虚弱时,他感觉异常敏锐,能预知未来,洞察细微。
克利斯朵夫按下最后一个键,满头大汗,一脸凶相地停了下来。他惊慌地四面看看,碰到了奥里维的眼光,便笑了起来,又坐回去了。
“你弹的是谁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奥里维问。
“我自己胡乱弹的,我只是搅浑了水,想抓几条鱼。”
“你要把它写进去吗?”
“什么?”
“刚才你弹的。”
“我全忘了。”
“那么你刚才想到了什么?”
“不知道。”克利斯朵夫说着,抬起手来摸摸额头。
他继续写他的东西,屋子里静了下来,奥里维一直盯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了,一转身,看到奥里维正温柔地望着他,眼里有无限的温情。
“懒虫!”他笑着说。
奥里维叹了口气。
“怎么了?”克利斯朵夫问。
“唉,克利斯朵夫,你心里还有多少东西啊!现在你陪着我,在我身边,可是将来你奉献出来的多少好东西,我都看不到了……”
“你疯了吗?到底怎么啦?”
“你的未来会怎样呢?还得经历多少风险,渡过怎样的难关呢?……我愿意陪着你……可是我却预感到了:我会被抛在半道上。”
“你真糊涂,你在说些什么傻话。即使你自己赖着不往前走,我也不会答应的。”
“你会忘了我。”奥里维回答。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坐在床边,面对奥里维,握着他冷汗涔涔的手腕。奥里维的衬衣敞开着,露出瘦弱的胸部,他那骄嫩的皮肤就像被风吹得很满快要破裂的帆。克利斯朵夫笨拙地为他扣上衣领,奥里维听任他这么做。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他温柔地说,“我已经经历过美满的幸福,可以死而无憾了。”
“哎,你在说什么?你不是健康得像我一样吗?”
“是的。”
“那么别说胡话!”
“对,我不该这么说的,”奥里维有些难为情,“大概是我的病弄得我精神不太好。”
“你要振作起来,喂!别老是躺着。”
“让我再躺一下。”
他仍旧躺在床上想心事。第二天他起来了,却只是在壁炉边继续想入非非。
那是个温暖的四月,常常起雾。绿色的枝条在白蒙蒙的雾气中舒展,雾中传来鸟儿的歌声,欢呼着等待驱散雾气的太阳。奥里维陷入了回忆:看到幼年的自己乘着火车,哭泣着在雾里同母亲离开家乡,安多纳德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她很美丽,而窗外雾中迷蒙的风景一一闪过。美妙的诗句如涓涓细流涌出心底,音韵、节奏都很和谐。他靠近书桌,这时要想记下这诗意盎然的境界是很容易的,但是他不想这么做。他很累,而且也明白幻象一旦被固定以后,就会失掉原有的香气。那是一向如此的:他不能展现自己最优秀的部分。
他的心像一个幽闭的山谷,里面百花齐放,但是他如果动手去摘,花儿就立刻萎谢,结果只留下几片花瓣,几个短篇,几首诗,隽永而凄凉。这种不能说出来的意境一直是奥里维最大的苦闷:感受到内心有无限的美好,却说不出来!……现在他隐忍了。不用人观赏,花儿也一样会开放,在无人采摘的地方,花儿开得反而更美。漫山遍野,沐浴阳光的鲜花不是更自在快活吗?当然,阳光很难照进来,但没有阳光,奥里维的幻景却会更美妙。那几天他心中有多少哀怨温婉的故事!不知它们从哪儿冒出来的,如同夏日天空上的白云,在空气中浮动消散,然后又有新的飘过来。这种故事他心中多得很。有时天空一碧万里,奥里维便晒着太阳迷迷糊糊,等着无声的梦幻再度拍着翅膀飞过来。
晚上,小驼子来了。奥里维心中有很多幻象,忍不住对他讲起来,然后微笑着陷入沉思。他常常这样,眼睛望向不可知的地方,孩子一声不吭。后来他忘了有孩子……讲到一半时,克利斯朵夫进来听见了,觉得很美妙,要奥里维再讲一遍。奥里维却不愿意:“我已经忘了,跟你一样。”
“没有的事,”克利斯朵夫说,“你最古怪了,对自己说的、做的,总是明白得很、你什么都不可能忘掉。”
“这便是我的不幸。”
“因为你忘不了,我才要你再讲一遍。”
“多烦啊,有什么用?”
克利斯朵夫生气了。
“这是不对的,”他说,“你的思想难道没有用吗?你丢掉了自己所拥有的,那是一去不回的损失啊。”
“不会有损失的。”奥里维回答。
奥里维讲述时,小驼子一动不动地坐着,此刻才醒过来,瞪着迷蒙的眼睛,阴沉着脸,神气很凶恶,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突然说:“明儿天气一定很好。”
克利斯朵夫笑着说,“我想他肯定什么也没听进去。”
“明儿是五月一日。”爱麦虞贤补充了一句,脸上放出光来。
“这是他的故事,”奥里维说,“喂,明天来给我讲讲。”
“胡说八道!”克利斯朵夫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要奥里维陪他去城里散步。奥里维已痊愈,但总是很疲倦,他不想出去,心中隐隐有些恐惧,又不喜欢混在人群里。他的心和精神都很勇敢,但身体却很娇弱的:他怕吵闹和骚乱。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但他不能自卫:因为他不愿让别人受罪。凡是虚弱的人都会比别的人更怕肉体的痛苦,因为他们对此更熟悉,而他们的幻想还要把它强化得更厉害。奥里维想到自己的肉体如此怯懦,觉得很惭愧,尽力想要压制自己的怯懦。但那天早上,他却不想和外界接触,只想躲起来。克利斯朵夫埋怨他、取笑他,一定要拖他上街,奥里维只是无动于衷,克利斯朵夫便说,“好吧,我自己去,去看看他们的五一节。要是没有回来,那我一定被抓进去了。”
他走了,在楼梯上,奥里维追上了他,他对让克利斯朵夫独自出门有些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