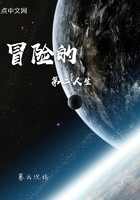朋友是什么?他是你找到的一个灵魂,使你在苦恼时有依靠,使你有个温柔的栖息地,使你在受惊时稍稍透一口气,他让你不再孤独,也不必再日夜警觉,担心给敌人可乘之机。得一朋友,你完全可以把性命交托给他,而且,你终于能够休息了;你们可以互为对方守护,他还可以保护你疼爱的人,给你最无邪的信任,而且还会倾心相许,为你两肋插刀。经过那次夜会后,奥里维终于有了一个朋友,他在狂呼:他跟我相隔那么远,又那么近,他永在我的心头,我的朋友是爱我的,我们相互占有,我们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了。那次晚后的第二天,克利斯朵夫一睁开眼睛便想去见奥里维?耶南——他立刻想见,于是在那个夏令早行的温暖的四月的一个早晨,克利斯朵夫不到八点便穿过被一阵轻雨笼罩的巴黎城去拜访奥里维。
奥里维的公寓在圣?日内维高岗下面的一条小街上,位于街上最窄的地方,但靠近植物园。克利斯朵夫忍着黑洞洞的院子尽头的难闻气味,踏上陡峭且倾斜的楼梯,走到三楼,一个头发蓬松且衣冠不整的妇女在三楼听到脚步声,开门出来,看见是克利斯朵夫,则摔上房门。这楼里住的全是些低俗的小市民,他们挤在脏乱的环境里,走过令人作呕的街道。克利斯朵夫满心厌恶地看着他们。
克利斯朵夫爬到奥里维那层,抓住打结的绳子拉响了门铃;铃声一响,好几家人都出来开门,穿着素雅整齐的奥里维也开了门,这马上引起克利斯朵夫的注目和愉快。奥里维的整洁,在这个肮脏地方给他身心俱爽的感觉。奥里维眼中那清亮的眼神,使他想起了头天晚上的印象,他向他伸出手去,奥里维一阵惊慌,嘴里嘟囔道:
“怎么,你,你来这里!……”
克利斯朵夫一心想同奥里维好好谈谈,故笑而不答,只是把奥里维推进屋里,走进了那间卧室兼书房的惟一的房间。克利斯朵夫首先是发现床上放着一大堆枕头,还有三把椅子和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几架图书和靠近窗的一张小铁床,把一间屋子占得没有空间。屋子里虽然很窄,光线也暗,可是布置得很好。水瓶里插着几朵蔷薇,显得很雅致,四壁挂着一些佛罗伦萨派的古画,房间干净、整洁,仿佛是出自于女人之手,而主人那种清亮的眼神也似乎有种反光照在屋子里,让房子生气不少。
“噢,你来……是找我吗?”奥里维热情地说。
“嗳,当然啦!”克利斯朵夫笑道,“你是不会来看我的。”
“你这么想吗?”奥里维顿了顿,然后又紧跟着说,“对,你说得对,可是我其实很愿意去!”
“那么有什么把你拦住了呢?”
“因为我太想见你了。”奥里维害羞地说道。
“不错的理由!”
“是啊,可……别笑话我,我就怕你不想见我。”
“我,哼,我就没这个顾虑!我来就是想见你,要是你不欢迎的话,我完全可以看出来的。”
“那你一定目光敏锐!”
他们对视一眼,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奥里维又说:“昨天我太笨了,生怕你厌烦我,我天生胆小,有一股让人讨厌的病态——我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别抱怨了,贵国喜欢说话的人太多了,能够碰到一个寡言少语的——哪怕是因为怕羞不爱说话的人,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克利斯朵夫为自己的俏皮话很得意。
“那么,为了这个你才来看我了?”
“是的,我是为了你的静默而来,这世上有好多种静默……我喜欢你的那一种,话是否说完了?”
“但你只见了我一面,怎么会对我如此友好呢?”
“那是我的事,我挑选朋友都是靠直觉,只要我喜欢,我就愿意让他成为我的朋友,如果是的话,我马上会去找他——而且必须找到!”
“你这样追求朋友没犯过错吗?”
“经常犯错。”
“你不怕这次又看错了?”
“那让我慢慢体会吧!”
“噢,那我可惨了,因为我一想到有人在观察我,我就会心惊,然后手忙脚乱的。”
克利斯朵夫好奇地瞧着他年轻的朋友,他朋友的脸红了。
“多敏感,”克利斯朵夫心里想着轻轻拍拍他的肩,“简直像个女孩子。”
“得了吧,奥里维,你以为我要解剖你吗?我最讨厌的也就是人家拿朋友来做心理游戏,我要的只是两个人敞开心扉,不要有所隐瞒,也不要怕自己说错话,这样不是更坦荡,更有男子汉气概吗?”
那一刻,奥里维对他肃然起敬:“是,没错,但你是强者,而我不是!”
“你肯定也是,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罢了,并且我就是来帮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刚才说的补充一点,我很欣赏你!”
奥里维马上脸红心跳,窘得什么也不能说不能做。
克利斯朵夫也不理他,向四周看了看:“你住的地方太差了,还有别的房间吗?”
“还有一间里面堆着东西。”
“嘿,这里简直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你怎么能够在这里生活?”
“我已习惯了。”
克利斯朵夫不答话,只是解开背心,大口地吸气,奥里维见他这样,便走到窗前,把窗子全部打开了。
“你肯定住得不舒服,但我却不会觉得有什么。我只要有空气就可活下来——无论在哪儿,但到了夏天,有时我也会受不了。那时,我坐在床上,就像快要窒息似的,想到那些快来的日子我便有一种恐惧。”
克利斯朵夫看看那些枕头,和奥里维一脸的倦容,他脑海中似乎正在浮现奥里维辗转反侧的样子。
“那么你完全可以离开这儿啦,干嘛还要留在这里?”
奥里维淡淡地说:“在哪儿都一样!”
这时,他们头顶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底层传来吵闹声,而街车震得墙在抖动。
“这种屋子!”克利斯朵夫有点儿激动地说,“到处是悲惨的景象,又脏乱又闷热,晚上怎能在这儿住?难道你一点儿也不泄气吗?换作我,一天也忍受不了,我宁可住在桥底下也不愿意住在这房子里。”
“最初,我和你一样,对住这房子也很难受,充满厌恶。还记得小时候和大人一起去散步时,只要走过贫民区,看到那肮脏的景象,我心里便作呕。我想,地震将我砸死在这里是我最怕的事。我根本想不到有一天我会愿意住在这种地方,说不定还要死在这儿。但我却没有权利去挑剔它,虽然我满心厌恶,只能竭力避免去想。当我上楼时,我就努力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我来说,只有外面那棵皂角树,我才可以看见——你瞧,越过那个屋顶,便可看见那棵皂角树——傍晚风吹树动的景致使我觉得身在田野。”
“是的,我知道你在出神,然而你不觉得用幻想来逃避生活,而不去寻求一种新生活没有意义吗?”
“这就是普通人的命运,难道你做一些无谓的抗争就有意义吗?”
“我不一样,我生来就为了奋斗,跟人家斗争是我的生活方式,瞧我的手臂。”他做了伸手的动作,“可你,却没什么力气,我早就看出来了!”
奥里维瞥一眼自己细弱的手腕:“是的,我的身子一向很弱,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总得生活下去!”
“你做什么工作?”
“教书。”
“教什么?”
“教很多课。拉丁文、希腊文、历史,为准备中学毕业考试的学生补习,而在市立学校,我还教道德课。”
“什么课?”克利斯朵夫惊讶地问道。
“道德课。”
“见鬼!居然还有道德课吗?”
“是的。”奥里维笑了。
“如果你能连续讲上十分钟相关的内容就太了不起了!”
“每周我讲十二个钟头呢!”
“那么你教他们学坏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善的本身是用不着说的!”
“那么就是说应该不说为妙了,是吧?”
“对啦,沉默是金,不能区分善恶的人便不会为善。善是一种行为,而非理论,只有软弱的家伙才会去讨论道德。而道德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软弱,那些迂腐的家伙教人道德,就好像是手脚残废的人教人行走!”
“那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你虽了解了它的真实含义,可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那就让他们自己像小孩子去爬,慢慢地自己就学会了,无论是手足并用或不并用也好,首先的事是要让他们会走!”
克利斯朵夫边说边来回走着,可不到四步便把房间给走完了,他打开钢琴的琴盖,随便翻了翻乐谱,抚弄了键盘一会儿,对奥里维说道:“弹点儿什么好吗?”
奥里维吓坏了:“真古怪!要我弹琴?”
“对,来,来,弹吧!罗孙太太说你是个很好的音乐家。”
“为你弹吗?噢!那会令我害羞的!”
克利斯朵夫不禁被这发自内心的天真话惹笑了,奥里维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要知道,在一个法国人眼里,这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克利斯朵夫说道。
奥里维却还在推辞:“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我弹呢?”
“我会告诉你的,你先弹吧!”
“弹什么呢?”
“你自己决定吧!”
奥里维叹了口气,坐到钢琴前,服从了这个专制且自动找上门来的朋友。他犹豫了半天才弹起莫扎特的B小调柔板——自以为在为莫扎特表述,可在音乐中却表露了自己的心思——音乐最容易泄露人的思想,暴露人的心事——开始时,他光是手指发抖连捺键的力气都没有,后来胆子终于大了些。而在莫扎特那一曲中,克利斯朵夫看透了这个新朋友:他体会到那凄美孤高的心愿和脸上温柔含羞的美,细腻敏感的神经和纯洁多情的心。到了曲终时,凄美的爱情终于到达顶点需迸发出来,奥里维无法弹下去:他手指哆嗦,垂下手说:“我没法弹下去……”
克利斯朵夫于是俯身将曲子弹完,说:“我听到了你的心声。”他抓住他的手瞧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我们似曾相识……而且我很清楚地觉得我似乎认识你很久似的。”
奥里维嘴唇发抖,差一点儿要抖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但是很久很久,他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
克利斯朵夫又仔细地端详他,然后微笑着,走了。
他离开时心情极好。他欢快地低声哼着,穿过了街道走进了卢森堡公园,找了张在阴凉处的长凳躺下休息,懒洋洋不想动。而树底下的阴影移走了他也不动,他思绪飘忽不定,只是感觉十分幸福卢森堡宫的大钟响时,他浑然不觉,后来才意识到敲的是十二点,已错过了哀区脱的约会。他笑着,打了个唿哨,轻快地回家了,进了屋子,他把衣服、帽子随手丢开,接着便坐下来工作。但他的心思定不下来,仿佛又回到了卢森堡公园一样。他虽然惊醒了几次,想集中注意力工作,可根本没有用,只有跑出去把头泡在冷水里,才清醒些,重新走回桌子边,他带着个慵懒的笑容,想道:“这似乎就像是爱情了?”
他似乎也很害羞,只敢悄悄地想,随后又耸了耸肩:“爱是只有一种……噢,不,有两种:一种是全身心地去爱人家,一种只是三心二意地爱人家。”紧接着又骂自己,“但愿我别这样吝啬。”
他再也不敢接着想,只是久久地对自己的内心的梦境微笑,低声唱着:你是我的,我才完整……
他拿起一张纸,静静地写出来刚才唱的。
他俩决定搬到一起住。心急的克利斯朵夫不管奥里维的租期还未到,要损失一笔租金,要奥里维马上搬,而谨慎的奥里维虽然很愿意马上搬,但考虑到经济方面,便劝克利斯朵夫等到租期满后再搬不迟,而奥里维的想法却令克利斯朵夫不解。正像许多穷人一样,他对这点儿损失根本不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奥里维在经济方面真正的窘境后,不由十分震惊。他立刻去向哀区脱预支了些钱,但他见羞红脸的奥里维不肯收起来时,一气之下,要把钱扔给楼下拉琴要钱的意大利人。奥里维只有把他拉住,收下了那笔钱,克利斯朵夫装作气冲冲的样子走了:其实,他是因为觉得自己太笨而懊恼,不知该怎样让朋友接受。但过了一段时间,奥里维的来信把他安慰了一番:奥里维把那些说不出来的话都写在信中,说他相当高兴认识了克利斯朵夫,而对克利斯朵夫的盛情亦表示极大的感激之情。克利斯朵夫马上像十五岁那年写信给他的朋友奥多一样,发了一封狂热的信,满纸充满了热情却傻气的话。
他们终于安顿好住的地方,新的公寓是由三间正屋带一间厨房组成,房间朝着一个围在高墙内的小院子,它就在蒙巴那斯区,靠近唐番广场。他们住在六楼,从那里沿对面较低的墙上望过去,能看见一所修道院的大花园,园子里很荒凉少有人迹。总之那环境较符合奥里维的胃口,因为那里有参天的古树,在阳光下随风摇摆,有成群的小鸟唱着婉转的调子。夏日的夜晚,燕雀唱着歌飞过月夜,蛤蟆浮上水面,发出阵阵有规律的叫声,若不是旧屋子被沉重的车子震动的话,你肯定会忘了是住在巴黎。
在决定住房时,因为有一间屋大且舒适,于是两个朋友相互推让,结果决定以抽签的方式来解决,克利斯朵夫耍了个把戏,巧妙地令奥里维抽到了那个好房间。
于是,他们进入了幸福甜美的时光;他们全部身心都浸在幸福中,所有的事令他们每分每秒都感到幸福。那段时间,那些深沉却静默的欢乐,惟有知己才能体会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