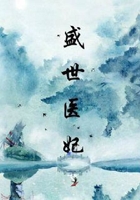李亚振
摘要:本文从宋末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士风与文学之互动关系,从士人风尚的角度探析吴文英的人格心态,将其置于历史与文学发展的交汇点上,从而诠释出梦窗词背后的吴文英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心理。
关键词:士风;吴文英;人格心态;审美心理
本文所涉及的宋末,特指南宋后期宁宗、理宗、度宗三朝,前后近八十余年。宋室南渡之初,曾一度呈现出“中兴”局面,但是自宁宗朝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矛盾尖锐,远甚于前代,南宋国势迅速衰落。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赵汝愚,将赵及其支持者陆续流放,致使赵汝愚暴死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同时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斥道学为伪学,开列“伪学逆党”党籍,立庆元党禁。后韩侂胄专权,盲目发动“开禧北伐”,在对金的作战中失败,导致金军入境,宋屈辱求和。同时,史弥远设计杀死韩侂胄,并将韩之首级送予金人,签下了宋金间更为屈辱的嘉定协议。此后,史弥远牢牢控制了南宋政局,且于嘉定十年,乘宁宗逝世之际发动宫廷政变,废原储君赵竑,另立自己易操纵的赵昀为帝,即为理宗。理宗朝时,因对史弥远擅权的不满,正直士大夫真德秀、魏了翁等纷纷上疏为济王赵竑鸣不平,继而引发出文化领域的江湖诗祸。大兴文字狱令众多文士多年后仍心有余悸。理宗后期、度宗前期,奸佞贾似道取得相位,排除异己,打击贤良,南宋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黑暗的深渊。
吴文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险恶的时代环境里,他出生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卒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这一段时间内党争激烈、权相相争,士人多于夹缝中求生存,少了南渡之初那种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爱国热情,大多数低迷颓败,顾影自怜。士人在一次次政治变动中渐渐消磨了自己的责任感,在腐朽没落的政局中自甘堕落,随波逐流,一时间奔竟、奢靡、变节之风泛滥,士大夫道德沦丧,甚至达到无耻的程度。而那些正直的士人,也不再如前代那样直言善谏,以天下为己任,而是采取躲避、漠然的态度,过起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隐逸生活,即使他们心里仍有挥之不去的入仕情结,却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压抑下去。在宋末士人身上,前辈士人的老成内敛被进一步萎缩,呈现出低迷颓废之相。
一、宋末士风对吴文英的人格心态的影响
(一)宋末的隐逸之风与吴文英的边缘人格
宋末时代,昏君当政,权相专权,造成了“君子在野,小人在朝”的不合理现象,正直之士或遭遇政治迫害,或不满于现实,畸形的社会加深了他们对政权的疏离。而南宋后期加剧的冗官政治使文人入仕艰难,科举之路艰辛而漫长,使他们不得不放弃科考而另谋出路。无论是在官场备受挫折和压抑,还是饱尝科考失利、倍感人生冷暖,末世的晦暗最终都将他们推向了最后的心灵净土——隐逸成为弥漫在文人士大夫间的普遍风气。
吴文英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潦倒终生,他先后于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入仓台幕,于淳佑九年(1249年)入浙东安抚使吴潜幕,于景定元年(1260年)客嗣荣王赵与芮邸。其中于苏州仓台幕的时间最长,近十年之久。其间,吴文英还因翁应龙的关系出入贾似道府,与权相史弥远的儿子史宅之(云麓)相交谊。吴文英没有入仕,却周游于达官显宦之间,这与其所生活的特定时代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对国家、社会怀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吴文英亦不例外。在梦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国事的关心,对仕宦生活的向往,更多的是入仕不成的失落。他的心中充满了“铜华沧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的家国之忧以及“浪迹尚为客,恨满长安千古道”的失意悲痛。因此,吴文英对政治有一定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却因为畸形的社会形态、腐朽的科举制度以及个人出身等诸多原因,惨遭时代的拒绝与庙堂的放逐。既然不能入朝为官,梦窗便只能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曳裾王门,附声权贵”,处理一些具体的幕僚事物,算是对不能进入仕途的一种弥补。但是他那种向往如苏秦、范蠡一样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业,留名青史的梦想却无法实现了,只能是“灯前倦客老貂裘”的一事无成。梦窗有对国事的关注和忧虑,但是作为幕僚和清客的他毕竟远离政治中心,没有经纬国家的权利,这样的状态是非常尴尬的,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如上层士大夫那样拥有雍容闲雅的心境或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更多的则是对自身生存处境的伤感和哀怜。于是在隐逸风气的盛行之下,梦窗亦希望在自然山水的抚慰下舒解人生失意的悲哀,寻找心灵的避难所。这其间多少无奈自在不言中。那么梦窗是否真的归隐了?在梦窗词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决意归隐的表述:
薄絮秋云,澹蛾山色,宦情归兴。(《水龙吟·用见山韵饯别》)化苏轼诗句“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表达对宦场的否定,写自己离开苏州仓台幕后,决意归隐杭州。
总不如、绿野身安,镜中未晚。(《瑞鹤仙·寿史云麓》)将仕途、官场比拟成镜中花,言现在认清仕途的虚幻未为晚矣,应及时退隐山野,享受隐逸之乐。
归隐何处?门外垂杨天窄。放船五湖夜色。(《大酺·荷塘小隐》)以设问的方式写出自己归隐的理想所在——不是门外垂杨那样狭小之处,难以容纳广阔胸怀,而是到范蠡隐居的太湖,月夜放舟,超逸洒脱。
湘浪莫迷花蝶梦,江上约,负轻鸥。(《江神子·送翁五峰自鹤江还都》)用庄周梦蝶之典,写不要迷恋官场仕途,人生短促,荣华如梦,不如早早归隐,实践鸥盟之约。
这样的例子在梦窗词中还有很多,可见在社会风气的熏染之下,梦窗亦有归隐的情结,但是仔细研读,却发现这些作品中真正写自然风光和隐居之乐的并不多,反而更多流露出的是一种对时事的无奈,面对现实,词人无可作为,放任自流,隐逸或许是一味安抚心灵的良药。而更重要的是,在古代潇洒归隐被看做是一种名士风范,文人不得入仕或是入仕不得志,归隐是一种不失身份的体面举动,亦可满足这些文人雅士附雅的心理以及弥补他们在心灵上的缺失。但是梦窗决意归隐却没有归隐,在十年苏州仓台幕僚生活后又先后在杭州、越州等地继续幕僚和清客的生活,毕竟归隐还需要肥遁之资。在仕途上无法立足,却也要面对生计问题。吴文英没有政治背景没有经济基础,如果辞掉幕僚的工作便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因此,梦窗虽有隐居之心,却也不得不面对生活危机。
吴文英胸怀大志却无法正常走入仕途,想要归隐却又囊中羞涩,作为封建文人的他,自幼接受的儒家教育使他不甘心于寂寞的老死田间,他在仕与隐之间无奈的徘徊,在这一天平上左右摇摆,然而这两种渴望又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当然,这种彷徨、苦闷与失落是时代、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士大夫权力核心阶层与真正的山林隐逸者相比而言,吴文英仕不能,隐不能,两难的境地造就了他无奈的心态和边缘化的人格。一方面,梦窗无法敲开权贵的大门,无法挤入政权中心,成为上层精英士人,另一方面,他既缺乏隐逸的资本,也没有真正老死埋名乡间的勇气。无论其如何挣扎,始终摆脱不了被孤立的命运和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他成了这个没落社会里的“局外人”,似乎自古以来文人雅士所应有的“正途”都没有他的位置,而正是这种“边缘化”的人格,造就了他多变的价值取向,使他不会像姜夔那样以名士、雅士的身份孤高自傲、不合流俗;更不会如稼轩那样尚侠任气、率性直言,因此,他的作品是苦闷的、感伤的、颓废的、繁复的、隐晦的,在末世隐逸之风盛行下他非仕非隐,这是时代凋敝所带来的压力,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曳裾权门”实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吴文英一生都处于不安、焦虑和彷徨的状态。
(二)宋末的奔竞之风与吴文英的矛盾心态
宋末奔竞之风的盛行,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士人道德的沦丧。吴文英所生活的理宗、度宗两朝,士风最为低迷。南宋后期,政治上的最大弊端就是权相专权,理宗时有史弥远擅权,度宗时有贾似道专政,宰相以个人之好恶掌握百官的任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于是一批士人为了能够尽快实现升官发财的愿望,禁不住利益诱惑,主动加入奔竞的行列。原本讲究“修身”的“清高”士人在名利面前成了名副其实的投机者、软骨头,他们见风使舵,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极尽谄媚之能事,奔竞之风最终造成了士大夫人格的扭曲和价值观的沦丧。
由于风气使然,吴文英亦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入到奔竞的行列,他是权贵门上的常客,以词章出入侯门,结交的朝廷显贵有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权相史弥远的儿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度宗的生父嗣荣王赵与芮等,梦窗与他们赋词唱和,过从甚密。在吴文英众多的交游之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与吴潜、贾似道的关系。这是因为吴潜和贾似道在历史上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为千古忠良,一为朝廷奸佞,吴文英却与这两位人品天差地别的人物都有较深的往来,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按《宋史》,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人。嘉定十年(1224年)以榜首登第,淳佑十一年(1251年)三月,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开庆元年(1259掂)八月,特进崇国公,判宁国府。还家。致仕离任时,庆元百姓匍伏挽留,热泪相送。可见吴潜是一个公忠体国、节用爱民之人。吴潜曾两度入相,颇有“贤誉”。后却惨遭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毒死于贬所循州。吴潜与贾似道忠奸对立,矛盾早已有之。据《宋史·贾似道传》载:“初,似道在汉阳,时丞相吴潜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移之黄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属江阃。黄虽下流,实兵冲。似道以为潜欲杀己,衔之。且闻潜事急时,每事先发后奏;帝欲立荣王子孟启为太子,潜又不可。帝已积怒潜,似道遂陈建储之策,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称旨。乃议立孟启,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这段史料讲了吴潜与贾似道的两次冲突:一是吴潜派贾似道驻军黄州,黄州乃是军事要冲,贾似道以为吴潜此举是要将他置于死地,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二是吴潜作为度宗的老师,在理宗面前却极力反对立其为太子,此时贾似道趁机上书,力主立忠王为太子,以迎合理宗之意,又命侍御史沈炎罗织吴潜指挥作战不力、在立储问题上“奸谋不测”等罪名,理宗便下令削去了吴潜的左丞相之职,流放其党人。最终贾似道密使人在循州将吴潜毒死,扫清了自己的政治障碍。
吴潜与贾似道忠奸对立,积怨甚深,形成党派,吴文英一介布衣,本远离权利中心和政治斗争,却在当时奔竞风气的影响下,不自觉卷入其中,饱受心灵的痛苦挣扎。
吴文英与吴潜最先相识,嘉熙二至三年(1238~1239)间,吴文英在苏州仓台幕上,吴潜任平江府知府(宋代称苏州为平江),而吴文英的兄长翁逢龙任该府通判,因这层关系,吴文英得以与后来的左丞相吴潜相识,二人志同道合、相交甚欢,梦窗与吴潜二人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产生很大影响。此期间,梦窗与吴潜二人曾共游沧浪亭,梦窗作《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词,吴潜亦有和章。通过这首词,可以看出梦窗与吴潜二人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有着真挚的友谊:乔木生云气。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旋小筑、吴宫闲地。华表月明归夜鹤,叹当时、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溅清泪。
遨头小簇行春队。步苍苔、寻幽别坞,问梅开未?重唱梅边新度曲,催发寒梢冻蕊。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
这首词感慨时事,词的上片从沧浪亭着笔,由悼古写起,缅怀中兴的英雄,伤叹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物是人非,词人潸然泪下。下片则抒发了二人游园的同忧同愁:“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东君,指的是吴潜,这两韵寓意深刻,词人盼望寒消冻解,国家能够重现春日景象,而把这一希望的重任全部寄托在吴潜身上。但是却是“后不如今今非昔”,国势日渐衰颓,二人面对这亘古长流的沧浪水,空怀一腔愤恨,无语付之一醉。通过此词可以看出,梦窗与吴潜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二人面对眼前景所生成的那种相知相恨之叹,体现了二人的真挚友谊和知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