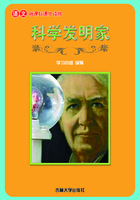我不清楚我是怎样到平台上来的,或许是加拿大人把我抱上来的。但我呼吸到新鲜空气了。我的两个同伴也在旁边尽情地呼吸着。而给我们送来这新鲜空气的,正是那海风!
“啊!”康塞尔说,“氧气,太好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呼吸了。”
至于尼德·兰,他没有说话,此刻他张着大嘴,如同燃烧着的火炉,拼命地在那里“抽气”。
很快我们就恢复过来了,我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在平台上的只有我们三人,船上的人员和尼摩船长都不在。难道诺第留斯号上奇怪的水手们仅仅呼吸流通到船内的空气就满足了,没有一人出来享受外面的新鲜空气。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感激我的两个同伴的话。他们在长期痛苦的最后数小时中延续了我的生命,我就是把我所有的感谢都拿出来,也觉得不够。
“好!教授,”尼德·兰回答我,“这事值得说出来吗!我们对这事没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这是很简单的事,因为您的生命比我们的更有价值,所以您必须活着。”
“不,”我回答,“我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真正有价值的人是善良、仁爱的人,而您正是这种人!”
“算了!”加拿大人有些难为情地说。
“你呢,我的忠实的康塞尔,你也一定受了很多罪。”
“说实话,先生,我并不觉得难过。无非就是少吸了几口空气,但我想我可以挺过去。并且,我看到先生晕过去了,我就也不想呼吸了,像人说的,这是断了我的呼……”康塞尔觉得自己太罗嗦了,没有说完就停下了。
“我的朋友们,”我情绪很激动地回答,“我们大家要永远在一起,同时你们有权利处置我……”
“我要使用这权利。”加拿大人马上回答。
“怎么?”康塞尔说。
“对,”尼德·兰又说,“我要到离开诺第留斯号的时候再使用这个权利。”
“还是先讨论一下眼前的事情吧,”康塞尔说,“我们现在是在向北走吗?”
“对,”我回答说,“因为我们是向着有太阳的方向走,现在有太阳的方向就是北方。”
“不错,”尼德·兰又说,“不过还要知道,我们是向太平洋还是向大西洋走呢?”
这点我不能回答他们,我怕尼摩船长要把我们带到广阔的太平洋中去,这样他就完成了他的海底环球旅行了。但是,假如我们回到太平洋中来,离开人所居住的地方,不敢想象尼德·兰的计划又会怎样,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久就会明确。
诺第留斯号走得非常快,不久就走过了南极圈,船头指着合恩角。经过合恩角时,我们已经忘记了以前的所有痛苦。我们只是想象着将来的情景。但尼摩船长好像消失了,在客厅中,在平台上都看不见他。他的副手每天把方位记录在地图上,根据它我就能知道诺第留斯号走的确切方向。就在这天晚上,方向明确了,我们是从大西洋的水路到北方去。我很满意,我把我观察所得的结果告诉了加拿大人和康塞尔。
“真是个好消息!”加拿大人说,“不过诺第留斯号要到哪里去呢?”
“这个我可不能说,尼德。”
“船长是不是去过了南极,又想去北极冒险,然后从西北方的著名水道回来呢?”
“有可能。”康塞尔回答说。
“那么,”加拿大人说,“我们就不能再客气了,恕不奉陪了。”
“总之,”康塞尔说,“尼摩船长是一位杰出人物,我们认识了他是不会觉得后悔的。”
“特别是在离开了他以后!”尼德·兰立即回答说。
第二天,诺第留斯号浮上了水面。中午前几分钟,我们从西面望见了海岸。诺第留斯号很快又回到了水底,靠近海岸,它沿岸走了几海里。透过客厅的玻璃窗,我看见很长很长的海藤,还有巨大的黑角莱,它长达三百米,简直称得上真正的铁索,它比大拇指还要粗,还很坚韧,可以把它当做船缆来用。另一种海草,名字为维培菜,叶有四英尺长,胶在珊瑚的分泌物中,它们像地毯一样铺在海底下面。它是无数甲壳动物、软体动物、螃蟹、乌贼等海洋动物的窝巢和食物。
在这物产丰富的海底上,诺第留斯号飞快地驶过。诺第留斯号在二十至二十五米深的水层,沿着美洲海岸向前行驶,尼摩船长还是一直没有出现。诺第留斯号的方向总是向北,它沿着南美洲蜿蜒曲折的海岸行驶。我们自从日本海出发直到现在,已经走了一万六千里了。
这种快速的行驶持续了好几天,后来,诺第留斯号潜入最深的海底,去找寻海底山谷,这座海底山谷是从与安的列斯群岛相同的纬度上分出来的。在这里,大西洋地质上的切面一直到小安的列斯群岛,有一道非常陡峭的悬崖,长六公里。另有一道差不多和它一样长的石墙,这样它们就把整个沉下去的大西洋州围起来。这座广大山谷的底层有些山脉,使这海底下面的景象异常的美丽。
两天内,诺第留斯号在这一带荒凉无物的深水中行驶。两天后,它忽然上升,来到了亚马逊河的出口,这个河口非常宽,输出水量很丰富,把好几里内海水的咸味都冲淡了。
穿越了赤道线,在西方二十海里有处法国的领地,我们在那里能找到容易藏身的地方。但是海风吹得厉害,波涛汹涌,仿佛不允许我们去冒险。尼德·兰一定了解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什么。当然,我也不提他的逃走计划,因为我不愿他做那些不会成功的试验。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诺第留斯号一直在海面上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