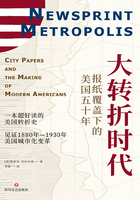这时,诺第留斯号的四周全都是冰墙,我们现在成了冰山的俘虏了。加拿大人急得用拳头拍打着桌子,康塞尔一言不发。我看着船长。他还是像平常那么冷淡、严肃,他双手抱胸,低着头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镇静地说:
“先生们,据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有两种死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被压死,第二种是被闷死。我不说有饿死,因为诺第留斯号还储藏着不少的粮食。因此我们只需考虑压死或闷死的可能性。”
“船长,”我回答说,“闷死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我的储藏库里有满满的空气。”
“是的,”船长说,“可是这些空气只够用两天的,目前我潜入水中已经有三十六小时了,诺第留斯号的空气需要调换。到四十八小时,我们储藏的空气就会消耗完的。”
“那么,船长,我们只要能想法在四十八小时前脱身就行了。”
“至少,我们要想法试一下,凿开围住我们的冰墙。”
“我们该从哪一面开始凿呢?”我问。
“当然从冰墙最薄的地方了,探测器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到时候诺第留斯号就停在那里,船员穿上潜水衣,就从那里开始凿。”
尼摩船长说完就走了。不久,诺第留斯号一点点地下沉,停在三百五十米深的冰底下,这是冰山下部冰层潜入水底的深度。
“同伴们,”我说,“情形真的很严重,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拯救我们自己。”
“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为了大家的安全,现在我准备牺牲我的一切。”
“好样的!”我对加拿大人说。
“还有,”他补充说,“我使铁锨和用鱼叉一样灵活,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请随便吩咐。”
“好的,我们一起去找船长吧。”
我和加拿大人来到船员换潜水衣的房子里,其他人都在换潜水衣,加拿大人也赶紧穿上了一件。几分钟后,十几个船员游出了船舱,我一眼就把身材高大的尼德·兰认出来了,尼摩船长也在其中。
在凿冰墙之前,船长做了种种探测,以确定工作的方向。探测完,找到最佳位置后,我们立刻开始工作。尼摩船长先在一个地方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其他人就在这圆圈的周围挖掘。过了一会儿,一块一块的冰被凿了下来。这些冰块受重力作用都飞快跑到冰层顶上去了。
两小时以后,尼德·兰回来了,他看起来疲惫不堪。现在轮到下一批人去工作了,康塞尔和我加入了这次工作。船副指挥我们干活,我一开始觉得海水特别冷,但我挥动铁锨,一会儿就感觉暖和了。
当我们工作了将近两个小时后,就被替换了下来。我们回来吃点了东西,歇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有点不适应诺第留斯号船中的空气了。这是由于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调换空气了。可是,我们在十二小时里,只在冰面上挖了不到一米的冰。如果按这种速度来计算的话,把通道挖好,至少需要五夜四天的时间。
“五夜四天呀!”我对我的同伴们说,“但空气没有这么多了,只够我们两天使用了。”
“并且,”加拿大人回答,“我们就算通过了这个通道,我们或许还要继续待在冰层下,不知要等多久,我们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到了夜里,一片大约一米厚的冰从这巨大的圆圈中挖了出来。但是,到了早晨,当我穿上了潜水衣,走过零下六七度的海水时,我发现冰墙又渐渐地连接了起来。冰坑中的水,也出现了重新冻结的现象。发生这种新的情况,显然又加重了我们得救的困难了。这样下去,整个诺第留斯号可能就会冻结在这里。到那时,我们必死无疑了。
我不想让我的同伴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免打击到他们做这种自救工作的勇气。不过,当我回到船上的时候,对尼摩船长说出了我的担忧,要他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
“我知道这事,”他对我说,语气还是那么镇定,“这的确是一个危险,但我还没有想出办法来避免这个危险。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工作速度要比冰冻的速度更快,我们要抢在前面才有得救的机会。”
这一天,我拼命地挥动着铁锨,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到了晚上,坑又挖去了一大半。当我回到船上时,我深吸了一口船中的空气,不过,差一点让我窒息。
这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醒来的。
第二天,我继续着挖冰的工作,现在的目标是要把第五米的冰挖出来。四周冰山的底层和两侧显然是加厚了。很显然,这些冰块很有可能在诺第留斯号脱身之前,就会凝结在一块儿,到时,我们会死死地困在这里。想到这些,我感到很绝望,铁锨几乎要从我手中掉下来了。再挖下去还有用吗?我们马上要窒息而死了,马上就要被像石头一样的冰压扁了,想必连最残忍的人也想不出这种酷刑来吧。
这时,尼摩船长亲自指挥大家工作,他自己也挥动起铁锨来。当他来到我身边时,我把冰墙指给他看,船长明白我要说什么,他对我做个手势,要我跟着他走。我随他来到船上,走到了客厅中。
“阿龙纳斯先生,”他对我说,“看来,我们得用些特殊的方法了,否则,我们就要被封死在这凝固的冰中了,就像被封在水泥里面那样,永远也出不来了。”
“对!”我说,“但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我不清楚诺第留斯号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承受这种压力,不会被压扁。”
“您说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问。我不明白船长的意思。
“水的冻结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当水凝固成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来炸开那些困住我们的冰层,就像它在冰冻的时候,可以炸开最坚硬的石头一般!您是不是现在感觉它并不是毁灭人的力量,而是拯救人的力量!”
“是的!船长。不过,无论诺第留斯号有怎样强大的抵抗力,它也不可能承受那种巨大的压力。那时,它会被压成一片钢叶的。”
“先生,我清楚这点。那么,我们就要对抗这种凝固作用,想办法消除它。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不但两侧的冰越来越紧,而且前后的冰也越来越紧了。”
“船上的空气还够我们呼吸多长时间呢?”我问船长。
“只能到后天了!”
我出了一身冷汗,感觉非常恐怖,好像我的肺叶中马上就没有空气了!
尼摩船长思考着,他沉默不语,一动不动。显然他已经有了一个主意,但是他好像又不太确定。最后,他说出了他的想法:“我们可以用开水试一试。”
“开水?”我问。
“对,先生。把开水从抽水机里不断地放出来,这样就可以提高温度,延缓水冻结的速度了。”
“可以试试。”
“我们不得不试试了,教授。”
当时,外面的气温是零下七度。尼摩船长领我到了厨房,那里有许多复杂的蒸馏器,它在蒸发作用下供应我们开水。当机器装满了水,电池的电热通过浸在水中的螺旋管传给水,仅仅几分钟时间,水就会达到沸点。然后,把开水送入抽气机中,同时进来冷水,补充流出去的开水。电池发出的热力很高,从海中吸进的冷水,经过机器工作后,再到抽气机中就变得滚开了。
我们开始向外面释放开水了,三小时后,外面的温度表显示为零下六度,温度比原来提高了一度!两小时后,温度表显示为零下四度,温度又提高了两度。
我看了这种工作的进展,同时检查了许多地方,最后,我对船长说:“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想会的!”船长回答我说,“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压扁了。但我现在担心我们会窒息。”
到了夜间,水的温度又上升了一度,开水就不能使温度再上升了。不过海水的冰冻作用要再低两度才会发生,这样,我们解除了被凝固的危险。
第二天,我们挖去了六米厚的冰,还有四米厚的冰需要挖去,这还需要四十八小时的工作。但是诺第留斯号的空气已经越来越让人感到窒息了。
这种空气让我感觉非常难受。下午三点左右,这种痛苦到了极限,我大口大口地喘气,不过呼吸到的空气里并没有多少的氧气,而且,空气越来越稀薄了。我完全处在一种昏沉沉的状态中,几乎失去了知觉。康塞尔也和我一样,他就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一直鼓励我,他低声对我说:“如果我不用呼吸就好了,这样就可以让先生多呼吸些空气了!”
听了他这话,我的眼中不觉充满了泪水。
我们大家在船上都觉得难受,所以轮到挖冰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并且很迅速地穿上潜水衣,立即出去工作!铁锨在冰层上吭吭作响。我们的胳膊累酸了,手弄破了,但这些疲倦、疼痛相对于新鲜空气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总算有新鲜空气吸到肺中了!人们总算可以畅快地呼吸了!可是,谁也不能超出指定的时间,延长自己在水下的工作。工作完毕后,自己就得将有氧气的气箱交给自己的同伴。尼摩船长最先做出榜样,一到时间,他就把他的气箱给另一个人,回到船上有害的大气中。他第一个遵守这种严格的纪律。他老是那么镇定,没有一句怨言。
这一天,就剩下了两米的冰要挖。这就是说,把我们跟自由海水分开的,只有两米的冰了。可是储藏的空气几乎要空了,剩下的一些空气只能留给工作人员使用,诺第留斯号是没有份的!
当我回到船上的时候,我差不多快要窒息了。多么难熬的夜!这样的痛苦是不可能描述的。第二天,我呼吸不到什么空气,大脑因为缺氧,疼痛得厉害,我昏昏沉沉的,就像喝醉一样。我的同伴们也和我一样,都在煎熬中。
这一天,只剩下了最后一米的冰,尼摩船长觉得用铁锨挖得速度太慢,决定用高压来冲开这个冰层。这个工作,由他一人策划、执行。船减轻了分量,它由于重力的变化从冰冻的一层浮了起来。当它要浮起时,大家就想办法把它拖到冰洞里。
这时候,所有的船员都回到了船上,诺第留斯号此刻全力加速。它先是用高压龙头冲击着冰层。
我们等着、听着,每个人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痛苦,都满怀着希望。这好像一场赌博,能否得救,完全就看这最后一击了。我脑子里嗡嗡作响,一片浑浊,但过了不久,我感到诺第留斯号有一阵颤抖。只听见冰层破裂时发出巨大的声响,诺第留斯号开始前进了。
“我们终于穿过去了!”康塞尔在我耳边低声说。
我不能回答他,我只是抓着他的手,紧紧抓住他的手。
突然,诺第留斯号像一颗炮弹一样,飞速前进。但是,现在从冰山下到自由海的航行的时间还要一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难免一死了!我在图书室的长沙发椅上半躺着,无法呼吸。我面部发紫,双唇变蓝,身体器官也失灵了。我听不到,看不见,时间的概念在我心中渐渐模糊了。我一动不能动。就这样,我意识到我马上就要死去了……
忽然,我醒了过来,只感觉新鲜的空气进入我的肺中。难道我们到了水面上,越过了冰山?
不!是尼德·兰和康塞尔——我那两个忠实朋友,是他们牺牲自己来救我。还有些空气留在一个气箱里面,他们不呼吸,把这些空气留给我,他们把一点一滴的生命送给我!我试着把气箱推开,但他们拽住我的手,于是我很畅快地呼吸了一会儿空气。
我看了一下大钟,正好是上午十一点。诺第留斯号以每小时四十海里的惊人速度向前行驶。它几乎是在水中作痛苦的挣扎了。
尼摩船长在哪里?他牺牲了吗?他的同伴们跟他同时丧失了生命吗?这时候,压力表指出,我们距水面只有二十英尺。仅有一座冰场把我们跟大气分开。难道我们不能冲开它吗?不过,诺第留斯号开始这样做了。我感到它采取倾斜的方位,把后部下降,将前面的冲角挺起来。然后,它像一架强大的攻城机一样,从冰场下面向上冲去。它先慢慢地把冰场撞开,然后退下来,再用全力向裂开的冰场冲去,最后,它被极大的冲击力带走,跳到了冰面上。
船舱立刻被打开了,新鲜的空气像潮水一样涌进诺第留斯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