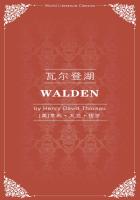“现代化”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明确的发展坐标,则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认识与大众认同的过程。大体说来,以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启动的开端,在最初的阶段,在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下出现的新的变革,仍是在传统儒学的思想框架内进行的。当时在排外心态下提出的“师夷长技”之说,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萌芽意识。从“御夷图强”到后来的“变法图强”,其核心价值都是“富强”,但是,对于如何“富强”的认识却是十分肤浅的,因此,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的认识和探索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皇权,共和代替了帝制,中国社会才渐渐突破传统儒学的思想框架,接受了西方输入的各种社会思潮,于是,学习西方,建设西方式的体制与文明,就成为中国变革的方向。这一时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也开始向“西化”价值观转化,但对实行什么样的“西化”却并无明确的认识,这是现代化意识形成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的认识和探索从器物的层面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国内展开了激烈的文化论争。如果说前期思想文化界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是为了指导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实践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化论争的直接目的,便是从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启民智,倡导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新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论争虽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但却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脚步。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与文明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在此期间,中国人虽然将苏联的发展模式作为未来的蓝图,崇尚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对现代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在现代世界的确切地位却并无明确的认识。这是“现代化”思潮形成的第三阶段。
二、“五四”运动初期的文化论争
五四运动初期的文化论争集中在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上。
当时在中国高举西方文化大旗的是《新青年》及其主要撰稿人,统称为“新青年派”。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封建文化。宣传西学,讨伐孔教,尊重人性注重人权,攻击封建宗法等级制度。陈独秀认为,近世文明的特征有三方面:“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1]而具备这种特征的典型国家是法国。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所羡慕并引以为战斗纲领的是《人权宣言》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们强调,为了使中国脱离蒙昧时代,应该急起直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反对中国固有的旧文化。
高举东方文化大旗的是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他们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西方文化为补充。在他们看来,东西文明的差异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是性质的差异。
1916,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自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假之所在。”他认为,东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2]
五四前夕关于东西文明的论战,还没有充分展开,论战双方虽然还只是通过列举某些表面的现象来说明东西文明的差异,但对两种文明的基本态度却已形成明确的思想分野。这种文化上的论争无疑为中国现代化的思路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线索。
三、五四运动后期的东西文化之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到了19世纪2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危机,在中国思想界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东西文化论争。这一次东西文化论争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为标志,一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新论战再次展开。
梁启超和梁漱溟站在东方文化的一边来认识东西文化。他们认为欧洲文化已无可救药,唯有中国文化能够拯救欧洲。梁启超指出,欧洲人过信“科学万能”,“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唯心唯物各走极端”,“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是抢面包吃”[3],而人们失去了为高尚的理想奋斗的目的。总之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梁漱溟认为,在东方文化受西方文化逼迫的紧的形势之下,应付的方法不外三条路:一是倘若东方化与西方化果真不并立而又无可通,到今日要绝其根株,那么,我们须要自觉的如何彻底的改革,赶快应付上去,不要与东方化同归于尽。二是倘若东方化受西方化压迫不足虑,东方化确要翻身的,那么,与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须有真实的解决,积极的做去,不要做梦发呆,卒致倾覆。三是倘若东方化与西方化果有调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现在这种“参用西法”可以算数的,须要赶快有个清楚明白的解决,好打开一条活路,决不能存疲缓的态度[4]。为此,梁漱溟提出了他的见解:“文化三路向”说。这三种文化路向皆以所采取的三种不同方向而界定。“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一路向代表西方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二路向代表中国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路向代表印度文化[5]。
争论的另一方则以胡适为代表。针对梁漱溟的观点,胡适进行了反驳。胡适认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连根拔去”和“翻身变成世界文化”这两条路所能完全包括的。针对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胡适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式,对于民族的文化不能下笼统的公式。
胡适指出,凡是有长久历史的民族,在久长的历史上,往往因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样式,往往有一种民族而一一试过种种可能的变法的。他认为各种民族都向“生活本来的路”走,而梁漱溟却认为中国、印度走不同的两条路。既然中国、印度可以走不同的两条路,那么,世界文化为何仅能以三条路向这种简单的公式来统一呢?我们承认民族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化所表现的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敢拿“理智”、“直觉”等等简单的抽象名词来概括某种文化,我们要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
由于胡适等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文化问题,因此,他们不愿意也不敢正视资本主义文明在当时确已陷入危机的事实。他们在反驳封建文化的同时,一方面完全抹杀中国固有文明的全部价值,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病百般辩护,不顾事实地把资本主义文化说成至善至美。在帝国主义的本质已经在全世界暴露得非常充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兴起,中国已不可能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旧坚持为资本主义辩护,这不能不说是西化派的历史缺陷。对于梁漱溟来讲,一战后欧洲文明种种弊端露出来,他便认为欧洲文化已无可救药,唯有中国文化能拯救欧洲,反对调和论,主张东方文化要么“连根拔去”,要么“翻身变为世界文化”。这种文化思想有其产生的背景,但也难免趋于简单化。
这一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反映出一战后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失望,对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迷茫。随着中国人对西方神话的破灭,五四以后,新文化人很快从追求法兰西文明转而学习苏俄社会主义,莫斯科取代了巴黎,而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希望所在。在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中,未来的世界新秩序之梦,很快为更光明更美好的新文明理想所取代。告别西方,“走俄国人的路”,预示着中国现代化范式转换的新趋向。
四、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与中国现代化的转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先进的中国人克服了狭隘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勇敢地睁开眼来正视现实,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比我们固有的文化先进的新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向往破灭,开始把目光投向苏俄。“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表征着新文化运动深刻的思想转向。
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论述东西文明的差异时,已经意识到“东洋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此危崖”[6]。不过当时还未能完全认识清楚这种既非封建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种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明。经过十几年的东西文明论战,他们的理论虽然还不成熟,可是他们的文化观进一步明确了,他们独立地打起社会主义文明的大旗。他们在不放弃对封建文化战斗的同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初步解剖,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即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唯一的结论。在东西文化论战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代表了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战线上的新成就。
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中,他高度赞誉了马克思主义之于当代世界历史的意义,将其归为俄国革命以及相继而起的中国社会革命的思想先导。继李大钊之后,瞿秋白先后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共同公律”,并认为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宗法文明和资产阶级文明都在淘汰之列,代之而起的只能是“通过世界革命走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道路”。他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上已经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但是不能因此就“向后转”,而是应当向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他还就“社会主义的文明”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他认为,在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同时,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由此可见,瞿秋白从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分析文明问题,直接回答的是中国革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不仅把“五四”以来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而且也透彻地阐明了文化问题论战的极端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至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争论的焦点。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营出现了新的分化。相继爆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
五四运动后期,在知识界,新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风行,引起了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满。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对知识界宣扬社会主义等各种激进的外来“主义”提出了异议。
胡适认为中国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非常多,空谈外来的“主义”不仅无益于解决社会问题,而且有被政客利用的危险。
继胡适之后,李大钊针对胡适的问题,在《每周评论》第35号刊发《再论问题与主义》,此文为其对胡适一文批评的响应。李大钊在文中对胡适关于知识界“空谈主义”、“假冒牌号的危险”、“过激主义”、“根本解决”等观点提出了批评,并阐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割,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而欲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其评价生活的尺度。否则,研究社会问题而与社会上多数人无关,那么社会问题就永无解决的希望。因而,社会运动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又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两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新青年》阵营及新文化运动分裂的开端。这场论战的真正焦点,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与“主义”、“具体”与“抽象”等哲学问题之争,而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之争。“问题派”之胡适主张在现存体制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渐进路线,“主义派”之李大钊则坚持以社会革命为“根本解决”的激进路线,由此才有研究问题与宣传主义的不同取向。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表征着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冲突,而且显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角色冲突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深层思考,即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模仿西方,实行渐进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