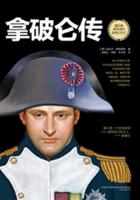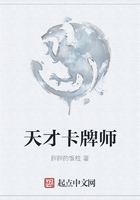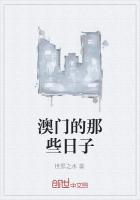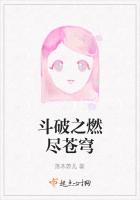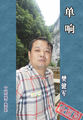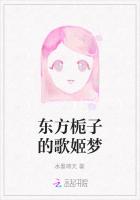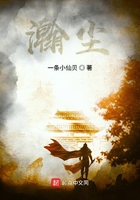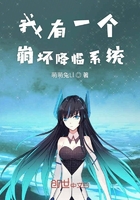在三结合过程中,工人、工艺人员积极配合、认真研究,共提出二千二百三十多条改进意见,被采纳用于图纸设计的一千六百六十多条,其中重大改进四十项,进一步完善了歼8机生产的工艺性。如后机身发动机冷却通风管和机炮输排弹槽形状极为复杂,图面上很难给出完整、准确的尺寸,工人师傅就按设计人员的构思和介绍的情况,先做出模型,经鉴定、配装合格后,再按模型测绘出图纸。又如机翼主梁取消垫块的革新方案,就是通过设计员章怡宁将自己的想法与工人师傅和工艺员交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并利用米格-21的主梁做试验,结果表明取消垫块,钢梁淬火后,变形不大,革新方案获得了成功。新方案不仅结构简单,温差影响小,而且减轻重量四公斤。实践证明“三结合”现场设计发图是设计与工艺相结合的好办法,它把设计人员的理论构思与工厂生产部门的实践经验,做到了有机结合,有力地改进了飞机设计的工艺性,充分调动了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大家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共同为新歼击机的研制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次科研与生产的较好结合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有其内在客观规律性。这就是科研人员必须在一定的物力、财力支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和精心设计,形成一套科研成果,然后在生产实践中听取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合理意见,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图纸日趋完善。下厂前,结构图纸已完成设计,系统、特设也都完成了打样设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下厂三结合的,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果研究所有生产加工能力,如果在批生产工厂中能开辟出新机生产线(至少有新机的试制车间),那么新机的三结合设计发图、新机的研制,当不致如此地步履艰难,效率就会更高,步伐就会更快。脱离科研和生产的内在规律,硬把研究所和工厂强行结合在一起,甚至提出什么“四个一”(一个实体,一个党委,一套班子,一个法人),都是无济于事的。难怪不少老科研人员说:“不搞厂所结合时,研究所和工厂配合的很好,一搞厂所结合,厂所关系反而十分紧张”。这恐怕是热衷于搞厂所结合的人失误的根本原因。关于如何认识歼8试制阶段的部院合并,厂所结合问题,当时我与陆纲同志有过几次长谈,充分表达了我的看法和做法,在本书第十章中专门叙述,这里就不细说了。
试制
1966年初,歼8研制生产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部、院合并前,原计划投产五架份,部、院合并后,三机部只准投产两架份(01架试飞,02架静力试验),这是后来拖延试飞定型时间的重要原因。
为了抢试制进度,工厂副总工程师罗时大和徐培麟、薛德馨、陈阿玉总结了以往仿制飞机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歼8的设计情况,大胆地提出了研制歼8时,不做整体标准样件,打破以往试制飞机采用模线样板、标准样件工作的惯例,采用了明胶板模线为依据,以光学仪器、型架装配机、划线钻孔台、局部模胎、局部量规为协调工具的综合工作法。歼8全机一万一千四百多个零件和二百多项标准件,从一百多个组合件直到前后机身对合、机身机翼对合,以及油箱、发动机在机上的安装,基本上都是协调的,达到一次对合安装成功,全机水平测量也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由于采取了这项措施加快了歼8机的研制进程。
为进一步缩短周期,采取了生产准备工作和飞机设计工作交叉进行的方法。2月初成立了随歼8飞机研制进程而移动的现场指挥部,由112厂罗时大、唐乾三、刘积斌、高德昌、孙国柱、薛家田及一所的钟敏昭等人参加。现场指挥部分管设计、技术、生产、计划、调度和供应等各方面工作,综合处理各方面发生的问题。指挥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随研制进程而改变。零件制造阶段,在生产准备车间办公。组合件、部件装配过程中,在装配车间办公。飞机进入总装时,指挥部移至总装车间办公。当飞机交到试飞站时,指挥部也随之到试飞站。这个短小精悍的指挥部,当时是有权威的。不仅行动迅速,解决问题果断,而且身在现场,解决问题准确,工作效率高。对歼8机研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12厂当时批生产线上有四大任务——歼5、歼6批生产(一年几百架),歼7小批生产和数不清的空军需用的零备件生产。这些生产任务极其繁重,压得车间没有精力想别的事情。按常规考虑问题,歼8研制无论如何上不了生产线。但用另一个办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激发人们的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心,以及不满足于老干仿制、要求改革的潜在精神力量,歼8这个庞然大物,虽有几万A4张图纸,就被几十个干了十几年仿制生产、技术熟练的车间消而化之了。硬是千方百计把歼8部件见缝插针地挤进了生产线,厂部生产办公室、技术办公室的同志们也积极支持。“三结合”展览会后,有的车间把过去安排歼8“见缝插针”的口号,改为坚决使歼8研制列车不在自己车间晚点。尽管计划部门,视歼8研制在生产线上是“软任务”,没有钱,不考核(有些同志死不相信自己能设计高空、高速歼击机,他们戏称国家投钱搞歼8研制是肉包子打狗,直到1967年在各方压力逼迫下,才列入考核计划,分点钱),但计划调度部门还是积极努力,东挪西凑,筹措经费使生产线不断前进。
1966年10月,根据部确保歼8 1967年底上天的要求,对歼8试制进度做了具体安排。要求1967年9月完成01架总装(试飞用),10月完成02架总装(静力试验用)。
一所参加“三结合”现场设计的科技人员,于1966年底发出全部结构、系统、特设图纸后,仍留下了一百五十多人的跟产队,在现场跟产,及时处理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共同的信念和愿望
1966年11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陆纲和我都靠边站了,从此我离开了歼8试制现场。1973年初“解放”出来工作,着重抓了歼8试飞定型。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机会继续参加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为了便于当时的试飞工作,也为系统总结歼8研制的历史,通过阅读一所的史料记载和向其他同志了解,知道歼8飞机在我被关押期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风风雨雨。我把这些情况综合记述如下,以使大家对歼8研制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967年初,“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夺权”之风铺天盖地,革命干部被揪斗,党政组织被冲垮,武斗不断升级,生产陷于瘫痪。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仍坚守岗位,甚至冒着枪林弹雨,坚持上下班。无论从住地到厂区、或是从塔湾一所大院到工厂所在地三台子上班的同志,常会在骑车行进途中,突然枪声大作,不得不弃车就地卧倒,等“战斗”和枪声过后再继续赶路。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当时情况的确如此。广大工人、干部、科技人员就是这样顽强坚守在歼8研制的第一线,为歼8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跟产队的赵国庆和蒋德超同志,以身作则,全心全意为跟产同志服务的可贵精神,永留在人们心间。在厂、所行政指挥系统均陷于瘫痪的情况下,为了使奋战在第一线加夜班的同志,能吃上“夜宵”(所谓夜宵无非是饼干一类食品而已),每天冒着危险,不辞劳苦,背上几十公斤“夜宵”和香烟,从一所步行到112厂,晚上十一点时由王南寿在办公室发到加班同志手中。这种忘我精神感人至深,他们为歼8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文革”中形成的派性十分对立,严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产的进行。而在歼8试制现场,却出现了惊人奇迹。观点尖锐对立的各派工人师傅、工艺员、设计员,只要一进了歼8装配车间(81号厂房),一律自觉地挂免战牌,不打派仗,不辩论,齐心协力,并肩战斗,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早日完成歼8研制。此奇迹滥觞于一个不成文的口头君子协定,时任歼8飞机代总设计师的王南寿,眼见派性斗争,已蔓延到了81号厂房,势必将严重影响歼8的研制。遂找车间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商量,探寻确保歼8研制的措施。共同的理想,促使他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定:为确保歼8研制进度,在歼8装配现场(81号厂房)所有各派一律不亮观点,更不辩论。就是这一条不成文的口头君子协定,竟使所有在现场工作的同志始终恪守不渝。无论社会上如何动乱,歼8生产在这里总能正常进行,厂内其他机种的生产已全部瘫痪,而这里的歼8研制仍在加班加点。原因何在?根本动力在于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愿望: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让我们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礼,感谢他们在特殊的时期,为歼8研制作出特殊贡献。尽管如此,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歼8未能按计划在1967年底上天。
在歼8型号01、02架研制的同时,试飞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六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歼8试飞问题。试飞所的同志和原定的首席试飞员,从1966年底就开始介入歼8试飞,多次到厂所进行试飞准备,直到1969年歼8首飞上天,并随同歼8飞机转场到阎良八所。
1968年3月5日,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批准成立由空军、三机部、六院领导同志组成歼8试飞领导小组,并要求歼8飞机于1968年7月1日上天。歼8试飞领导小组由空军常乾坤副司令员任组长,部院领导段子俊、曹丹辉、刘增敏等为副组长。下设空勤、地勤和调研三个组。从空军、三机部、六院共抽调技术干部四十余人,由空军干部高仲云和冯振沧分别任办公室主任和政委。办公室及三个组的人员均住在工厂,深入科研第一线和生产现场,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无论主机、辅机、成品、材料、试验鉴定,凡与歼8机有关的问题,他们都管,甚至亲赴西北等地,催成品、材料,直到把成品附件带回沈阳装机。
经过六院二所与410厂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的艰苦奋斗,1968年提供了首批装机的发动机,但规定只保证工作五小时,可见当时外协研制中的困难。
歼8历经磨难的01架机终于在1968年6月23日胜利完成总装、转到试飞车间准备试飞,接着又完成了02架总装。虽经“文革”的严重干扰破坏,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在党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进行现场设计,实行“三结合”,群策群力,共克难关,终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歼8机的生产试制。我国在自行研制歼击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不应被遗忘的总设计师
1965年5月正当在全所出现热火朝天大搞新机的兴旺景象的时候,总设计师黄志千出国考察,在开罗地区上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这是我国航空事业的重大损失,也给新机研制工作带来极大影响。我们立即调总体室主任王南寿代理总设计师,组织总设计师办公室,实施技术领导,并分专业负责。其成员有蒋成英(电子、特设)、顾诵芬(气动)、冯钟越(强度)、胡除生(军械、散装件)。
此外,还曾安排方宝瑞、沙正平在总体专业方面、沈尔康在系统方面、管德在颤振方面、詹心田在试验方面,协助总设计师处理一些有关的专业技术问题,实际也起了副总设计师的作用。
关于王南寿的任职问题,我向院长唐延杰报告说,我们所党委建议调总体室主任王南寿同志任总设计师。唐院长说,现在“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可先代理总设计师,待“四清”结束后,即正式下达任职命令。王南寿同志代理总设计师工作后,总体室主任由谢光接任,并抓歼9型号的准备工作。由于随后不久,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办理总设计师的任命手续。
“三结合”现场设计开始后,王南寿以总设计师身份兼任了歼8现场工作队队长。当时所谓的总师办,就是代理总师和副总师以及几个起副总师作用的同志的工作地点。其中负责全面技术工作的型号总管、兼具体负责总体专业的总师一人,即王南寿。所谓的总师办,实际上不是一个实体机构,而只是一个由五人组成、以代总设计师王南寿为核心的总师集团(或曰“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