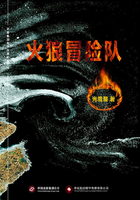她想起上午的堂上作文,从小到大,她对这一类的作文题目就异常敏感,既不愿触及也无法自然接受,并且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她来自单亲家庭,不为什么,就是不想。所以从小学作文开始,类似《我的一家》、《我的爸爸妈妈》这种作文,她就会编出一个父亲来,好在她爱看书,书中父亲的形象对她来说新奇、陌生,但仍可过目不忘。但是写出来如“爸爸摸着我的头说……”这种句式就觉得空洞又虚假,只能蒙混过关。但是无论做过多少训练,她依旧不能从容面对。像报纸上黑体字的大标题“他们来自破碎家庭”,就会令她异常反感。
这就是她头上无形的标签吗?这个社会看人看事,只要是负面的,第一句话一定是来自单亲家庭。
所以她对自己要求严苛,要懂事、刻苦好学、真诚助人,把所谓真善美像勋章一样,一枚一枚的别在身上,用事实证明她同样可以阳光灿烂。
她今天的作文,基本是一篇“爸爸语录”,她模拟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父亲工作很忙,需要挣钱养家,因为要出一趟长差,走前留给她一封信,如:“孩子,当你对自己感到失望时,不要钻牛角尖,找亲密的朋友谈谈吧;关注你的直觉,不要做你并不想做的事;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这样的人生才丰富多彩;不要用自我毁灭的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心理障碍的征兆……”不记得是在哪本励志书上抄下来的。
不过这一切妈妈并不知道,她们在这个问题上零交流。
崖嫣已经感觉到手腕乏力、酸痛,但她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妈,你很恨爸爸是吗?”崖嫣冷不丁冒出了这么一句话,这令她自己都有点吃惊。房间里明显静场。
须臾,母亲才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会啊……”
崖嫣的眉毛向上挑了一下,不过马上恢复原状,双手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但也只是片刻,又开始继续按摩。心中万分不解,文艺作品中都是满满的恨啊,什么挨千刀的,什么化作厉鬼绝不放过之类,书面语言是掩面疾奔、泪雨滂沱,都是当事人必备的神情。
或许,在崖嫣的潜意识里,她觉得可以聆听母亲了,希望接过她心中一半的担子。这一刻,她感觉内心还是蛮庄严的。
想不到母亲只是轻描淡写:“也许没那么爱,也就恨不起来吧。”一边说,一边慢慢地转动脖子,表示可以了。
她离开之后,崖嫣仍然想不明白,既然不爱也不恨,何以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呢?
5
每周星期五的下午,最后一节是美术课。
其实许多高中都没有美术课了,因为备考的压力,通常的做法是没用的课程统统让路。但是培诚高中部一直都有美术、音乐和体育。培诚有在省级或全国级才艺表演中拿名次的光荣传统。校长汪敏之出身教育世家,他坚持艺术熏陶是人的成长期不可或缺的一课,还有调剂枯燥和沉闷的作用,不见得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所以培诚不仅有美术课,还有学生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同时也是社团组织活跃的原因。
学校的大门是古色古香的琉璃瓦牌坊,迎面是一方陈旧而厚重的壁影,上面写着培诚的校训:至善至诚,培诚至醒。每周一的早上,汪校长都会衣冠整齐地站在壁影前面迎接学生们来上课,风雨不改。
他不能一刻不停地鞠躬,因为腰部有伤痛,发作时还要穿钢背心,他只是微笑,满脸都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蔚然。他最大的特点是包容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的所谓个性,能做到这点相当难得,因为学校和军队一样,是一个客观上消灭个性的地方。
培诚中学创建于一九○四年,历经学堂、分校等阶段,最终在一九六○年定名为培诚中学。这座有文化沉淀和传承的学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创造了经久不衰的高考神话,被称作神一样的中学。
汪校长的名言是,死抓学习,孩子会被抓死。而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也要从小培养,我赌的是后劲,是明天。
如果不说这些,断然没有人相信培诚还有美术课。
美术课的老师江渡,瘦高、平头、眼睛像充满星星的宇宙深洞。他的装束永远是深色的休闲裤,上身无论是黑T恤还是格仔衬衫,都是长袖但卷至胳膊肘之上,露出完美的手臂和修长的手指。整个人的感觉是久看尽显深秀。
江老师也不过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平时安静、低调、喜欢独处,深受广大的女同学喜爱。当然,崖嫣也是其中之一。
这一天的周五下午,是美术欣赏课《印象主义绘画》,上课前夕,同学们在德彪西的《月光曲》中进入教室。这就是典型的江渡风格,他会带着录放机到课室里来,讲台会擦拭一新,课本和教案绝对干干净净。有同学笑称他这是行为艺术,告诉我们学会欣赏现代绘画的重要性。
江老师还自打幻灯片,在一系列的名画中问同学们最喜欢哪一幅?为什么?最后才众星捧月一般地推出法国画家莫奈的风景画《印象·日出》,然后讲解此画以阳光和色彩为主角,借助光与色的变幻来表现作者从一个飞逝的瞬间所捕捉到的印象,从而成为印象派的代表画家。
他备课的认真程度让人匪夷所思,都什么年代了?如果不聊房子车子,至少也应该对时尚八卦有点兴趣,谁还有心情提升修养欣赏名画?只有他恪尽职守,没有野心,讲课时眉飞色舞,并不大管学生,有人打瞌睡或者做数学作业他也熟视无睹。
以往,江老师的写生课也是别开生面,他说这不是简单的对景绘图,不是看到什么画什么,也不是画得像不像的问题,重要的是生活体验,是和自然景观对话。所以他规定写生过程中“全程禁语”,只用心灵去感受大自然给予的美妙与灵性。那一次的写生地是在华南植物园画水杉,崖嫣也不是没有一点绘画天分,她画的水杉倒是比现实中的更安静、更深沉。
当时江老师走到她身后的时候,停留了一分多钟,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但是崖嫣觉得那一片刻时间漫长,令她好不自在,而且全身发热,额头冒出了细小的汗珠,后脖颈大概比脸还红吧。
这种异样的感觉让她又惊慌又羞愧,甚至有点憎恨自己。
下课的铃声响了,很奇怪,每一次江老师的美术课,崖嫣都觉得光阴似箭,稍稍恍惚了一下,课程就结束了。
同学们潮水一般地涌出课室,崖嫣还在慢吞吞地收拾书包,这时她看见张豆崩夹着一本精美的画册走上讲台,一边哗啦啦地翻着画册,一边跟江老师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什么,因为离得有点远,听不到他们聊的内容,但肯定跟课程有关,而且画册的封面是莫奈的另一幅名作《卢昂大教堂》,因为刚才在幻灯中出现过,令人印象深刻。
看得出来,江渡非常高兴,也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他是那种说到自己的专业就话多的人,平时似乎又沉默不语。
崖嫣其实从心底里面羡慕张豆崩,她不但聪明而且热情,有着润滑剂一般的性格,无论是扮酷的人还是自卑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她的暖意,这一切又自然天成,不加修饰。
她真是少有的受欢迎。
在高二(2)班,崖嫣至少发现有两个男同学喜欢豆崩。一个是“王行长”,王行长的本名叫王火牛,因为他爸爸是银行行长,比较有派头,所以大伙管他叫王行长。还有一个就是“筷子”,筷子的本名叫李瓦特,瘦成一道闪电,喜欢说“拿得起放得下”。张豆崩说,拿得起放得下那是筷子,人当然都是要纠结的。所以她们两个人背底里管李瓦特叫筷子。
说到喜欢,当然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是一种感觉。
比如王行长借文具,明明离崖嫣更近一些,但他会越过崖嫣,在豆崩的文具盒里乱翻,豆崩正好扭头跟后座的同学说话,回身瞪了王行长一眼,王行长就像得了奖牌一样高兴得要命。
李瓦特的目标是考上北航,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听说很难:实变函数、泛函分析、微分方程是三大天书,可以把人学到挂。直接把他刺激得跃跃欲试。这个家伙因为数学好傲视群雄,问他一道数学题就装聋,半天不吭气,要不就解释得飞快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崖嫣发现,如果是张豆崩问他数学题,他就痛快得多。
美术课,张豆崩为什么准备得那么充足?好像也备课了一样。难道豆崩也喜欢江老师吗?
看着他们两个人有说有笑地离开了教室,崖嫣有一点点失落和沮丧,若论她跟江渡的关系,那还真是“全程禁语”,他们至今都没有单独说过一句话。